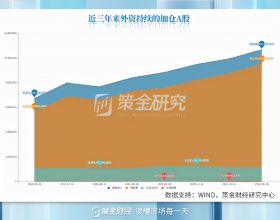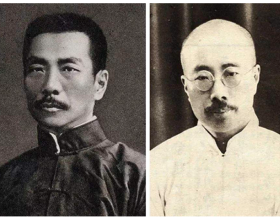中國國家博物館“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讓國博所藏大盂鼎與來自上博的大克鼎聯袂亮相,圖為展覽海報
最近半年以來,商周青銅器備受關注。繼上海博物館舉辦“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讓國博所藏大盂鼎與上博所藏大克鼎聯袂亮相,引發廣泛關注後,眼下,上海博物館正在舉辦“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這幾個大展不約而同聚焦商周時期最具特色的青銅文化風貌。
商周青銅器素有“國之重器”之稱。它們中的不少的確有著驚人的體量,例如子龍鼎(高103釐米,口徑80釐米,重230公斤)、大盂鼎(高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重153.5公斤)和大克鼎(高93.1釐米,口徑56釐米,重201.5公斤)三鼎,但這畢竟浮於表面。商周青銅器之“重”,更在於極為豐富而厚重的歷史積澱,有著從本質上體現其作為國之瑰寶的重要特徵。

最能體現商周青銅器內在價值的,當屬其中豐富銘文包含的文獻資訊
其實,單憑一尊毛公鼎就足以破除有關重器之“重”的迷思。現藏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它與大盂鼎、大克鼎並稱為“海內三寶”,但與盂、克二鼎相比,毛公鼎“僅”重34.7公斤,高53.8釐米,口徑47釐米,在重量方面就比前兩者足足少了一位數字。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毛公鼎卻佔有一項三鼎之最,那就是字數。據統計,三鼎內壁所刻銘文分別是497(毛公鼎)、291(大盂鼎)和290(大克鼎)字(引自杜迺松《中國青銅器發展史》)。毛公鼎銘文字數不但冠絕所有商周青銅鼎,而且也是中國所有已知青銅器中銘文最多的。按照杜迺松的說法,毛公鼎銘文數量“實可相當《尚書》一篇”。而盂、克二鼎雖不能在青銅器中佔據次席(現存字數第二多的,是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散氏盤),但在現存銅鼎中卻能緊隨毛公鼎之後,分列二三(因為銘刻四百餘字的周康王時器小盂鼎,四百十字的周共王時器曶鼎,都已於清末亡佚,僅銘文拓片存世)。

商周青銅器內壁往往刻有銘文,包含著豐富的文獻資訊(攝影:陳拓)
除了銘文字數之外,這些銘文所記載的內容,同樣體現了它們不凡的分量。按照原器所鑄時間來看,大盂鼎最早,為周康王時器。記載了康王對貴族盂的訓誥和賞賜。康王先是讚美文、武先王,然後總結了商代覆亡的經驗教訓,告誡盂要引以為鑑,不能沉湎於飲酒取樂。這部分銘文內容恰與《尚書·酒誥》等傳世文獻吻合,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其次,又授予盂掌管兵戎、民事的權力,輔佐周王管理天下。最後還賜予了他代表權威的鬯酒、命服、車馬等等,以及各類奴隸1726人,其中既有夷人的頭領十三,也有夷眾上千。
而大克鼎年代次之,為周孝王時器。講述了貴族克繼承先祖師華夫的官職,並被周王授予“膳夫”之職,獲得諸多田地人口的事情。孝王首先讚揚克的祖先侍奉恭王,因而提拔克為王臣,負責傳達王命的要職。接著重申了對膳夫克的任命,詳細記錄了對他的賞賜,包括禮服、土地和奴隸等等。最後是克叩跪感謝,鑄鼎以紀念其先祖師華夫。
三鼎中的毛公鼎相對最晚,為周宣王時器。它記錄了周宣王為中興周室,改變西周後期的種種弊政和不利局面,策命重臣毛公,監督各種政令的釋出和實施。希望在毛公的忠心輔佐下,使國家免於衰頹的境地。最後為了體現對毛公的尊重,宣王還賜給他極為豐厚的賞賜,包括各種寶物和貴重的車馬器。而毛公為了回謝周王,特意鑄鼎記錄此事。
三鼎銘文的時間跨度恰好分屬西周的早、中、晚三個階段,從中我們甚至可以對西周的歷史程序形成一些粗淺的認識。上古商周時代留下的文獻非常有限,除了《尚書》《逸周書》《竹書紀年》等屈指可數的傳世(或早期出土)文獻外,就只有同樣數量有限,且散落於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記載了。那麼,銘刻在商周青銅器上金文文獻,就自然要擔負起全面勾勒商周社會原貌的重任。而這才是商周青銅器之為國之重器的根本原因。
青銅器上的銘文作為第一手文獻資料,確實可以幫助我們在有限的傳世先秦文獻之外,復原西周史事,並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正如李學勤在《青銅器與古代史》中所言,“武王時利簋銘文記牧野之戰……何尊述興建成周……厲王時多友鼎記對獫狁戰爭;……此外,如衛盉、衛鼎、散氏盤等記土地轉讓,魯方彝、兮甲盤等記商賈貿易,曶鼎、訓匜等記法律訴訟,這些不過是西周重要青銅器中的幾個例子,其對研究當時歷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見一斑。”
那麼,顯而易見,最能體現這些中國商周青銅器所蘊含內在價值的,當屬其中豐富銘文所包含的文獻資訊,以及由其獨一無二體量、形制所體現的歷史見證感。

青銅器物所體現出來的“物質文明”,讓我們有機會一睹上古時代的審美旨趣
商周青銅器本身同樣散發出的不容忽視的藝術價值。
談到商周青銅器的藝術審美,最有發言權的當屬孔子。他在《論語·八佾》中就表達了對周人文化的讚揚:“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這裡所說的“文”,一部分說的是禮儀制度,另一部分則是由這些青銅器物所體現出來的“物質文明”。正是這些“文化遺蹟”不但為我們拼貼上古剪影提供了可能,也讓我們有機會一睹上古時代的審美旨趣。
當然,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來說,孔子所推崇的周代“文、物”其實也是從之前的“二代”逐步發展而來的。青銅文明在西周所走向的巔峰,離不開前人在技術和文化上的積澱。那麼要梳理其中的傳承關係,我們大體可以從青銅銘文、器形和紋飾這三個方面加以探討。
首先,西周中後期的青銅器銘文出現了小盂鼎(周穆王時器,400餘字)、曶鼎(周共王時器,434字)、毛公鼎(周宣王時器,497字)這樣超過四百字的案例,但這並非一日而成。如孔子所言,西周青銅器銘文字數增長的趨勢也可追溯到商代。商代固有甲骨卜祝習俗,但從商末遺存的銅器來看,既有如國博所展出“子龍鼎”一樣銘刻族徽的範例,也不乏銘刻數十字“長篇”的範本。
比如,今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商代小臣餘犀尊,銘有27字,今藏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的小子卣,蓋、器銘共計47字。另有故宮博物院所藏二祀邲其卣銘39字,四祀邲其卣銘42字,六祀邲其卣銘27字。雖然商末銅器銘文通常都只圍繞祭祀事件本身,並不作進一步展開,但都可以算作西周長銘文青銅器的先聲。而周人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將器內銘文華麗、繁富的風格發揮到了新的高度。

青銅觥是用於盛酒的禮器。圖為鳳紋犧觥,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館藏
其次,器形上講,周代青銅器繼承商代,但其中出現的新的組合變化,則反映了商周人群在觀念上的差異。商代青銅器按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三個時期,呈現逐漸增多的趨勢,殷墟所見銅器,在二里崗時期基本都已現身,其中既有對後世影響巨大的烹煮器鼎、鬲、甗和食器簋、豆,也有觚、爵、尊、卣等酒器、盛水器,以及兵器、工具等等。到了殷墟時期,除了出現了方彝等新型酒器,在其他器物中,圓鼎、方鼎都出現了胎壁變厚的情況,國博所藏子龍鼎、後母戊鼎是其中的代表。
西周繼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型別,數量增長的同時,種類有所變化。具體來說,從周初開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為固定禮器組合出現的頻率有所提高。這也是這兩類器型通常作為銘文載體而為我們所常見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漸少,但出現了新型的簠,樂器則出現了鍾。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型別在周代基本保持不變,但數量已經較商代大幅減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書·酒誥》所言,“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周王為了避免重蹈商末貴族酗酒荒政的覆轍,不但發文強調禁酒,還在大盂鼎等器的銘文中屢屢提及,給人留下極深印象。而且,隨著西周中期向後期的發展,當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歷史舞臺,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壺保留了下來,使後人對商末景象不禁產生無限的懷想。

第三,從紋飾上看,商周之間同樣存在繼承關係。商代廣為流行的饕餮紋、夔紋和鳥紋等主要紋飾基本都延續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細節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稜較先前更高、也更顯著),這造成了兩者之間較難區分的情況。幸運的是,大多數時候,周代青銅器內的銘文通常起到了斷代的作用。
不過,兩者之間同中有異,變化也在悄然間發生。西周青銅器足逐漸改變了商代粗壯的柱足、扁足樣式,朝著模仿動物足部的蹄足方向發展。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變得較淺,器壁也變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到西周中期開始,紋飾方面的變化則變得更為顯著。首先,紋飾由繁複變得簡約,饕餮紋等特徵鮮明的動物形象淡化。一個原因可能是,周代製作者對前代生動而具象的鳥、獸動物開始變得陌生,在追求儀式化的過程中,變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於同樣的道理,用於裝飾的細密雷紋等地紋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時代基本不用。此處的變化則與大量銘文的出現存在因果關係,因為複雜的地紋可能會對銘刻文字造成影響。其三,則是西周竊曲紋、重環紋等簡單而重複的紋飾,在西周中後期的青銅器中大量出現。它們或簡化自夔龍紋,或取自龜殼鱗甲,用於器物表面裝飾填充。按照李學勤的說法,這種變化“可能是禮制的宗教色彩減弱,逐步走向儀式化的一種表現”。從總體上講,也基本符合裝飾紋樣在歷史上不同階段的發展趨勢。
這些無與倫比的國之重器,奠定了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的自信和底氣
商周時代留下如此眾多的青銅重器,既豐富了我們對當時歷史的瞭解,也讓後人有機會一睹蘊含於器物之中的上古風韻。從這些古物中,我們得以理解“殷尚質,質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體驗“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不但窺見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讀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質彬彬。
從商人酒宴上“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的琳琅滿目,到周人對“殷鑑”的屢屢反思,從青銅紋飾豪華到質樸的變遷,我們得以繪製出一幅商周交替的動態景象。從周初克商,到中期為南(銅)北(馬)交徵,再到西周末期的銅料不貢、重器難覓,我們從青銅銘文中勾勒出一段傳世典籍之外的商周信史。而這些都離不開前輩學者對那些國之重器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而與此同時,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透過打破地域、時間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將從更多維度呈現商周青銅文物背後的歷史資訊。比如,上海博物館攜手中國國家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鄭州博物館、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機構,正推出名為“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覽。在該展覽中,禹鼎和噩侯馭方鼎一同現身,講述了這個西周古國與周王室之間的千古恩怨,也見證了西周王朝從鼎盛走向風雨飄搖的唏噓之路。
《漢書·郊祀志》提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青銅器作為無可替代的古代遺存,既是上古中國的真實見證,也為我們穿越三千年的歷史探索旅程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座標和導航。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這些無與倫比的國之重器,賦予了我們“鬱郁乎文哉”的古典氣質,讓我們不至於迷失在歷史虛無主義的想象之中,奠定了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的自信和底氣。
作者:顧雯(上海博物館館員)、張經緯(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
編輯:範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