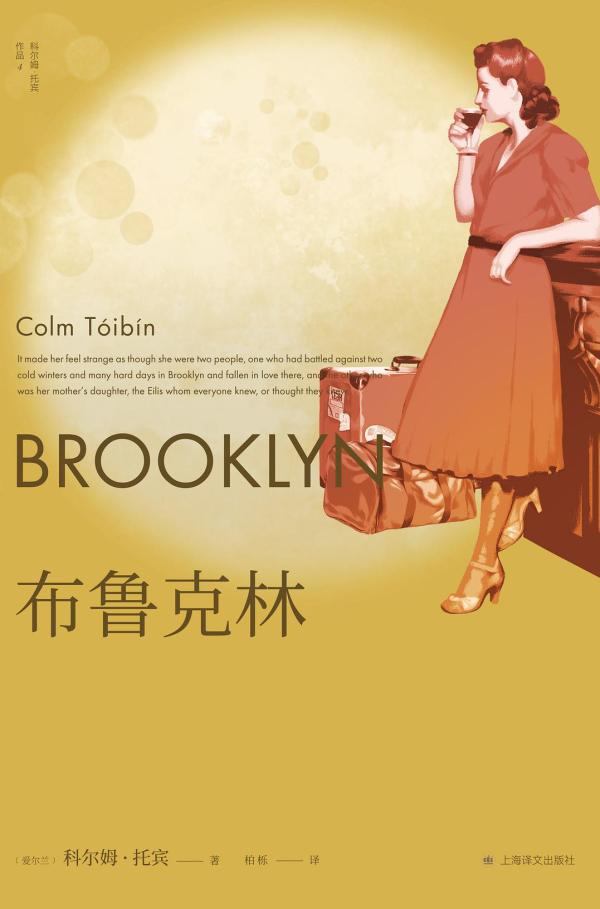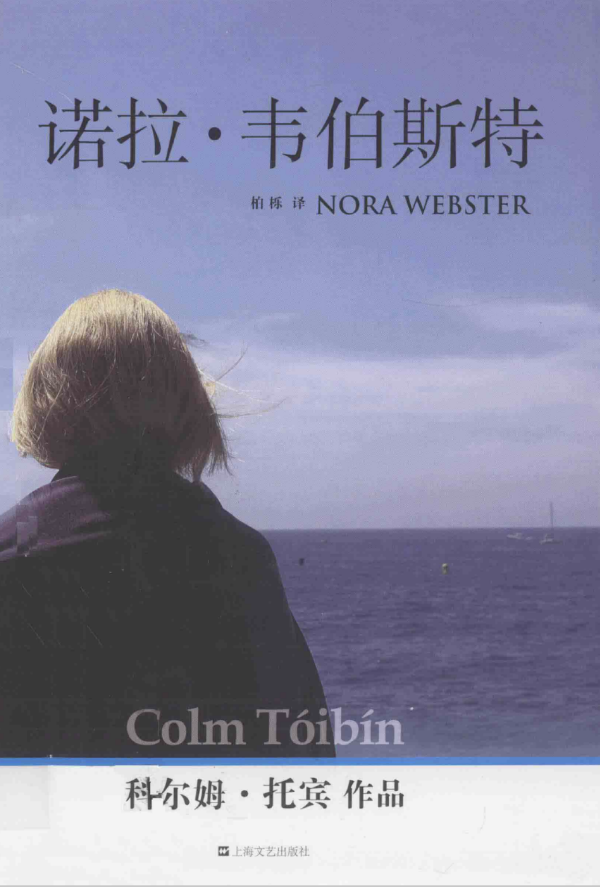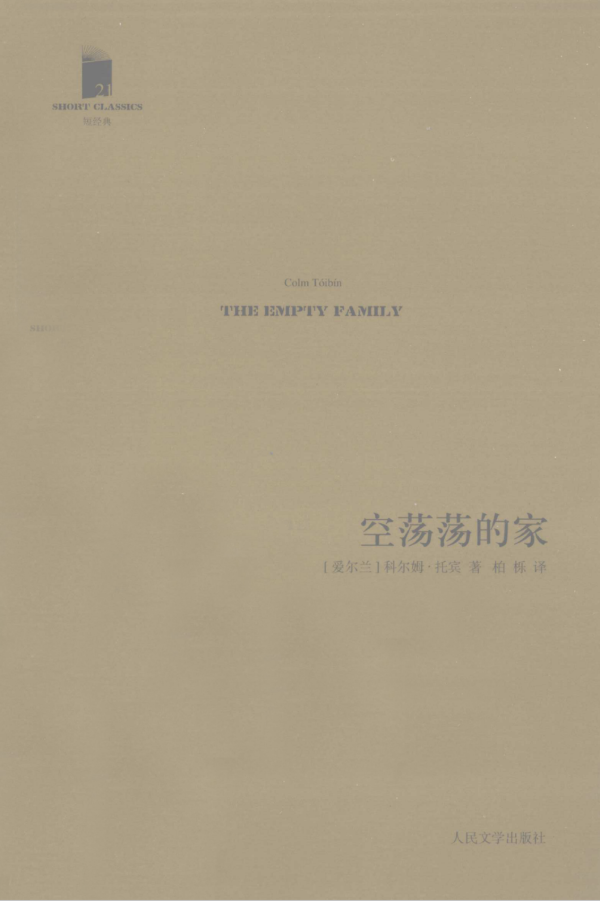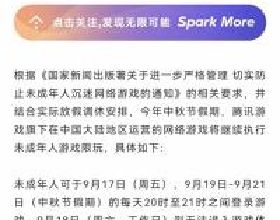柏櫟
2010年夏,我在訪問都柏林的大半個月中,特地去了一趟恩尼斯科西。當時我正在翻譯《布魯克林》,小說的開篇就在描寫恩尼斯科西的街景,那是女主人公艾麗絲的老家。
對託賓的粉絲來說,恩尼斯科西乃至整個愛爾蘭東南角的威克斯福德郡,遍佈著熟悉的地名。小鎮往東大約十九公里就到海濱,那裡的黑水村,是《黑水燈塔船》的發生地,海倫和德克蘭曾在附近的巴利瓦羅村散步,參觀燈塔船。再往南六七公里,是克拉克勞海濱浴場,東海岸最好的沙灘之一,艾麗絲和喬治曾在海中游泳,而他們漫步沙灘時聊到的古虛的度假屋,原屬於《諾拉·韋伯斯特》的女主人公諾拉。那部小說的開篇,便是諾拉在一個風雨天從恩尼斯科西駕車前往古虛,去收拾房子。而同一棟房子,也出現在短篇小說《空蕩蕩的家》中:
家就是這個位於巴里肯尼加的懸崖背後的空蕩蕩的房子……夜氣晴朗時,我站在陽臺上舉頭看星星,望見羅斯萊爾港口的燈火,圖斯卡礁燈塔一閃一滅的光,還有夜幕與暗色大海交融的那條淡淡的線,望之令人心安。
威克斯福德郡的海濱、沙灘、燈塔、礁石,還有那棟山崖上被海風侵蝕的度假屋,是託賓童年時代的記憶,並在他的作品中不時地出現。這些小村彼此相隔不遠,然而要去探訪並不容易,那裡不是聞名的旅遊勝地,沒有便捷的公交接駁和散客服務,如果無法自駕,就只能依靠班次很少的公交車,極為耗時,所以我那次的目的地只能是恩尼斯科西。
恩尼斯科西是個大鎮,往返都柏林的火車很多,在康諾利車站的自助購票機上買一張票,跳上下一班車,可以說走就走。切記,在南下的火車上,要坐左側靠窗的位置,以便一覽沿海風光,回程則是坐右側。
車程約兩小時,鐵軌遠遠地離開海岸線,在滿目蔥綠中行進,讓你積攢小小的興奮,卻不至於忍不住喊出聲來。唯有從威克洛到戈裡的這段,火車緊貼海岸線,不時地鑽入隧道,一側是懸崖峭壁。透過車窗往下望,暗色的礫石灘上翻湧雪白的浪花。這時你能感到,愛爾蘭的東海岸並不溫柔,它險峻,突兀,犬牙交錯,如果天氣不好,甚至透出幾分猙獰。若干年後,當我翻譯《諾拉·韋伯斯特》,我驚喜地發現託賓並沒有放過這段峭壁上的火車之旅:
這是一個無風的上午,地平線上壓著灰濛濛的雲,威克洛鎮外的海一色的鉛灰。……火車鑽出隧道時,他靠近視窗,峭壁下面是起伏的波濤。
但你要想領略海岸的精髓,得找個地方下車,漫步到海灘。距離都柏林不遠的鄧萊裡,都柏林灣的南岸,火車下來便看到密密麻麻的帆船泊在港口。若要避開人群,往北稍稍步行一段就到海灘。這邊的海灘並非羅斯萊爾那種度假沙灘,而是粗砂或礫石灘。那次我無意間逛過去,在海灘上坐了好一會兒,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幾隻海鷗不時落下來休息。那裡佔據視野的,是不知疲倦地衝刷岸石的海浪,以及遺留在海灘上,不知何時會被再次捲走的小石頭。我想,東南海岸有著太多類似的景象,隨便翻開託賓的一本與威克斯福德郡有關的小說,都能輕易找到這樣的描寫:
這一片幾乎沒有色彩。她眼前的世界已被沖刷乾淨。如果走近岸邊,會瞧見一些小石頭,浪花在石頭上碎開,發出咯咯的聲響。每一粒石頭的顏色都是如此真切。(《諾拉·韋伯斯特》)
再如:
她想知道從這裡到巴里肯尼加之間的海灘上散佈的小石頭是從哪裡來的。從陸地上還是從海里?它們會不會深嵌在那構築懸崖表面的淤泥和泥灰之中?(《黑水燈塔船》)
這些小石頭,似乎曾是託賓與家鄉的海溝通的一箇中介。它們擁有可無限遐想的過往和未來,在《空蕩蕩的家》中,第一人稱的主人公寓居舊金山,每月開車前往雷耶斯,只因為那裡的海岸景觀與恩尼斯科西的相仿。他從雷耶斯撿了幾塊石頭,想要帶回愛爾蘭,放在親人的墳墓上,並由此產生了一番奇想:
將來如果有考古學家來到這些墳墓,會研究遺骨和周圍的泥土,也會為這些流浪石頭寫篇論文。這些石頭是被太平洋的波濤沖刷過的。這位考古學家會推想那是何等瘋狂,何種動機,又是怎樣一份柔情讓人把這些石頭大老遠運來。
在鄧萊裡的那個下午,我在海灘上搜尋託賓筆下的那一類小石頭,那鐫刻著他深切的思鄉之情,記載著海岸變遷資訊的石頭。他曾這樣細緻地描寫其中一塊:
我注意到這塊石頭是因為它在沙子的襯托下顏色細緻,淺綠底色上分佈著白色脈絡。在我看到的所有石頭裡,這塊似乎承載了最多海浪衝刷的資訊,它的色彩被水淡化後更為生動,彷彿色彩和鹹水之間的戰役,賦予它無言的堅強。
也許這種“無言的堅強”、在時間中的堅守,也像是歷史賦予小鎮的遺產。託賓為他父親邁克爾的隨筆集《恩尼斯科西:歷史與遺產》撰寫的前言中提到的:“無論在哪你都能注意到變化,但到處還是舊日的感覺。” 恩尼斯科西火車站位於鎮子東側,走出車站就能看到斯蘭尼河,這條穿鎮而過、南向蜿蜒到威克斯福德出海的長河,泛著柔和的波光,平靜地流淌。它也多次出現在託賓的筆下,幾乎所有寫到恩尼斯科西的篇章中,都少不了斯蘭尼河的身影。
同樣令我有似曾相識感的是河對岸的恩尼斯科西堡。這是一所始建於十二世紀的古堡,後世幾經諾曼人和英國人的修建,至今維持了十六世紀的面貌。託賓說,“很難想象還有另一個建築能有恩尼斯科西堡這樣敦實、堅毅的外形”。古堡與託賓家族關係密切。上世紀六十年代,託賓的父親與約瑟夫·蘭森神父合資購買了古堡,並將它改為博物館。當時託賓只有六七歲,他至今記得古堡前面原有一道十九世紀的古牆,但為了修博物館的緣故,被拆除了。開掘古堡內部的地牢時,他也在場,他迄今記得那股潮溼腐敗的氣息,以及囚徒在牆上的塗鴉。當博物館向鎮民徵集藏品時,人們踴躍奉獻有歷史價值的祖傳寶貝,最後開闢了1789年與1916年兩個展廳,陳列小鎮的英勇抗英史。我在去恩尼斯科西之前久聞古堡大名,但不巧的是,那年夏季古堡內部維修,關門謝客,我只得在外環繞一圈,算是打卡託賓筆下的勝地。
從古堡腳下,或是小鎮任何一處開闊的地方,都能望見河東的醋山。這座百米多高的小山丘,記載了一段驚心動魄的“醋山之戰”。1798年夏,武器和兵力都佔優勢的英軍對恩尼斯科西的愛爾蘭起義軍發起圍剿,這場戰鬥成為威克斯福德起義的決定性一戰,最終起義軍退到醋山上並以失敗告終。在之後數百年的歷史中,“醋山之戰”被一再重述和定義,“比愛爾蘭歷史上任何一起其他事件都更有爭議性,它可以被解釋為一種情況,也可以被解釋為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情況”(《恩尼斯科西:歷史與遺產》前言)。比如在1898年,主流說法是這是一場芬尼亞兄弟會領導的、驅逐英國勢力的起義鬥爭。一百年後,重點成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一次聯合抗爭,顯然這受到當時北愛與歐盟的合約影響。也許這就是歷史的作用,它將意義和迴響賦予當下的議題。
我在造訪恩尼斯科西之前,和託賓通了一次電郵,提到想去醋山看看。託賓不是很建議我去,說步行過去路途遙遠。我喜歡徒步,覺得幾公里的步行不算什麼。於是那天下午,逛完小鎮後就去攀登醋山。在山腳下,我經過一棟棟白色的房子,那些房子的窗臺上都點綴著盆栽和飾品,看得出是專門為了路人一飽眼福而佈置,鐵藝窗臺也各不相同。相比小鎮中心略顯密集的住宅,這裡更能讓我感受到多處小說場景中的在時間的流逝中幾乎一成不變的安穩生活。步行大約四十分鐘登上山頂。那裡留下的不多的戰爭痕跡,是在起義期間被改成臨時監獄的半截磨坊,以及岩石上據說是英軍留下的彈孔。這處歷史遺產,顯然早已成為當地居民的休閒去處,一位母親帶著兩個女兒和狗過來散步,一對老夫妻也攜手爬山健步。坐在山頂的長椅上,整個小鎮一覽無遺,遠處的山坡上有青色與金色相雜的麥田,和鋪到地平線的黛色的灌木林。無論以前發生過什麼,幾乎都被自然所遮蓋,歷史的意義和細節,大概只能在博物館和圖書館中查詢。
鎮上有一家1798年的遺產博物館和鎮圖書館。博物館按時間順序串聯了本地上啟古希臘羅馬時代,下至1798年起義的抗爭暴力統治事件,似乎刻意為威克斯福德郡梳理一條清晰的脈絡,並將恩尼斯科西置於中心。這也許也是小鎮居民共同記憶的一部分,經歷過歷史的老一輩將他們的故事代代相傳,抵抗主流話語的權威,為他們的立場和視角留下一隅陣地。託賓在其回憶錄《盛宴上的來賓》中提到,幼時他父親帶他經過恩尼斯科西附近的圖拉鎮,就會指著一家店說,店主的祖輩背叛過義軍,你永遠都不能踏進這家店。
鎮圖書館則比博物館的氛圍輕鬆很多,那裡很像是為鎮上的孩子辦的休閒閱讀中心。英俊的圖書管理員友好地接待了我,問明來意後,遺憾地說他們只有託賓的幾部最新的小說,但沒有任何研究資料。走出圖書館是落日時分,回到鎮中心車流密集的集市廣場,感到一種忙碌的暖意,似乎現代生活又部分取代了我從小說中得到的印象——那裡的主人公總是在廣場周圍來來去去,敏感地留心著周圍人的反應。艾麗絲曾經居住的弗萊瑞街就是廣場西側的上坡路。是的,只要你願意,你可以將託賓筆下恩尼斯科西所有的大街小巷都走一遍,他寫到的每一條路都是真實存在的,他寫過的建築物也都真實存在,甚至他的人物都彼此呼應,從這部書到那部書,原型都來自於小鎮居民,他們構成了一個現實與想象並存的世界。那是一個如此緊密地浸潤著人情的小世界。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