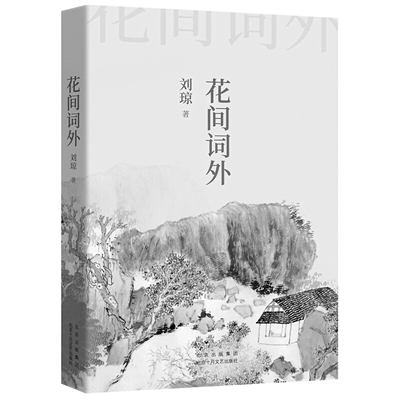與劉瓊相識經年,她是資深的媒體同行前輩,也是活躍的文藝評論家,曾多次在研討會上聆聽她對作品的見解;而在工作之外,我們還有一層特殊的關係——花友。她曾開車載我一同去花市“尋花問柳”,兩個愛花人逡巡花間,滿心歡喜,滿載而歸。我還記得有老大一盆月季,喚作“小女孩”的,開滿了正紅色的嬌俏花朵,後來擺在了她辦公室的陽臺上。另有一次,一同往溫州出差,住宿的酒店就在甌江畔,飯後相約江邊散步,恰是金桂飄香時節,空氣中馥郁的甜香令人愉悅流連。劉瓊是皖人,我是鄂人,共飲長江水,長江中下游區域有著相近的自然氣候條件,我們便有了相似的對於花草樹木的記憶,譬如,桂花香就頑固在我們的童年記憶中。我和劉瓊均輾轉南北,最後都定居北京。桂樹是典型的南方佳木,抗不住北方的大風大寒。每年秋天,桂花香是我們共同的鄉愁。
在《花間詞外》這本以“花間”為關鍵詞的書中,劉瓊當然會寫到桂——悠悠歲月,桂香幽幽,幾千年來,飄散在嫦娥玉兔的廣寒宮,飄散在唐代白居易,宋代楊萬里、趙長卿等人的詩詞裡,飄散在郁達夫的小說中,也縈繞在中國人的舌尖——作者看似閒筆一蕩,“沒有桂花的藕粉,杭州人是不吃的”,由花的審美價值一下子過渡到了食用價值,然而,這實用也依然是帶著審美的實用,這便是中國式的“色、香、味”的生活。
劉瓊寫桂、寫荷,也寫梅、蘭、竹、菊,寫槐、桑、梓、桐,寫桃花、海棠、櫻桃、石榴、柿子,寫杜鵑、丁香、水仙,甚至也寫平平無奇的薺菜花,端的是一部“植物裡的中國”。——何以說是“中國”?嚴格說來,這些植物非但不是中國獨有,甚至有些原產地也並非中國,然而,它們卻又是那麼“中國”,從古至今,陪伴著中國人的生活,是最為習見的花木。它們連線著悠久中華文明的前端,比如,“桂花在中國的栽培史長達兩千五百餘年,《呂氏春秋》盛讚其為‘物之美者,招搖之桂’”。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不僅構成了中國人生存的自然環境、日常生活中的“風景”,而且還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是內蘊豐富的文化符號。
劉瓊此書的重點顯然不在對花木物質層面的考量,植物的形態、分類、分佈等資訊間或一筆帶過——“把巖桂和桂花區別對待是這些年植物學界的事。我自己倒是一直不分。這是沿襲老習慣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一個“桂”字,其內涵早已溢位了自然科學的分類、歸屬與命名,上升為美學。在中國古人那裡,這些花草樹木很早就成為審美的客體,尤其是作者在本書中所寫及的植物,幾乎都是高度美學化的,在這一過程中,文人墨客無疑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說,《神農本草經》和《本草綱目》等致力於發掘草木的食用、藥用等實用功能,發展中國的醫藥科學,那麼,古代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則在詩文畫作中不斷建構著中國的植物美學。他們投注在花木上的,不僅有其獨特審美情調與趣味,更有人格精神與生命意志,一如陶淵明之於菊,周敦頤之於蓮,王安石、范成大之於梅,李清照之於海棠,李商隱與近代戴望舒之於丁香……中國文人給我們提供的“植物濾鏡”,歸根結底是中華美學精神。
劉瓊五歲便在長滿植物的院子裡背誦古典詩詞,接受中國文化的啟蒙;大學念中文系,碩士階段研究中國現代詩歌,博士又讀了藝術學專業;所從事的工作為她提供了周遊各地開闊眼界的便利,同時,她又是一位細膩的、愛美愛生活的女性。有這樣的履歷、修養和主客觀條件,她堪稱是一個理想的審美主體,面對審美客體時,便很難做到如胡塞爾所言的“面向事物本身”,她觀賞花木的那雙眼睛,戴著“中華美學”的濾鏡。
美學不只是要簡單地區分感觀意義上的“美”“醜”,還包含歷史、時代、政治、經濟、道德、民族、人性的內容,絕非未經文化浸染者“直面事物本身”所能達致的。《春入平原薺菜花》篇,寫到薺菜是“中年開花”,此乃物種的生物屬性,當“薺菜花”作為一種審美物件被書寫時,便投射了詩人的中年況味:“人到中年的詞人,閱歷多樣,透過似錦桃李,看到薺菜花樸素到近乎塵埃的容顏和繁榮的生機。”
作者捕捉到審美的主客體之間的交會。在此之上,作者細緻對讀了辛棄疾吟詠薺菜花的兩首詞,近乎相同的鄉間景物,然而其間情感卻有微妙的差別:“春在溪頭薺菜花”闋,不免著上了詩人人到中年壯志未酬的感傷色彩,是降調;而稍晚的“春入平原薺菜花”闋,則洋溢著飽滿的生活樂趣,流露中年的閒適、淡然與圓熟之感,是升調。“審美主體在不同的情境下欣賞植物或花卉,代入不同時期的主觀感受,植物或花卉便具有了不同的形象。”能從語言和形象上感知如此細微的情感和差異,知人論詩,這才算是高階的審美吧。在鑑賞之外,作者也敢於下判斷,如評價齊白石的畫:“老爺子畫中秋,蝦和蟹都很精彩,配菊花,菊花沒精打采,差了點意思。”
本書內容一如書名所蘊含的,不僅有“花間”,有“詞”,還有“詞外”。如《蘭生幽谷無人識》篇,明明寫著蘭花,不經意間轉到映山紅,再轉到電影《閃閃的紅星》(電影插曲《映山紅》),穿插童年的回憶,《越絕書》“勾踐種蘭渚山”的記載,紹興棠棣“蘭花村”的蘭花產業,畫蘭的友人,胡適的小詩《希望》和據此譜曲的流行歌《蘭花草》……看似信馬由韁,意念騰挪,移步換景,然而可真是“形散神不散”。所謂“神”,一直都被作者緊拽在手裡:“蘭花品相素雅,符合中國古典審美標準。古典的美,追求有內涵和韻致的低調的美,或者叫簡約、樸素的美。”“美來自自然,美來自單純。”
可以說,《花間詞外》是一本形象生動解析中華美學精神的散文,如《落梅橫笛已三更》篇,由納蘭性德的詞引出古典詩詞的“意”“境”與“象”;由李白與李賀的風格對照,引出“中國藝術強調生命精神,即主體投射的必要性”;最後回到清代佳公子納蘭性德,指出他吸引人處,“無非是深情和優美”。這樣的書寫方式,本身就是深受中華美學浸潤的,如行雲流水,鬆弛自如,也有刻意的留白餘味與“詞外”之意。
沈從文曾將寫作區分為“事功”與“有情”,提出:“事功可以為學,有情則難知。”在他看來,成熟的書寫“不僅僅是積學而來”,而且“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別的東西”,亦即“情”,“這個情即深入領會的,深摯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由此觀之,《花間詞外》當是作者的一部“有情”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