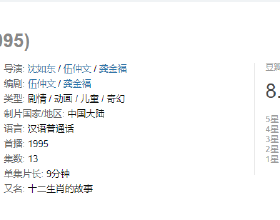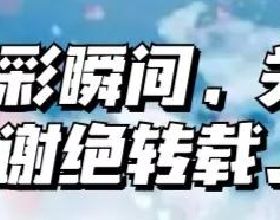“生活不是電影,生活比電影苦。”
在電影《天堂電影院》之中,阿爾弗雷德曾對多多說過這樣的話。面對生活,梵高在給提奧的信裡提出了他的觀點:“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種無限的、深刻的、真實的東西,我不再眷戀人間……”而在上個世紀學海波瀾的文壇裡,曾有一個人這樣說道:
“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世界先愛了我,我不能不愛它。”
說到此處,你可能不能馬上想到他的名字,但你一定聽過“人走茶涼”的詞句,一定見過冬日裡“家人閒坐,燈火可親”的盛景。他用他的文字,他的一生告訴了所有的讀者:生活是很好玩的。筆者第一次讀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只覺得平實自然,像是一位親厚的長者坐於你的身旁,將一切有趣的小事向你娓娓道來。而後多次捧起汪老的書,但覺如品一壺美酒,愈慢愈能品其真味,愈久愈覺其中香醇。
讀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門檻是很低的。譬如他的小說《受戒》:
“明海出家已經四年了……”只是第一句話,平平白白,不加任何修飾。簡單到極致的文字,任何一個國人都能聽懂。但就是這樣的文字,寫出了一個簡單美好的愛情故事,寫出了一個亂世中的“世外桃源”。無論是天真爛漫的小英子,還是情竇初開的明海,汪老的筆觸始終是自然的,自然地塑造出了鮮活的人性。
“英子跳到中艙,兩隻槳飛快地划起來,划進了蘆花蕩。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 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 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隻青樁(一種 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
讀到此處,沒有一個人不說美的。我們或許曾震撼於稼軒詞中“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的萬丈豪情之美,或許曾驚歎於王勃筆下“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匠心獨運之美,但讀了汪老的文字之後我們才發現:
那種充滿人世煙火的文章,同樣可以美得動人心魄。
他寫夏天,“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寫梨花,“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寫昆明的火炭楊梅,“極大極甜,顏色黑紫,正如熾碳”。他自創的塞餡回鍋油條,更是好吃到“嚼之真可聲動十里人”。
汪老用他的作品,真切地告訴我們何為“文字的力量”——不事雕琢卻成就了渾然天成的美感。
在《人間詞話》第四十篇中,王國維提到了兩個關於詩詞的概念:“隔”與“不隔”。
“陶謝之詩不隔,延年之詩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
筆者以為這兩個概念同樣可以解釋汪曾祺先生文字的魅力所在:最直白,最易懂,也最直擊人心,最能引人共鳴。汪老的文字是“不隔”的,正是那種與讀者間無甚距離的交流才能傳遞最為真摯的感情,也正因此汪老的文字才能驚豔了一代又一代的國人。
汪曾祺先生曾作《小說筆談》,無疑是他自己對語言文字的畢生追求所在:
“語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記住。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
也正因此,這個老人的一生都在給自己和自己的文字做減法。
從早年作品中對各種風格的探索,到晚年作品裡乾脆簡潔的語言,如同一位有心的園藝家將一樹寒梅剪去多餘的枝丫,只留下令人動容的風骨與佳韻。在汪老的筆下,語言擁有了更大的自由性:
“夏天一地濃蔭,秋天滿株黃柿。”
“羅漢堂外面,有兩棵很大的白果樹,有幾百年了。夏天,一地濃蔭,冬天,滿階黃葉。”
“他不咳嗽,不腰疼,結結實實,像一棵榆樹。”
這樣的文字,平淡卻也奇絕。如一泓清泉,浸潤了每個讀者的心。
汪老一生命途多舛,受過許多不公正的待遇,即便如此,他依舊微笑著告訴所有的人:
“生活是很好玩的。”
闊達樂觀如汪老,在他的文章裡寫盡了人世煙火。
他“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
他愛吃,愛玩,愛看,會因為孩童無心一句“汪伯伯能把難吃的黃豆燒好吃”而志得意滿。
他不屑於作宏大文章,選擇“寧作我”。
在汪老的筆下,有“吱”一聲冒出紅油的鴨蛋,有“竹酒一杯天過午,木香花溼雨沉沉”的景緻;有糖炒栗子,淮揚早茶,四時的美味都有;有叫賣聲,鍋碗瓢盆聲,也有鐘鼓之聲。兼具生活的詩意與情意,恰是汪老一生的浪漫所在。
如果有一天,你疲憊于都市的繁忙生活;如果有一天,你不可避免地思念起某個溫暖的地方。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想走進一個小巷,去吃一碗餛飩,尋一枝花,見一個人。
請不妨去讀一讀汪曾祺。
恰如汪老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