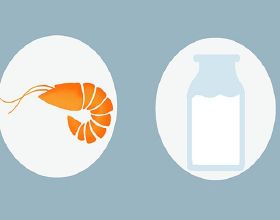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賴星
1931年11月7日,她伴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而降生。從誕生之日起,她便為黨而歌,與人民同行。
她是新華通訊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在中央蘇區,新華社的先輩們譜寫了她慷慨悲壯的紅色序章,其中滿是激揚的文字、奔騰的熱血和不滅的信仰。
90年的時光賦予了她深沉持久的力量,從而描繪出中華大地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記錄紛繁變化的時代風雲,銘刻中國人民刻骨銘心的共同記憶,讓人們得以深情回望歷史,自信走向遠方。
這是新華通訊社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新華社記者周科攝
筆墨勁旅青春激揚
1931年11月7日,一場上萬人參加的提燈晚會在江西瑞金舉行,演戲、放煙火,很是熱鬧。
此時,山外的世界,愈加動盪。美國大蕭條波及全球,國際關係日益惡化,日本加緊對華侵略……當時的人們或許並沒有意識到,贛南山村的一角將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變遷。
就在那天夜裡,從瑞金的崇山峻嶺之間,發出了一條歷史性特大新聞——“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釋出這條新聞的就是紅色中華通訊社。從此,新華社作為黨中央直接領導的新聞機構,成為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紅中社成立一個月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創刊。“報與社是一回事,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曾任紅中社負責人的王觀瀾生前回憶說。
若稍加翻看下這一時期紅中社工作人員的履歷,就會不禁感慨,這是何等的朝氣蓬勃又才華橫溢。以瑞金時期紅中社的7名負責人為例,他們任職時平均年齡只有30歲。其中,周以慄34歲、王觀瀾25歲、梁柏臺33歲、李一氓29歲、楊尚昆26歲、沙可夫30歲、瞿秋白35歲,幾乎每個人都有傳奇般的經歷。
周以慄畢業於長沙師範學校,教過書、搞過農民運動,曾協助毛澤東創辦中央農運講習所,還參加過武裝起義。1930年秋,他帶著一身的傷病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不久前,經黨組織營救,他被國民黨釋放出獄。在獄中,他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遍體是燒烙的傷痕。
來到瑞金後,周以慄除了擔任過紅中社負責人外,還擔任過臨時中央政府內務人民委員、紅軍總前委組織部長等職。他還是《紅色中華》第一任主筆,報紙最初的報頭就是由他所寫。
李一氓24歲時曾參加南昌起義,曾任南昌起義參謀團秘書長,還曾在上海從事黨的保衛工作,自然是能文能武。瞿秋白則更加為人熟知,他曾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知識淵博,論文著書,倚馬可待。
戰爭環境下的紅中社並沒有完全穩定的班子和團隊,人員也並非新聞科班出身,很少有人辦過報,寫過新聞稿。即便如此,紅中社依然堪稱筆墨勁旅。編輯部人員除採訪、寫稿、譯電外,還兼刻蠟紙和校對,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
李一氓住在瑞金城,與編輯部所在地相距十里。每週六下午,他從瑞金城騎馬到葉坪村,利用中央政府大廳做編寫工作,晚上則隨便找個地方過夜。第二天吃完午飯,發了稿,他又騎馬回城。
編輯部位於一棟普通的客家茅屋內,整個房屋佔地面積不足200平方米。“條件簡陋到只有幾張桌子,組稿、寫稿、編稿、校對,我們都是一肩挑,什麼都幹。”此後擔任紅中社秘書長的任質斌當時只有16歲,他記得當年雖然辦公條件簡陋,但大家夜以繼日工作,雖然很累但心情舒暢。
在《紅色中華》百期紀念時,當時的領導同志特別提出:《紅色中華》向困難作頑強鬥爭的精神,值得全蘇區的黨政工作同志學習!
這是紅中社舊址內當年《紅色中華》報編委會的辦公室。新華社資料片
人民喉舌喚醒工農
是什麼力量讓百姓鐵了心跟黨走?答案,或許就寫在紅中社的一篇篇報道中。蘇區的讀者親切地讚譽《紅色中華》是“我們蘇維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現”“全蘇人民的喉舌”。
“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憲法大綱明確揭示——人民,是這個紅色政權真正的主人。
千百年來,在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從未發生如此新奇的變化。底層群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土地,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婦女翻身解放,兒童實行義務教育,全體蘇區人民享受民主權利。
根據《紅色中華》1932年2月17日刊載的一篇報道:“蘇維埃選舉運動,這一個運動的實質,是改造各級蘇維埃,建立強有工作能力的蘇維埃政權,來領導和執行目前革命鬥爭的任務,決不是一個普通的選舉運動。”
經過不斷改進,蘇區選舉工作日臻完善。1934年1月1日,《紅色中華》第139期刊發了梁柏臺寫的文章《今年選舉的初步總結》,認為這年的選舉宣傳動員工作明顯改善,選民登記普遍進行,吸收了最廣大的群眾,婦女代表佔了很高的比重,群眾的提案也是這次選舉的一大亮點。
這些提案涉及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消除市面現洋與紙幣的差異現象、修理道路橋樑、設俱樂部列寧小學等問題。“由這些提案中可以反映出群眾的要求,使蘇維埃在日常工作中更加註意完成這些提案。”梁柏臺在文章中寫道。
當年,群眾不識字、無文化是一個普遍現象。因此,加強文化建設,提升蘇區軍民文化水平的問題擺到了特別重要的位置,這也成為紅中社報道的一大領域。
《紅色中華》第122期刊發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兩週年紀念對全體選民的工作報告書》。《報告書》深刻指出,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工農群眾才有受教育的權利與可能。一年來蘇維埃對於文化教育事業已在著力的進行。小學、夜校、識字運動與俱樂部運動,已在各地廣泛發展起來了。
戰爭環境下,蘇區想方設法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1931年11月之後,蘇區幾乎村村都辦起了列寧小學。師資不夠,就開展師範培訓教育;沒有校舍,就把祠堂騰出來;沒有課桌板凳,就用門板和磚頭搭起臺子;組織人員專門編寫列寧小學課本。
為了改進報道,《紅色中華》在創刊一週年之際專門發表了一篇業務文章《本報一週年的自我批評》,其中寫道:“我們覺得‘讀者通訊’是要開始建立起來的,儘量的發表蘇區中工農勞苦群眾的意見,他才可以真的成為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報紙。”
經過各方面的努力,《紅色中華》成為中央蘇區發行量最大、影響面最廣的報紙。“它的發行,由幾百幾千而突破了三萬,走向著四萬,是一個群眾化而得到群眾愛護的報紙。”那時,鄧穎超是《紅色中華》的熱心讀者,也是一名活躍的撰稿人,為了慶祝“紅中”百期刊,她寫下了《把“紅中”活躍飛舞到全中國》的祝願。
胸懷世界志存高遠
即使是在中央蘇區,黨中央和紅軍的日子依然過得緊巴巴,他們為此專門透過《紅色中華》號召要節省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儘量減少,尤其紙張信套,更可以節省使用。”
雖然地處偏僻的小山村,生活工作環境艱苦,紅中社這批青年卻胸懷世界,志存高遠。他們在《紅色中華》上開設了《國際風雲》《世界零訊》《國際時事》等欄目,幾乎每期都刊載國際新聞。
在國際報道中,《紅色中華》較多轉載塔斯社、路透社等國外通訊社稿件,內容多關乎莫斯科、倫敦、華盛頓這三大資訊中心,可以讓蘇區的讀者瞭解到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
“巴黎城各大街,除百貨商店飯店雜貨鋪肉鋪外,其餘都閉門停業。晚間各商店的電燈,大半熄滅,素來稱為不夜城的巴黎這次卻變成了一個寂寞的都市,呈露著黯淡蕭條的景象。”從《紅色中華》第59期的報道,我們能看到1933年初巴黎街頭的大致景象。
蘇聯,則是《紅色中華》關注最多的國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當時,蘇聯誕生不過十餘年。紅中社以極高的熱情,好奇地打量著這個既親切又遙遠國度的一舉一動。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自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建立了國家工業化的強固基礎,第二個五年計劃,更注意於國家電氣化一項,最近蘇聯人民委員會頒發關於建立水電工程的命令。”《紅色中華》以欣喜的口吻報道了蘇聯取得的各項經濟成就,尤其是工業生產的飛速發展,並向讀者表示這是“在勝利中前進著的蘇聯”。
在戰爭環境下,紅中社還把革命樂觀主義與浪漫主義展現得淋漓盡致。1934年1月22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沙洲壩開幕。會議期間,蘇區舉辦了各種各樣的體育比賽、歌舞晚會。紅中社記者對大會代表的生活進行了細緻觀察,在記者眼裡,香樟下喜慶的歌舞,田野中湧動的綠浪,一切都散發著新生的氣象。
兩天後,《紅色中華》刊登了特寫《一個精彩的晚會》,講述22日夜晚參會代表和各機關觀眾三千多人觀看演出的情景。當晚的演出“大腕”雲集,報道中說:“這幾個要角是全蘇有名的明星,表演極為努力,特別是王燊、李克農兩大滑稽博士,一舉一動,一聲一笑,無不令人捧腹絕倒。”
是什麼樣的信念,讓紅中社的這群青年們在缺衣少食的日子裡,依然懷揣夢想,暢想詩和遠方?1934年2月3日的《紅色中華》上,一篇署名朱華的稿件給出了答案:我們的心完全一樣,我們共同娛樂,共同生活,共同戰鬥,共同勝利,共同爭取全中國的解放!
熱血鑄魂信仰如磐
1934年秋,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準備戰略轉移。10月3日那天,紅中社就停止了新聞廣播及對外發稿,開始踏上征途。
此時的周以慄,已重病纏身。他不能隨大部隊行動,黨組織決定安排他去上海治病。1934年11月,陳毅派出一個班的部隊護送他與其他幹部,從江西于都出發。
一天夜裡,他們休息時,突遭敵人包圍。周以慄在突圍時壯烈犧牲,時年37歲,他是新華社為中國革命戰爭英勇捐軀的第一位烈士。
很快,中央蘇區也陷入絕境。從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蘇區在三個月內幾乎全部淪陷,許多村莊被殺絕戶。在這樣的危急關頭,瞿秋白依然領導著韓進等少數幾個人組成的編輯部留在了蘇區。
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怎麼保住性命,而是如何繼續出版發行《紅色中華》。他們堅持四個月之久,共發行24期《紅色中華》。
為了給敵人制造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沒有轉移的假象,《紅色中華》版式不變,期號延續,繼續宣傳擴紅、徵糧。那時,編輯部轉移到了于都縣黃麟鄉井塘村,報紙的印刷則在會昌縣白鵝鄉梓坑村的深山密林中,兩地相距約20華里。
在韓進的回憶中,這一時期的《紅色中華》最初堅持每週出版三期,後來由於環境惡化,每週兩期,最後不得不一週一期。
歷史細處不忍卒讀,一旦翻開,可能每一個字都帶著血痕。
在今天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珍藏著一張被燒燬的報紙殘頁。這是目前所能發現的瞿秋白在蘇區出版的最後一期《紅色中華》,為1935年1月21日第264期報紙。
1935年1月,瞿秋白的肺病癒加嚴重,《紅色中華》被迫停刊。在向閩西突圍的路上,他不幸被捕。福建長汀羅漢嶺下白露蒼茫,瞿秋白唱著《國際歌》坦然走向刑場,盤腿坐下,飲彈灑血,慷慨就義。
1935年,是中國共產黨新聞史上、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悲壯的一年。
曾任《紅色中華》代理主筆的梁柏臺,和瞿秋白同年生人,同年被捕,同年犧牲;23歲的紅中社秘書長徐名正跟隨瞿秋白行動,也在1935年2月突圍途中被捕,在長汀英勇捐軀,時年23歲……這是黨的新聞工作者對黨無比忠誠的生動寫照,他們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堅守本身就是一種信仰。
新華社老社長郭超人曾言:“在革命的歷史長河中,新聞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新聞記者就是革命戰士……在革命戰爭年代,新聞工作,絕不是一種單純的職業,更不是一種謀求個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是為人民、為民族解放的神聖革命途徑。”
新華社的先輩們所樹立的歷史豐碑,不僅由於他們用自己的鮮血浸染而輝煌燦爛,更由於他們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永世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