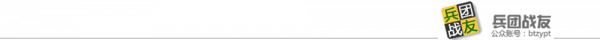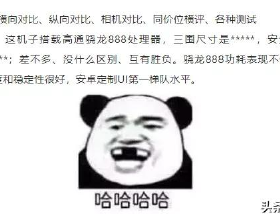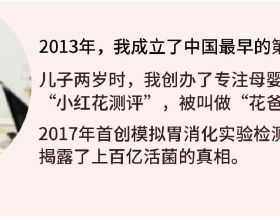Original 劉佔龍 兵團戰友
網路配圖 與文無關
“憶苦思甜”背後的故事
—— 還原一樁歷史公案
劉佔龍
“文化大革命”中,我參加過很多次由各級組織召開的“憶苦思甜”大會,聽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農民以及街道老大媽懷著滿腔怒火、滿腹悲痛,憤怒地控訴黑暗的舊社會,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人們受盡了屈辱和剝削,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牛馬不如的生活,遭受過無窮無盡地苦難;熱情地謳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人們當家做主,過上了無憂無慮、吃得飽穿得暖、幸福美滿的新生活。在一波又一波驚天動地、排山倒海“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倒地、富、反、壞、右!”的口號聲中,我一次次不知流過多少同情的淚水。
隨著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更迭,時代的變遷,這些形式雷同,內容大同小異的“憶苦思甜”大會,多年來早就被其它的資訊一次又一次的覆蓋了。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別開生面的“憶苦思甜”大會至今還記憶猶新,令人沒齒難忘。
那次會上,沒有一般會議上標配的“憶苦思甜大會”橫幅,沒有花花綠綠的標語,也沒有人義憤填膺慷慨激昂的領著呼口號。人不多,男女老少都算上,大概也只有四、五十人。但是,對於我來說,那是一次真正觸及靈魂的大會。
那是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在老家——山西省晉中市一個小村子的大隊部參加的“憶苦思甜”大會。
我是六六屆小學畢業生。“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還時不時地去趟學校,後來“停課鬧革命”,就不去學校了。“革命大串聯”開始後,中學生、大學生都投入到熱火朝天的革命大串聯中,天南海北的各地跑,到處“參觀學習”、“煽風點火”,時不時地還有大人物接見一下,既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鼓勵,忙得不亦樂乎。我們這些小學生既沒人接見,更沒人待見,每天沒事可幹,就在街上待著,樂得逍遙,也只能逍遙,一天到晚無非是東遊西竄,招貓逗狗。家裡的大人們今天是“左”,明天是“右”,查歷史,翻舊帳,今天這個單位挖出來一個隱姓埋名的“資本家”,明天那條街上刨出來一個潛伏多年的“反革命”,後天不知又從哪個犄角旮旯抓住一個深藏多年的“國民黨特務”,人人自顧不暇,個個提心吊膽,沒人管也沒心思管我們這些小屁孩的事。
因為沒事可幹,我就在那年的10月底,11月初回了老家。其實回去也沒什麼事,住在姥姥家,幫助撿點柴火,乾點雜活兒。那天村裡開會,我也是閒的難受,無聊的厲害,去湊個熱鬧。
開會的地點就在大隊部。
大隊部在村子主街的南面,路東的一個大院裡,一長溜北房,有六、七間。開會都在靠西面的那間屋裡。這間屋挺大,有四、五十平方米的樣子。房門開在東南角上,西北角有一個能睡兩個人的炕。炕的旁邊生著一個大土爐子,土爐子連著炕,爐火熊熊,烤得屋裡暖暖和和,燒得炕也熱熱乎乎的,靠近土爐子附近的炕都熱的有點燙屁股。這個屋子白天有人辦公,晚上有人值班,一般活動都在這個屋子裡舉行。
屋裡的西面放著一張三屜桌,桌子兩邊各放著一盞馬燈,照得桌子周圍挺亮,其它地方影影綽綽的。有人走動時,就會有一個長長地黑影投到牆上,走動的人多了,牆上的黑影就會晃來晃去,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奇形怪狀,像演皮影戲。桌子後面靠牆放著兩把椅子,算是主席臺。
晚上六點多,隊長用大喇叭通知開會,七點多陸陸續續開始來人,一直到八點,人才到的差不多了。
農村開會不是每個家庭成員都參加,無論什麼性質的會,一般是一家派一個或兩個代表出席就行了,來的絕大部分是男勞力。吃完晚飯,女主人在家要收拾碗筷,照顧小孩,洗洗涮涮,縫縫補補,就不出來了。男人在家多少都有點兒大男子主義,吃完飯,一抹嘴就什麼都不管了,要麼躺著休息,要麼到外面串門,典型的中國傳統家庭的“男主外,女主內”。不過,年輕人不在此列,他們一般是哪兒熱鬧往哪兒湊。
人們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任何人、任何生物都會遵循這個自然法則。農民也一樣。無論老少,一進門先四處踅摸,一是看看開會來了多少人,二是找自己的夥伴。雖說都在一個村,住得近的,時不時的還能見上一面;住的稍遠一點的,可能好長時間也見不上面。借這個開會的機會,有找同學的,有找親戚的,有藉機談事的,更多的人是找朋友聊天,開會是一個和朋友見面的極好機會。
大姑娘小媳婦聚在一起,嘰嘰喳喳的像一群麻雀,別人只能聽到她們的說話聲,聽不清楚她們在嘀咕什麼。說到高興了,時不時地你打我一下,我杵你一下,然後就是一串銀鈴般的笑聲;年輕小夥子湊成一堆,胡吹亂侃,海闊天空,說到一些逸聞趣事,哈哈大笑,旁若無人;中年婦女不多,手裡都拿著活兒,不是納鞋底,就是上鞋幫,沒有閒著的,嘴裡還不停地和旁邊的人叨叨著家裡的、鄰居的一些瑣事。無非是張家長李家短,王家的媳婦沒洗臉,沒什麼新鮮的;中年漢子和老年人,幾乎每個人嘴裡都叼著一支菸袋,一煙鍋接著一煙鍋,吧嗒吧嗒不停的抽著。青煙嫋嫋,冉冉彌散,不一會兒,整個屋裡就煙霧騰騰,濃烈的旱菸味嗆得人直咳嗽。吧嗒一陣兒,就和旁邊的人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兩句,然後再吧嗒一陣兒。
“開會了!”隊長劉柱子大聲地宣佈。人們這才注意到主席臺上已經有人了,一個是劉柱子,站在桌子後面主持會議;一個是公社派來的蹲點幹部,在靠近炕的另一把椅子上坐著。在他面前放著一個開啟的筆記本,旁邊放著一支鋼筆。
那時,每個大隊都有公社派來的蹲點幹部,他們是國家的正式幹部,掙工資,吃派飯,協助生產隊做一些管理工作。因為他們只對上級負責,所以有監管的意思。農民把這些蹲點幹部叫做“工作員”。
這個工作員我認識。那天,我好不容易撿了一捆柴火,扛著往回走,誰知就那麼寸,在進村的路口正好碰到他。他攔住我說,隊裡的柴火不讓撿,要沒收。我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後也沒沒收。不過,我特別恨他。過了幾天,我在親戚家吃飯,正好碰到他在那兒吃派飯(在村裡挨家輪著吃飯,一家一天,吃三頓飯交0.20 — 0.30元,還有規定的糧票。不過,太邋遢的人家就不安排了)。我們互相看著,一天三頓飯,一句話也沒說,特別尷尬。別看每天的伙食不怎麼樣,這傢伙吃的細皮嫩肉的,每天像只狗一樣,在村裡、地裡到處轉悠,不知道在踅摸什麼。
隊長劉柱子大概三十歲左右,身材不高,略瘦,頭上扎著白毛巾,腰裡繫著黑腰帶,挺精幹利索的一個人。由於馬燈上面帶一個鐵罩子,光只能透過玻璃罩平射,人站那兒,只有胸部以下部分是亮的,整個臉黑乎乎的,看不清模樣。宣佈開會後,屋裡說話的聲音一下子小了許多,只能偶爾聽到小孩子的叫聲和中年婦女納鞋底拽麻繩時“刺啦”、“刺啦”的響聲。
“今天開憶苦思甜會,下面讓給地主劉建扛了二十多年活兒的老長工給咱們說說舊社會受的苦。”隊長沒有開場白,也不拖泥帶水,一上來就開門見山,直奔主題。接著補充道:“他有老寒腿,別上臺來了,就在原地說吧。”
隊長說完,在我右後面緩緩地站起來一位老爺子。由於燈光比較暗,只能看到一張黝黑的臉。老爺子咳嗽了兩下,清了清嗓子,像背書似的:“我們家是幾代的貧農,解放前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我從十幾歲就給地主劉建家當長工,一直幹了二十多年,吃的是豬狗食,乾的是牛馬活兒。”說到這兒,老爺子停頓了下來,咳嗽了兩聲,嘴裡吃力地囁嚅著。本來是右手拿著菸袋,只見他把菸袋一會兒別到腰帶上,一會兒又拿下來,一會兒又別到腰帶上,雙手使勁搓著,不知怎麼辦才好。雖然黑燈瞎火的看不清臉上的表情,但從他手足無措的樣子,你肯定會猜到,他的臉一定漲的通紅,急得滿頭冒汗。
隊長看他急赤白臉、費勁巴拉的樣子,就出面打圓場說:“老前輩幹了一輩子,被地主剝削壓迫了一輩子,想起舊社會受的苦遭的罪有些激動,說不下去了。我們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地、富、反、壞、右批倒鬥臭,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樣,我們貧下中農就永遠不會再受二茬苦,遭二茬罪了。”
老長工說的劉建是我們村最大的地主,大約有二百多畝地,僱著四、五個長工,農忙時還得僱短工。他住的院子並不大,五間正房,五間南房,東西房各四間,一磚到頂,是非常精緻的一個方方正正的四合院,有四、五百平方米。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那個門樓和一進門的那個影壁,全部是福祿壽喜等吉祥磚雕砌成,構思獨特,佈局新穎,雕工精美,巧奪天工,在全村獨樹一幟,無人企及。
最扎眼的是他家那輛膠輪大車,那是全村唯一的一輛當時最豪華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駕轅的是匹大黑騾子,渾身上下沒有一根雜毛,遠遠看去,像緞子一樣,黑中透亮閃閃發光,繃頭嚼子甩頭纓,脖子上掛了一串銅鈴鐺,走起來是昂首闊步威風凜凜,哪個車把式見了都挑大拇指。
拉套的是兩匹高頭大馬,領套馬是匹紅棗騮,外套是匹小黃馬,馬頭上都帶著紅布做的甩頭纓,繃頭嚼子把馬頭勒得高高的,馬脖子下也都掛著一串銅鈴鐺,走起來鈴聲清脆,鐵馬叮噹,五里地外都能聽見。
老長工就是這輛大車的車把式。
土改前,劉建就聽到了風聲,悄悄地把家裡的一部分浮財、農具分給了長工和鄰居,自己帶著金銀細軟逃到北京投奔了兒子。解放後,在村裡就沒露過面。“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定性為“逃亡地主”,被遣送了回來,在街上有時能見到他。瘦瘦的身材,穿一件土黃色的舊棉襖,拄著一根柺棍,將近八十了,進進出出的,看上去身體還挺硬朗。
由於在外多年,村裡的絕大部分人都不認識他。每次村裡開批鬥會、遊街,都是把現在還活著的一個地主婆劉鳳、一個富農分子劉瑞弄到臺上當活靶子,從來沒找過劉建的麻煩。這兩個地、富分子每天負責打掃街上的衛生,也從來沒讓劉建參加。不知是隊裡想不起他來,還是認為這個人不歸他們管,具體原因不清楚。
緊接著,第二個上臺“憶苦思甜”的是個婦女,毛巾包著頭,由於燈光太暗,看不清多大歲數,說話的聲音有點沙啞。看穿著打扮,走路的姿勢,應該有五十多歲的樣子。做事倒是乾脆,不用隊長督促,自己就上了主席臺,沒有“各位領導”、“各位鄉親”之類的客套話,一開口就開始控訴:
“舊社會就是害人呢!那會兒,吃是沒得吃,穿是沒得穿,一天到晚餓得頭昏眼花,走路都打晃兒。俺老漢(即老公)餓的不行了,偷了人家點兒吃的,被逮住,叫人家把眼給挖了。俺們房沒一間,地沒一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只能拉著俺那瞎老漢到處討飯吃。那會兒,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錢看病呀!可憐俺那老漢沒幾年就走了。”說到這兒,老太太是熱淚縱橫,啜泣不已。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誰了。
當年,這是一樁有名的公案,這個案子曾經驚動了十里八鄉,一度成了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主要話題,過了好多年,事情才慢慢地平息下來。
那時,我媽才八、九歲,這件事像一根鋼針紮在她幼小的心裡,那種撕心裂肺的疼,錐心刺骨的痛,深深地銘刻在她的記憶裡,讓她一輩子都無法忘記。從我記事起,媽媽就一遍又一遍地給我講這件事,所以今天這個人一說她老漢被挖了眼,我就知道她是誰了。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這個女的叫改芳,她的前夫扣兒(當地許多人給孩子起乳名習慣用一個字,後面帶“兒”音,以示寵愛)和我姥爺劉瑛是本家,沒出五服的近親。住得也很近,只有一牆只隔,但不在一條街上。我姥爺家的這條街是東西走向,扣兒住的那條街是南北走向,兩條街正好在這兒交匯,形成一個丁字路口,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座很小的五道廟。我姥爺家在廟的西面,廟的後面是我姥爺家的菜園子,緊挨著菜園子就是扣兒家,他們家房子的位置和我姥爺家的裡院平行。
兩家是近親,又是近鄰,平時關係非常好。好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就知道了。
扣兒來我姥爺家串門,出了他們家的街門,得從丁字路口拐彎兒,繞過五道廟,才能到我姥爺家。為了讓他們進出方便,我姥爺特意在外院的牆上開了一個小門,從這個小門穿過菜園,開啟籬笆門就是他們家的街門。這樣,從他們家的街門出來,可以直接拐進我姥爺家的外院,免得再繞那個街角。
那時,我大姨有十六、七歲,心靈手巧,在家做些針線活兒。訂親後,就開始繡一些結婚用品。改芳雖然比她大幾歲,可是她也喜歡繡活兒,所以她們有共同話題,能說到一塊兒,兩人的關係就越發親近。常常待在一起,邊做活兒,邊聊天,一待就是半天。好的是誰也離不開誰,只要半天不見面,兩人都會念叨對方。
每天吃飯時,這兩口子都要端著飯去我姥爺家,邊吃邊聊。
扣兒年輕,心眼兒活泛,為人處事像《烈火金鋼》中的解老轉兒,有七十二個轉軸,三十六個心眼。辦事看人下菜碟,用得著朝前,用不著的朝後,給人的印象是不踏實,不那麼可靠。
俗話說,好漢在嘴,好馬在腿。扣兒就長了一張好嘴,伶牙俐齒,巧舌如簧,死人都能說活了。
1937年忻口會戰失敗後,太原失守,隨之整個山西淪陷,晉中平原就成了日本鬼子和八路軍進行拉鋸戰的戰場。白天,日本鬼子挖地三尺到處搜查八路軍;晚上,八路軍四處活動到處騷擾日本鬼子。這時候,最難過的是老百姓,白天躲,黑夜藏,一天到晚提心吊膽,連睡覺也得睜著一隻眼,沒有一天能踏踏實實的過日子。
生逢亂世,對於一般人來說,會有一種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感慨;而對於有的人來說,生逢其時,亂中取勝,正是大展拳腳渾水摸魚的好機會。扣兒就是這樣一種人,而且他也抓住了這個機會。
當時,八路軍和日本鬼子天天打仗,沒有人管老百姓的事,而村裡的村規民約也蕩然無存,有的人為了賺錢就開始倒賣白麵兒。扣兒看到這個買賣既輕省又來錢快,馬上跟著做了起來。
頭一、兩年,扣兒還真的過了幾天滋潤日子。
自從有了錢,扣兒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穿著打扮,還是吃喝用度,那真是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了,連走路都是昂首闊步、趾高氣揚。在村裡,儼然成了一個人物。人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料子扣”。由於他做的是損人利已、傷天害理的買賣,人們背後都罵他“不得好死”。誰知一語成讖,最後居然應驗了。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的。時間一長,錢掙得多了,平時也不用下地幹活,閒的無聊,慢慢地扣兒自己也開始抽上白麵兒了。
剛開始,人們對這種東西危害性的認識並不那麼清楚,甚至覺得是個好東西。因為農村缺醫少藥,人們平時有個頭疼腦熱,肚子不舒服,抽上兩口就可以緩解;如果哪天渾身痠懶沒有精神,抽上幾口,馬上精神十足。後來才發現,這種東西抽的時間長了,有了癮,麻煩就大了。而且是越抽越想抽,越抽越上癮,越抽菸癮越大,這時候就已經中毒了。等你幡然悔悟,想棄舊圖新時,一切為時已晚,所以一般人不敢碰這個東西。
剛開始是扣兒一個人抽,以販養吸,雖然掙的比原來少了,可是日子還行,過得去。後來,他媳婦改芳也學會抽了。這麼一來,抽的就比賣的多了,開始入不敷出,只好東挪西借,拆了東牆補西牆,這日子慢慢地就走下坡路了。
家有金山銀山,也架不住煙槍冒煙,何況還是兩杆煙槍。這兩口子抽了不到一年,把家裡的東西就賣了個精光。要命的是,到了這個節骨眼上,他倆想戒菸也戒不了了。飯少吃可以,這大煙不抽可不行。家裡實在沒的賣了,只好賣地。十幾畝地,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全都化成了青煙。
俗話說,兵敗如山倒,家敗如塌方。沒幾年時間,這兩口子就把好端端的一個家,折騰的是一無所有,每天吃了上頓沒下頓,過起了有今天沒明天的日子。為了抽上這口煙,最後把他們家的心肝寶貝、唯一的一個八歲的兒子也賣了。
人活臉,樹活皮;沒臉沒皮,天下無敵。一個人,如果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線,那簡直和畜牲沒有什麼區別。這兩口子活到最後就已經沒有人樣了,像兩條賴皮狗,每天就在村裡到處踅摸,不管誰家的東西,逮著了就抄走,你說是順也好,偷也罷,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抽上這口煙。有時候,主人找上門來,指著鼻子罵一頓,甚至給兩下,他們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主人也沒什麼脾氣。如果東西還在,拿走了事;如果東西已經沒了,罵幾句解解氣,也只能拉倒。
他們家一年到頭,街門大開,三間正房的門,兩間東房的門從來不關,因為家裡的東西都賣光了,家徒四壁,一無所有,既無替換之衣,又無隔夜之糧,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不用說有人來偷,就連耗子都餓的受不了,搬家了。唯一的財產是炕上堆著的幾床破被褥,確切地說,是一堆爛棉花,煙癮上來,抹的不是鼻涕就是哈拉子,又黏又潮,臭氣熏天,這哪兒是人住的屋子,就是一個圈,牲口圈。
就在這個時候,扣兒盯上了我姥爺家的那匹大灰騾子。
我姥爺是個地道的農民,沒什麼文化。在他的思想意識裡,世界上只有一樣好東西——地。他認為只要有了地,就有了一切。地就是他的命根子。平時是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攢點兒錢,就買一塊地,然後再攢錢,再買地。就這麼一點兒一點兒地湊。老人留的遺產,再加上自己買的地,最後居然也有了五、六十畝,過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日子。即使如此,家裡一年到頭也是以吃高粱面以主,很難吃上幾頓白麵。偶爾蒸個饅頭,也不讓蒸全白麵的,必須是白+紅(高粱面發紅)。究其原因,有山西人固有的勤儉持家的秉性,有一個汗珠摔八瓣奮力拼搏的艱辛,有進一步發家致富的企盼,也有旱澇災年吃不上飯的擔心。使他不得不精打細算每一頓,持籌握算每一天。
我姥姥劉趙氏性情隨和,賢惠,只知道洗衣做飯,相夫教子,家裡的大事小情都是我姥爺做主。
大灰騾子是頭年收了大秋後買的,3歲口。買這匹騾子可是出了大價錢,花了血本了。一個農民哪兒有那麼多現錢,全是靠賣糧食換的。那時候,我媽還小,不知道具體花了多少錢,只看到用毛口袋(當地用的一種裝糧食的口袋,每個口袋裝滿了糧食,紮好口,正好是100斤)裝的糧食擺滿了比半個足球場還大的多半個場院。我媽說,那年過春節,全家連白麵餃子都沒吃上,大年初一,姥姥是用兩樣面給他們包的餃子。早就答應給她們姐妹買的花衣服,也變成了一個夢,一個五彩斑斕的美夢。
自從買了這匹騾子,我姥爺就和這個畜生結下了不解之緣,每天有事沒事都得守著。大冬天的,北風呼呼地刮,除了晚飯天黑必須在屋裡吃之外,早飯,午飯都得端著碗到外院吃,只有看著騾子他才吃的下飯,這飯才吃的香。前面端詳,後面細瞅,左面瞧、右面看,就這麼圍著騾子轉。那個憨憨的樣子,那個痴痴的傻勁兒,就跟看剛過門的新媳婦一樣,眼睛裡滿滿地都是疼,都是愛,怎麼看怎麼喜歡,怎麼看怎麼順眼,怎麼看也看不夠。
我姥姥說他魔怔了。
每天光看當然不行了,還得好草好料地伺候著。除了白天喂之外,每天晚上還得起來兩、三趟,加草加料。自從買了這個牲口,我姥爺就沒睡過一個囫圇覺。而那匹騾子被他喂的是滾瓜溜圓,渾身上下像緞子一樣閃光。要說這牲口也通人性,每次看見他,這騾子都會愜意地搖頭甩尾,噴著響鼻刨著前蹄討好似的哼叫,像見了老朋友一樣。
每天干活兒,老爺子不想讓騾子受一點兒委屈,有些累一點兒的活兒,恨不能他去替騾子幹。只有傍晚回來,卸了套之後,騾子自由自在地伸脖子甩尾巴,躺到地上痛痛快快打幾個滾兒,然後站起來抖擻乾淨汗漬,我姥爺才會舒心地笑一笑,就好像他解除了一天的勞乏似的。
騾子是那年春天的陰曆二月底三月初丟的。
一開春,我姥爺就忙活上了。耕地、耙地、送肥,五、六十畝地,一個人起早貪黑、披星戴月的整整折騰了一個多月,這些活兒才基本上幹完。本來想著能稍微輕鬆上幾天,天氣再暖和點,開始播種,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出了這檔子事。
那天早晨,大約四更多天,我姥爺起來喂牲口。雖然已經是春天了,可一開門,一股冷風順著門縫鑽進來,他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嘴裡自言自語輕輕地叨叨了一句:“好狗日的,這天氣!”轉身放下油燈,把披著的棉襖穿上,然後端起油燈出了門。
外面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我姥爺右手端著燈,左手握成一個半圓形,遮著隨風搖曳的燈苗,慢慢地挪著步子。走到二街門(裡院和外院的一道門),輕輕地拉開門栓,下了外院的臺階,這時一般都能聽到騾子吃草的聲音,今天一點兒聲音都沒有,他覺得奇怪,但也沒多想,幾步走到槽子跟前,舉燈一看,騾子沒了。猶如晴天霹靂,恰如五雷轟頂,一下子把他打懵了。舉著燈,四處照了照,沒有,再照街門,街門關著呢;轉身再照通往菜園子的小門,才發現小門大敞著,他知道壞了,聲嘶力竭地大喊:“有賊了!有賊了!”我姥姥聽見喊聲,邊穿衣服,邊往外跑。兩個人追到街上,哪兒還能看到賊的影子。
這下子,我姥爺可是廟裡著火——慌了神兒了,五尺高的漢子,直轉磨磨。還是我姥姥的一句話提醒了他:“去叫上康壽,追吧。”
康壽是我姥爺家的鄰居,世交,哥們兒。姥姥的一句話如醍醐灌頂,提醒了我那矇頭轉向的姥爺,拔腿就去敲康壽家的門。
康壽出來,聽說騾子丟了,也吃了一驚,略一思索,說:“你彆著急,大哥,咱們這麼辦。我去追,你去找劉和年,他不是有輛腳踏車嗎,叫他騎上車,跟上來就行。”說吧,就往村外走去。
這時,天已經矇矇亮了。
康壽是個膽大心細的人。他一聽情況,心裡就猜到這事有可能是誰幹的了。但是,捉賊要贓,捉姦要雙,光懷疑不行,得有證據,所以當時並沒有和我姥爺說什麼。他分析,如果是這個人偷的,那肯定得去左墩村,因為只有那個村裡有煙館。所以,一出村,他就往去左墩村的方向走。走了不遠,就看到耙過的地裡有一串特別清晰的腳印和牲口的蹄子印,往左墩村的方向去了。康壽也不走大路了,順著這串腳印追了下去。
在耙過的地裡走路,跟在沙漠裡走路一樣,一步一個坑,特別費勁。康壽顧不了那麼多,連跑帶顛,一口氣走了十多里地,累的是氣喘吁吁,汗水把棉衣都溼透了。進村時,正是人們吃早飯的時候。他看見有三個男的蹲在一個臺階上面正吃飯(當地人吃飯喜歡端到街上,邊吃邊聊天),就上去打聽。人們告訴他,有這麼一個人,牽著一匹騾子,還問他們買不買。大清早,開價那麼低,估計不是好來的,沒人敢買,這人剛進了煙館。
煙館在一個大門院裡。一進大門,康壽就看見那匹騾子渾身溼淋淋的拴在一根木樁上,甭問了,偷騾子的人肯定在裡面呢。掀開門簾進到屋裡,有十幾張煙榻的一個屋子,只有扣兒一個人,側身躺在一張煙榻上正在吞雲吐霧,那叫一個香,跟八輩子沒吃飯似的,今天好不容易逮著了一頓,有人進來他都顧不上看一眼。
康壽看著他是又氣又恨,心裡七上八下的說不上來是什麼滋味。三十多歲的一個漢子,原來在村裡也是一表人才,要個有個,要模樣有模樣。如今是形銷骨立,縮在那裡像一堆柴火棒,都沒人樣了;那張國字形的臉,如今是形容枯槁,肉皮緊緊地貼在骨頭上,像經過了千年風霜雪雨的木乃伊;大約長兩米的煙榻,他側身躺著,蜷著雙腿,大概只佔了床的一半多點兒。原先一米七四、五的個子,如今至少縮小了三分之一。
康壽看了一會兒,大聲罵道:“扣兒,你他媽的真不是個東西,連你大哥家的東西也偷啊。成天在人家吃,在人家喝,最後還要把人家的騾子偷走,你他媽的是人嗎?”
扣兒雙眼閉著,正在聚精會神的抽著一個煙泡,享受神仙一般雲裡霧裡的感覺。康壽一喊,嚇了他一跳,睜眼一看是康壽,“呦,是你呀!我還以為是誰呢,嚇死我了。”說著,雙眼一眯又抽上了。
看著他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康壽說:“你還抽啊,我告你啊,劉和年馬上就來了。今天你要讓他抓住,你的小命非玩完不可。”
扣兒一聽劉和年要來,馬上從床上坐了起來,問了一句:“真的?”
康壽說:“這我能哄你,你現在要不跑,一會兒你想跑也跑不了了。”
扣兒想了想,說:“我把這口煙抽完就走。”說完,又躺那兒抽上了。
劉和年是何許人?讓扣兒這麼害怕。
劉和年是村裡遠近聞名的一個惡霸,心黑手恨,無惡不作。按說村裡劉建是村長,他負責治安,可往往劉建做不了他的主。如果村裡逮住一個小偷、流氓,都是劉和年親自動手,掄起一根胳膊粗細的棗木棒子,照著小腿的迎面骨往死裡打。打得小偷鬼哭狼嚎、呼爹喊娘,三、五個月下不來炕。所以,村裡人聽到劉和年的名字,都有點兒不寒而慄。臨解放的頭兩年,他被游擊隊長郭鳳山槍斃了。解放後土改時,他們家的成份是地主。
順便介紹一下郭鳳山。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郭鳳山帶領一支游擊隊一直在晉中地區活動,解放後擔任了祁縣縣長,直到離休。現在縣廣場對面的“歷代名人錄”上,從春秋戰國至抗日戰爭,名人無數,其中有兩個抗日英雄,一個是當年被日本鬼子殺害的烈士武克魯,另一個就是郭鳳山。
再說扣兒。
一個煙泡還沒有享受完,就聽咣噹一聲,兩扇門猛然被推開,帶著一股冷風,劉和年已經進了屋裡,兩隻眼睛像鷹一樣盯著扣兒。扣兒睜眼一看,劉和年正站在屋子中間看著自己,嚇得屁滾尿流,想跑是不可能了,就在他剛把兩條腿抬起來放到床沿下,用一隻胳膊撐著想坐起來時,劉和年一個箭步衝上去,一下子就把他按在床上,手裡的繩子一抖,三下五除二,乾脆利索地把他綁了起來,像粽子似的捆了個結結實實。
怎麼處理扣兒,劉和年和劉建吵了一架。
平時,抓住一個小偷小摸的,劉建不管,都是劉和年處理。一般情況都是打一頓放了,或者由家裡的人領回去。有些屢教不改的,在村公所的小屋裡關兩天,找個人作保,也就放了。
這次,扣兒可不是小偷了,是大偷,而且偷的東西還價值不菲,所以不能像平時一樣放了了事。劉建主張,把他交給日本人,由日本人處理,要殺要剮,要關要放,由日本人作主,村裡就不趟這渾水了。
劉和年不同意,擺在桌面上的理由是,咱們都是中國人,同村同宗,憑什麼要交給日本鬼子去處理。實際上,他心裡還有個小九九,不能放到桌面上說。第一,他和扣兒有仇,他想借這個機會,把這個仇報了,最起碼不能輕而易舉地放過他,不整死也得把他整殘了;第二,扣兒有個連襟在警備隊當中隊長,如果把他交給了日本人,這個連襟能幫上忙的話,很有可能,日本人就把他給放了,之前村裡所做的一切努力就白費了;第三,扣兒的那張嘴特別能說,也特別會說,萬一日本人被他說動了,放了他,那算好的。如果他加油添醋,把我劉和年弄進去,那麻煩可大了,搞不好連命都得搭上。所以劉和年堅決不同意把扣兒交給日本人。
話不投機,劉建說服不了劉和年,甩手回家了。
劉和年把扣兒關在村公村的一間小屋裡,讓他的打手凌昌看著。
凌昌是個流氓無產者,劉和年的得意幫兇。這兩個人湊一塊兒,真是應了那句話:什麼人找什麼人,夜壺找尿盆,是天上難找,地上難尋的絕配。他們倆在村裡是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打瞎子罵瘸子,踹寡婦門,扒絕戶墳,什麼事都幹,就是不幹人事。
凌昌在村裡惡名遠揚的緣起是一次殺狗。
一天,凌昌不知從哪兒逮住一條狗,他既想吃狗肉又想要一張整皮,就採取活剝的方式。從狗的眼角下刀,一點兒一點兒地往下剝,疼得狗“嗷”、“嗷”慘叫,大白天的,叫得周圍的鄰居渾身直起雞皮疙瘩。有幾個膽子大的鄰居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就出來找,最後找到他們家門口。推開門,才知道凌昌在殺狗。正在這時,那條狗居然掙斷了指頭粗的繩子跑了出來,半個臉上耷拉著被剝下來的皮,鮮血淋淋,疼得叫聲都變了音了,邊跑邊嚎,凌昌提著將近一尺長的殺豬刀,邊罵邊追,嚇得人們紛紛躲避。
從此,人們知道了凌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吃人肉喝人血的活閻王。
我姥爺在眾人的幫助下,把騾子找回來,以為完事大吉了,天天在家伺候他的騾子。
當然,他也不敢掉以輕心,怕再出什麼岔子,晚上就搬到外院的柴房裡睡。一則喂牲口方便,二則防止再出現被盜事故。通往菜園的那個門也關上了,和扣兒家的交情從此也就一刀兩斷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樹欲靜而風不止,或許是宿命,或許是劫數,該來的一定會來,想逃也逃不脫,想躲也躲不掉。
第三天傍晚,凌昌來找我姥爺。他告訴我姥爺,劉和年同意了,把扣兒交給日本人處理。他還訴苦說,老在咱們村公所押著也不是事,我還得白天黑夜的看著他,弄得我什麼事也做不成。言詞懇切,訴說在理,我姥爺深信不疑。
我姥爺說:“你們該送哪兒就送哪兒吧,就不用和我說了。”
凌昌說:“那不行!騾子是你們家丟的,你是失主,你不去,日本人問我,我能說清楚是怎麼回事嗎,你怎麼也得跟著去呀!”
聽凌昌這麼說,我姥爺也沒轍了。抬頭看了看天,馬上就要黑了,就說:“天快黑了,要去也得明天去吧。”
凌昌說:“不行,今天不送走,我還得看他一個晚上,太累,就現在走吧。你收拾一下,我去把扣兒押來,在村東頭的財神廟等你。別進夏家堡村,讓人家看見笑話,咱從他們村東邊繞過去。”
凌昌霸道慣了,說話總是盛氣凌人,一副命令的口氣,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這時,我姥姥出來對老爺子說:“你可別跟他去。天兒馬上就黑了,誰知道他憋什麼壞主意呀。”
我姥爺是個老實人,膽小怕事,明知道凌昌不是好人,可是怕他找麻煩,猶豫了半天,最後還是去了。
雖說已經是春天了,傍晚還是有些寒氣逼人。村外,一望無際的田野裡,看不見一個人影,小風肆無忌憚地使勁吹著,把樹枝子凍的瑟瑟發抖。不時颳起的一股股小旋風,捲起黃土和枯葉,嘩啦啦地響著,追著人不停地打轉,在寂寥空曠的野地裡,令人有點毛骨悚然。太陽已經落山了,餘輝映紅了西面的半個天,紅彤彤的,隨後逐漸由鮮紅變成了暗紅,慢慢地一點一點消失著,天越來越黑了。
我姥爺披著黑棉襖,剛到廟門口,遠遠地就看見凌昌押著五花大綁的扣兒過來了,嘴裡像吆喝牲口似的,時不時地推搡兩下,推得扣兒趔趔趄趄地往前走。
走到廟門口,凌昌和我姥爺說:“咱們走吧。”
廟門口有一條路可以直接通到鎮上,即使路過夏家堡村,離居民區也有一段距離,這麼晚了,根本碰不見人。
走了一百多米,出了村,凌昌忽然回過頭來對我姥爺說,“劉和年說來怎麼還沒來呀,你到廟門口看看,他來了沒有?我在這兒等著你。”
我姥爺只好折回來,走到廟門口,根本看不見一個人影,心想我在這兒等會兒吧,等劉和年來了,讓他跟凌昌去得了。
正在這時,突然從村外傳來“啊!”,“啊!”的兩聲慘叫,尖利無比,一聲比一聲淒厲,一聲比一聲悲慘,一聲比一聲瘮人。叫聲在黑咕隆咚、寂靜無垠的野地裡迴盪,讓人感到渾身發緊、頭髮直奓,恐懼像漆黑的夜色一樣包圍著我姥爺,讓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緊接著,聽到扣兒撕心裂肺的哭喊聲。
聽到叫聲,我姥爺嚇了一跳,趕緊就往村外跑。遠遠地看到凌昌手裡拿著繩子大步流星地往回走,邊走嘴裡還不乾不淨地罵著。我姥爺以為他又打扣兒了,嘴裡還說呢:“給兩下子就行了,別打壞了他。”走到跟前,凌昌說:“走吧,回去吧,不用去鎮裡了。”邊說邊自顧自的走了。
我姥爺跟著往回走了幾步,聽到扣兒像只受傷的狼,還在一個勁地嚎著,心一軟,就回去了。由於天黑,看不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就看見扣兒趴在地上,雙手捂著臉,頭拼命地往地上拱,悲慘地叫著,似哭非哭,似嚎非嚎,身體一下接一下痛苦地抽搐著。
我姥爺蹲下來,伸出雙手想把扣兒扶起來,碰到他的手,感覺手上溼乎乎的發黏,才發現扣兒滿手滿臉都是血。趕緊問他怎麼了,問了半天,扣兒才斷斷續續地說,眼被凌昌捅瞎了,氣得我姥爺一陣亂罵。
等我姥爺把扣兒送回家,到家已經是半夜了。
兵荒馬亂的,我姥姥怕出事,根本就沒敢睡覺,一直坐在炕上等著我姥爺。看我姥爺回來了,禁不住埋怨起來,可聽我姥爺一說情況,才發現事情弄大了,要麻煩,再也不說話了。
第二天剛吃完早飯,改芳過來借錢,說要給扣兒看病。自從他們兩口子發家致富後,改芳就再也沒來過,今天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姥爺心裡明白,說好聽點兒是借,說不好聽點兒就是來要,只要拿出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可想到明天晚上的事,心裡有點含糊。如果昨天沒去現場,天大的事也和咱沒關,問題是昨天去現場了,有些事情就未必能說清楚。凌昌是個流氓無賴,說翻臉就翻臉,扣兒不敢惹他,可敢惹咱。如果扣兒一口咬定,是我把他的眼睛弄瞎了,能說清嗎?誰能證明不是我弄瞎的?思前想後,最後還是把錢借給了改芳。
從此以後,扣兒一家就吃上我姥爺了,剛開始是借,借錢,借米,借面,借這個,借那個,什麼都借,什麼都是有借無還。後來就是明目張膽的要了,一沒吃的就來要,一般十天半月就來一次,一直要了四年多,直到扣兒死了,改芳改嫁之後,我姥爺才如釋重負,過上清淨日子。
當年,播種一結束,我姥爺就把那匹騾子賣了,從此再也沒有買過牲口。
人惡神鬼懼,人善有人欺,這就是社會法則。
扣兒眼被捅瞎後,從來沒敢找過凌昌,更不敢去找劉和年,他是從心裡怕了。
凌昌把扣兒的眼睛弄瞎後,村裡人從此再也不叫他的大名了,給他起了一個綽號 —— 眼睛三。這個綽號叫開後,人們反而很少知道他的大名。
解放後,眼睛三的成分是貧農,沒有人和他過不去,也沒有人找過他的麻煩,更沒有人和他算這筆帳,日子過的逍遙自在。
“憶苦思甜”的會散後,回到家,我把開會的內容和姥爺、姥姥一說,兩位老人都有點害怕,一晚上忐忑不安的,連覺都沒睡踏實。當時“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不斷地掀起一個又一個鬥爭高潮,如果把這件事當做階級鬥爭新動向,抓個把人鬥一頓或者打一頓,再正常不過了。我姥爺奔八十的人了,要是這麼一折騰,那可就要了命了。
兩位老人就這麼煎熬著,等待著命運的安排。
那天的會上,改芳說來說去就那麼幾句車軲轆話,顛來倒去地說了三、四遍,也沒有什麼新內容,她講完後,隊長開始佈置下一階段的生產任務。
改芳本以為她的憶苦會引起村民的共鳴,在村裡掀起一個滔天巨浪,誰知連個漣漪也沒有蕩起,日子還是原來的日子,平靜如常。因為農民都是世世代代住在一個村裡,無論說起誰,那都是開水鍋裡洗澡 —— 熟人。誰的人品怎麼樣,每個人心裡都有數。不僅知道現在活著人的底細,連他們家祖宗八輩的事都能說的一清二楚,想編個故事騙大家,根本不可能。
“憶苦思甜”大會開過後,大隊裡沒有任何動靜。可是,我姥爺、姥姥的心還一直懸著。過了好幾個月,村裡也沒有人提這件事,他們心裡的那塊石頭才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