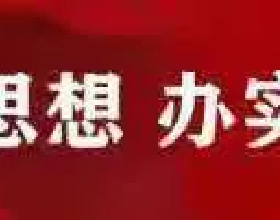1956年,毛澤東和藝術家在一起。
對藝術的特殊理解
毛澤東並非藝術收藏家,卻算得上是一位不錯的藝術鑑賞家。他在藝術方面有一種特殊的理解。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他說,“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
8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與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其中對文化藝術規律的論述,相當精闢:
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
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現在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可以搞,聽憑人選擇。外國的許多東西都要去學,而且要學好,大家也可以見見世面。但是在中國藝術中硬搬西洋的東西,中國人就不歡迎。藝術有個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後人還是喜歡它。
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並不等於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
特別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但是,應該是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為八股。過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處一樣就不好。
……
演些外國音樂,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樂、十部樂,多數是西域音樂,還有高麗、印度來的外國音樂。演外國音樂並沒有使我們自己的音樂消亡了,我們的音樂繼續在發展。外國音樂我們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長處,就對我們有益。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
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這樣爭論就可以統一了。
……
這是毛澤東幾十年以來對藝術的切身感悟和深刻思考!這當中也包括了他對在故鄉的切身體驗的思考。
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他在故鄉的藝術體驗經歷,就像他家居生活的其他幾乎所有的方面一樣,故鄉是他的根,也影響著他一生的愛好傾向或習慣。
毛澤東的藝術體驗和思考經過長達80多年的漫長時間———韶山的17年是他的第一階段。同時,我們應當注意到,毛澤東的藝術領域基本上涵蓋的範圍是語言的藝術(詩歌、散文和口頭表達)和視覺的藝術(書法)、聽覺的藝術(戲曲、音樂)、綜合的藝術(表演)。這幾者常常是交匯在一起的,其規律也是完全相通的。
在私塾裡,毛澤東受到了正宗傳統文化的陶冶———對於先生來說,他們授以課讀,主要是為了讓學生識字,其次是囿以儒家禮法。藝術導引,則是無意的薰陶。
6年的私塾生涯,毛澤東以他聰慧的資質,以超過與他同窗共室的人們的速度和效率,從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中吸取著營養,並開始開出最初的藝術花朵。從南岸的詩對:“濯足———修身;牛皮菜———馬齒莧”到井灣裡的《贊井》詩,他的起步是令人驚奇的。書法,也由描紅到臨摹歐陽詢、錢南園,我們從他這一時期留在《詩經》《論語》等書籍封皮上的墨跡,可以看出他最早的書法,是非常工整秀穆的。
當然,對戲曲的愛好與其他藝術品種對毛澤東的影響是同步的,只是自從離開家鄉,他對戲曲的愛好一開始就表現著兼收幷蓄的特點。
從這諸多的風俗習慣中,我們可以抽出對毛澤東影響深遠的藝術之線。這條線是漢苗交織、雅俗同在的一條線,既有遠古苗民的遺存,又有近500年中移民從江浙帶來的藝術之風,既有山間田野的口頭藝術,又有祠堂廟宇的祭祀演藝之樂。
毛澤東早年在故鄉的聽戲觀劇主要在大路邊、地坪裡和廟堂中。春節裡,龍燈一般從初四五耍起,耍到元宵節,團有團龍,族有族龍,後來一般按土地廟的管轄地域(大致相當現今一個村,如毛澤東家所在地域屬於關公廟管轄),從團防局和各族祠堂一直耍到各家各戶,費用按田畝分攤。為圖吉利,龍燈都要進堂屋。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遠遠地聽到鑼鼓嗩吶聲,早早開啟堂屋門,點上燈,龍就進了屋,繞香火堂幾圈在前坪耍起來,伴隨著花鼓和湘劇高腔的“關雲長”,還有一躍一躍的獅子,真是喜氣洋洋!毛順生高興,早準備了一個不大不小包封,毛澤東兄弟則一掛掛地放響著炮竹。龍燈的苗文化味道比較重,花鼓戲則是典型的湖湘地方戲。正月十五的燈節則帶有十分明顯的中原文化特徵。
過了春節,屬於韶山和湖湘本土的娛樂活動(準確地說是娛神活動)則是端午的劃龍船,比較近地觀看龍船賽是在銀田寺前雲湖(韶河)上,遠的更壯觀的則要到百里之外的湘江,各團各境的船一邊擊鼓一邊喊著號子,競相爭先,岸上則是人山人海。相應地也會有一些古苗民留下來的藝術形式開演。
這些都是民間的公共娛樂活動,而在清明、中元、重陽諸節裡,各姓氏都要在各自的祠堂開祭。毛家的祠堂專設戲臺,祭祀之後,族人就有看戲的機會,多是花鼓戲和影子戲。
另外,毛澤東還愛跑到清溪寺去看熱鬧。每當關公的生日(農曆六月廿四)和觀音菩薩的生日(農曆二月十九),清溪寺都會有大的祭祀活動,這些活動當然帶有濃濃的柏香味和虛幻的色彩。毛澤東總是陪伴著母親虔誠地感受著這種宗教的氣氛。
毛澤東還有一個接受地方戲曲和文化薰陶的時機,那就是婚、喪的禮儀。其中婚嫁禮俗,大多來源於中原文化,多是儒家的一套,而韶山的喪禮卻是儒、釋、道、巫雜糅:祭祀多用儒家的禮節,超度則純是佛家的那套,種種禁忌和晚間的唱夜歌,則是特別富於南楚山區神秘文化特徵和苗民遺俗的東西。
毛澤東少年時代見得最多的戲種,無非是花鼓戲和湘劇高腔,還有影子戲,前兩者多在過年的時候能看到,後者則是祭祀的時候或者給長壽老人慶生的時候演。影子戲多用湘劇高腔,清越而高揚,許多時候帶有一種悲壯和涼意,有濃濃的楚地古風,內容卻是正宗的中原文化曲目,與毛澤東後來喜愛的一些劇目非常相近,有《關雲長》(韶山方言“關文長”)《薛仁貴徵東》《樊梨花(薛仁貴的兒媳)徵西》《鍘美案》等等。
總的說來,毛澤東早年接受過多種藝術形式的薰陶,這是他喜愛民間藝術和戲曲藝術的根源。
藝術給他以靈感
毛澤東後來離開韶山,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對視覺和聽覺藝術的愛好也向東西南北乃至外國藝術延伸。對藝術的喜愛和欣賞,使他在緊張的環境中得到休憩和放鬆,甚至直接開闊了他的思維,拓展了他的戰略空間,他每每從中獲得難得的休閒,也得到了種種靈感。
在故鄉,因為經濟條件的限制,毛澤東沒有專門的藝術欣賞而只有隨大家一起的感受,在征戰途中,他只能偶爾得暇與民共樂。就算在他到達延安特別是進入北京城,有了穩定的家居生活之後,欣賞聽覺藝術和視覺藝術的機會多起來,也從來沒有沉湎其中。他對藝術的欣賞一方面是出於他在忙碌的工作之餘的休息或調整,另一方面則是出於他對民族優秀傳統的喜愛和重視,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新文藝的倡導和創造。
中南海毛澤東居住處留下大量唱片、磁帶,內容包羅永珍,從戲劇、相聲到國內外各種舞曲、古典音樂,應有盡有。其中,各種戲劇,尤其是京劇、崑曲佔絕大多數,這是毛澤東由少年到晚年一直愛好音樂、戲曲的明證。
毛澤東在中國300多個劇種中特別鍾情由徽劇、崑曲、秦腔等深化而成的京劇。他正式接觸京劇是從延安開始的。當時有一大批充滿活力的藝術家和青年才俊來到延安,他們把京劇等藝術也帶到延安,使物資極度匱乏的延安有了都市精神生活的活力。
京劇的出現幾乎與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同步。在中國飽受帝國主義侵略,人民浴血奮戰的時候,這個劇種拔地而起,那種黃鐘大呂,抒發的正是民族悲壯的心聲。毛澤東是一位史家,又是一位救國的英雄,同一種情感在延安與國統區和上海、北京間發生著共振和共鳴。毛澤東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喜歡京劇,看似突然,深層次上實則正是這種共振與共鳴的體現。
據李銀橋回憶:毛澤東轉戰陝北時經常唱的是《空城計》《草船借箭》;到達西柏坡後常聽高慶奎的《逍遙津》、言菊朋的《臥龍弔孝》、程硯秋的《群英會》;進入北平前後,毛澤東最喜歡《霸王別姬》。
如果仔細捉摸,我們會發現,毛澤東聽戲的軌跡竟然暗合著他和中國共產黨偉大事業的發展軌跡,也有著他對革命程序的深刻思考,彷彿他一方面在聽著這些歷史上發生過的大戲,一方面又在現實的中國演繹著新版的歷史大劇,於是他時常借鑑歷史的經驗,告誡自己和人們不要重蹈覆轍。
由此看來,我們不能從純藝術的角度去研究毛澤東對京劇和其他戲曲的愛好與欣賞。
毛澤東對京劇的喜歡並非全盤的拿來主義,像思想的其他許許多多方面一樣,毛澤東的藝術思想也在延安走向成熟,其觸角也伸向中國的傳統劇種,包括京劇,京劇在延安得到了改造,被注入時代的氣息和抗戰的精神。
他在繁忙工作之餘聽聽京劇,看看邊區文工團員演出的秧歌戲,也不全然是休閒,而是帶著思考。
1949年3月,他帶著在延安時期添置的手搖留聲機進入北平。那些曾給予他不少歡樂的京劇唱片也隨之走進庭院深深的中南海。不過,這時已今非昔比,大都市的繁華畢竟不可與延安邊塞的荒涼同日而語,毛澤東有條件添置更多的唱片了。後來,他有了錄音機、電唱機,也有了藏量豐富的種種戲劇、音樂磁帶。
1957年4月1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率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中國,毛澤東親自到首都機場迎接,並代表中國政府向伏羅希洛夫和他所率領的代表團致歡迎詞。在確定文藝招待演出的劇目時,有人提出演一出比較輕鬆的京劇,也有人提出演一出典雅的崑曲,爭來爭去,最後,大多數的意見是怕蘇聯人聽不懂京劇和崑曲,決定全部改為歌舞類。節目內容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大為不滿:“一定要有戲曲,而且要演崑曲,崑曲聽不懂,難道京劇就聽得懂嗎,崑曲載歌載舞,而且一定要演崑曲《林沖夜奔》,一定要是最好的崑曲演員來演,就讓‘活林沖’侯永奎來演吧,我也要去看。”
毛澤東親點《林沖夜奔》,並陪伏羅希洛夫觀看。當侯永奎唱到“管叫你海沸山搖”時,毛澤東帶頭起立鼓掌,全體中央領導和在場觀眾也隨之起立鼓掌。伏羅希洛夫雖有些莫名其妙,但還是對中國戲劇產生了興趣。
毛澤東曾多次請文藝界人士進入中南海演出。在看梅蘭芳、周信芳、馬連良等京劇大師表演京劇摺子戲時,毛澤東還建議由侯寶林等相聲演員表演幾段輕鬆幽默的相聲。他多次邀請侯寶林到中南海表演。
北京剛剛解放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一般在原來的美國駐華使館聽侯寶林表演相聲。他通常坐在第三排的中間位置。這裡放著兩把藤椅,一把是毛澤東的,另一把是朱德的。有一次,葉劍英、彭真為毛澤東等準備了一臺文藝晚會,毛澤東得知侯寶林將出場,才來到東交民巷的北京市委機關禮堂。侯寶林、郭啟儒合說了一個新段子《婚姻與迷信》,毛澤東聽後稱讚:“侯寶林是個天才,是個語言研究家。”返回居所的路上,毛澤東還在對侯寶林的演技讚不絕口:“侯寶林對相聲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學問,將來可以成為一個語言專家。”後來,他還看過許多侯寶林表演的段子,如《字象》《關公戰秦瓊》等。
1959年至1963年,馬季所在的廣播說唱團每週至少兩次去中南海演出,共演出100多箇中小型段子。毛澤東經常去聽,他最喜歡聽馬季表演的揭露江湖醫生騙人伎倆的《拔牙》和張述今創作的《裝小嘴兒》。
1963年,馬季下鄉到山東文登縣創作,寫出《畫像》《黑斑病》《跳大神》等作品。毛澤東知道後高興地說:“那好,演一演,我聽一聽。”看完演出,毛澤東握著馬季的手說:“還是下去好!”
毛澤東家裡留下的唱片、磁帶當然不能說他都聽過,有些則是工作人員安排舞會時常備的舞曲。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有時在客廳裡跳跳舞,以此運動身心。這些舞曲唱片有《村舞》《戀歌》《新年》《陝北民歌》《東方舞》等,也有一些外國音樂,如維也納音樂《無窮動》《撥絃波爾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