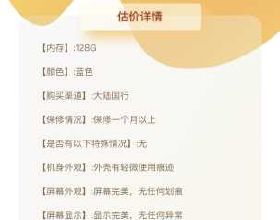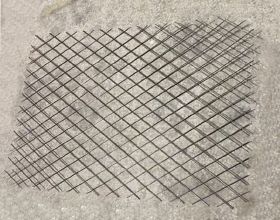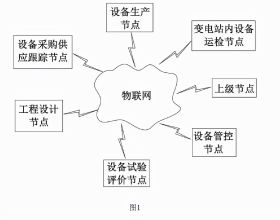聚焦:《Hello,樹先生》
劇情介紹:
村裡有個單身男青年叫做“樹”(王寶強飾),常去村口的酒館和朋友喝酒,在村裡閒晃。“樹”在汽修鋪受工傷後,在醫院被解僱,心生悲慼,竟無所事事調戲護士(何潔飾)。一起長大的夥伴,有人開著好車成了煤老闆,有人遠在省城辦私立學校。村子裡的煤礦日夜開採,地面下沉,整個村莊不得不遷往別處。常被取笑被漠視的“樹”乾脆遠走省城在學校打工,孩子們讓他想起自己的童年。父親和哥哥在“樹”小時候就離開了人世,他常夢到自己的父親,卻從來夢不到哥哥。與聾啞女孩小梅(譚卓飾)一見鍾情,相愛過程頗富戲劇性,婚禮前夜,“樹”終於夢到了哥哥一一在寒冷冬天,在“樹”的婚禮上,哥哥帶著女友為他唱了一首詭異的八十年代流行歌《冬天裡的一把火》。從此,“樹”意識到自己能夠通靈。村裡發生的很多事情都驗證了他的預言,“樹”成為受人尊敬的“預言家”,被人尊稱為“樹先生”。村裡的人們搬到了縣城新區“太陽新城”,小梅也離開了。“樹先生”在空蕩蕩的村子裡抱著一棵樹,大著肚子的小梅突然回來了,啞巴竟開口說話:走,咱們回家。(來自百科詞條)
《Hello,樹先生》海報
見聞
前幾日去鄉下考察學習的時候,我們路過了一個小鎮。那個小鎮的牛肉丸是一大特色,所有人都下車去尋覓那個味道。在我們要穿越一座小橋直奔目的地時,一個流浪漢被一群小屁孩追著跑。那流浪漢不時地轉過身來朝孩子們吼叫,他臉上掛著笑意,這種也許顯得滑稽的行為惹得後面的男孩們一陣陣興奮地叫喊。
我想起了自己小時候夥同朋友們挑逗流浪漢的情景。過了這麼多年,男孩們的惡趣味依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只不過時過境遷,流浪漢該是越來越少了吧。
我常常會設想這些人的精神處境,我好奇他們的世界有沒有俗世的紛紛擾擾。這些人衣衫襤褸地在人世上游蕩,哪天他們消失了我們也不會有絲毫奇怪。
我們和他們毫無交集。
流浪漢為什麼會成為流浪漢,這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謎。(在我的記憶中,村裡時常會來一些要飯的人。這個時候,母親總是去屋裡拿一個饅頭出來。)對這個謎的探究就好像去問某人為什麼會成為某人一樣,是永遠也不可能得到精確答案的。每個人都會在敘述中騙人,你又能分辨多少真假?
流浪漢不會騙人,因為從來沒人向他們提問。
流浪漢的精神狀況多數令人擔憂,因此和他們的交流就變得幾乎不可能。可儘管如此,在許多文藝作品裡,我們仍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他們在藝術家的想象中被建構出來,變為一種我們可以談論的物件。在藝術的有限世界裡,流浪漢不再神秘。
流浪漢、乞丐、瘋子、精神病患者,應該是我們這個社會中最不為人關心的構成,但卻常常拷問著我們的良知。他們是社會的少數派,但我們卻並不陌生。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引述柯萊特描述“瘋子”的話語那般:
在這條大道上,我看見
一群孩子尾隨著一個白痴。
……想想看,這個可憐蟲,
這個瘋癲的傻瓜,他帶著那麼多的破爛能有什麼用?
我常常見到這種瘋人
在大街小巷中高聲叫罵……
這和我在小鎮所看到的景象沒有任何差別。
瘋癲的樹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裡,馬小軍和他的朋友們在北京的衚衕裡穿行時,那個騎著木頭的“傻子”格外引人關注。他和馬小軍們用“古倫木”和“歐巴”這樣不明就裡的語言唱和著。這個“傻子”變成了一處“景觀”。
在很多電影作品裡,對這類人的表現都是程式化的,這些精神上的邊緣人更不可能成為敘事的中心,所以《Hello!樹先生》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價值。
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則對本片的評價:每一個村莊裡,都有一個樹先生。
原諒我沒辦法考證這句話究竟誰最先提出的,但我私以為其很準確地描述了一個實存的社會事實。
至少在我的經驗中,這句話是成立的。
人們尊稱他為“樹哥”。可在影片中,“樹哥”時刻在遭遇著冷落和白眼。就連街上的小孩也不把他放在眼裡,說他算老幾。老闆在他受傷後開除了他,他丟了工作。二豬表面喊他樹哥,內心裡一點都瞧不上他,就連給他說媒的媒婆也不忘言語譏諷他。
對他稍好一點的陳藝馨也不拿他當回事,雖然藝馨沒有直接傷害他,但總歸也不是一路人,更沒法給樹一個精神慰藉。
影片當中唯一一個對他好的,不以另眼看他的人就是礦工小莊了。小莊是一個和樹同樣卑微的人,他最後的死也只有樹在乎了。
樹本不瘋,可最終他卻走向了瘋癲。
在尊嚴被無休止地踐踏後,瘋癲或許成了唯一的歸宿。
樹何時走向瘋癲的呢?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樹在所謂“朋友”的婚禮上遭到了二豬的侮辱後走向了瘋癲,另一種說法是樹在自己的婚禮前因想要豪車卻未能滿足而走向瘋癲。不論哪一種說法其實都有其依據,都指向了樹喪失了自己尊嚴的事實,在此不多談。
我想談的是促使樹瘋掉的真正原因,這才構成了真正的悲劇。
正是這一層原因結構起了本片的心理空間,這是一個最動人的空間。
1986年,樹的哥哥被派出所當作流氓抓了起來,這件事很讓樹的父親難堪,一怒之下,樹的哥哥被父親吊在樹上打,失手將樹的哥哥勒死。父親勒死了自己的孩子,父親勒死了樹的哥哥,這件事成了樹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霾,以致於常常出現幻覺,他的父親和哥哥在自己的幻覺中輪番登場。
80年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了沒有多久,卻對中國大陸的刺激很大。一時間,外來的文化被以一種飢渴而瘋狂的姿態吸收著。歐洲二三十年前的電影在張藝謀他們看來是如此“新潮”。鄧麗君為代表的港臺歌手的聲音遍及大街小巷。費翔在198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演唱了《冬天裡的一把火》之後,便火遍大江南北。
費翔在198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
年輕人總是更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樹的哥哥是這群年輕人中的一員。我們無法從影片中獲知更多關於樹的哥哥的資訊,但從樹對哥哥的想象性呈現當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哥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喜歡唱歌跳舞,在兩性關係當中比較開放。也正是因此,哥哥被當做流氓抓了起來,讓父親“蒙羞”。
如今“流氓”“臭流氓”這樣的詞在某些語境中幾乎已帶有一種“風流倜儻”“高情商”之意,你完全想象不到三十多年前,“流氓”是貼在一個人身上最難承受的標籤。
198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規定了6種提高量刑幅度的犯罪,流氓罪列於首位。不少人因為流氓罪鋃鐺入獄。
除了樹的哥哥之外,《地久天長》(2019)中的張新建(趙燕國彰飾)也是這樣的罪犯。
很可惜的是,在這兩部電影中關於他們如何被以“流氓罪”論處的細節的描述是缺席的,所以何以流氓就成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問向觀眾,更問向了那個年代。
在劇烈的時代變革中,受到衝擊的不僅僅是我們的物質生活,還有更難言說的精神世界。在精神急需依附的80年代,思想變得異常活躍。
像樹的哥哥和張新建這樣的人,不過是那個年代的一個小縮影罷了。他們或許不能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但是也起碼是一個重要的音符,彈奏著彼時最“撩人”的一曲。所以《冬天裡的一把火》被樹的哥哥和其女友載歌載舞地在他的婚禮上呈現了出來,那是最“撩人”的歌曲,也最能說明樹對小梅的感情。
哥哥之死是樹內心無法治癒的傷。或許這創傷也使得樹變成了一個懦弱的、自卑的和頗為自戀式的人。在遭遇了生活的鞭笞後,他選擇了退回到自己的幻覺中,也就是以一種極端自戀的方式在這個世界“活著”。他無法正視生活中自己的無能,他只能像那喀索斯(Narciccus)那樣迷戀上自己水中的倒影。
樹,與其說是迷上了幻境,倒不如說他創造了幻境。
在這個幻境中,樹擁有小梅又失去小梅,最後又得到了會說話還懷著他孩子的小梅。在這個幻境中,他擁有通靈的能力,之前對他頤指氣使的二豬也跪在他的面前。他還成為了成功人士,當地的礦區開業也得請他剪綵,並和大人物一起暢談登陸月球的宏遠計劃。
這些荒誕不經的場景在《Hello,樹先生》中產生了極大的悲感,刺痛著每一位觀眾。場景越是美好,其內在的悲感就越強烈。所以故事結尾,當小梅走到樹面前牽起他在空中“舞動”的手時,悲感到了極致。
這就是樹,一個瘋癲者,一個被排除在人類社會之外的人,一個試探著人類道德底線的人。
讓我們尊稱他一聲“樹先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