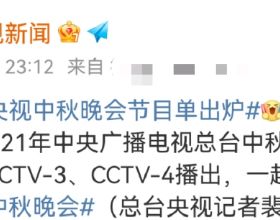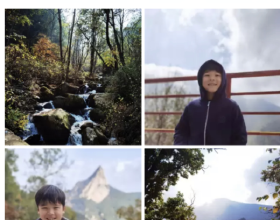放――炮――了――,急促的喊聲在黑漆漆的坑道中一聲聲地迴盪著,“捂住點耳朵,” 父親向我們說完,隨後用一隻手壓下了發爆器上紅色的按紐。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只聽到一聲沉悶的巨響充滿了整個巷道,我的腦袋嗡嗡的,地面也感覺到了劇烈的顫動,我嚇壞了,緊緊地縮在父親身後,任憑那些由於震動而掉下來的煤渣落進我的肚子裡,動也不敢動。聲音過後,刺鼻的煙塵立刻向我們挾裹而來,它們發瘋似地鑽進我們的鼻孔裡,喉嚨裡,腸胃裡,嗆的人喘不過氣,咳嗽的眼淚都出來了。
許久,煙塵淡了,我們吃完了帶的乾糧,喝幾口涼水,緩緩地向工作面走去。現場一片狼藉,零亂不堪,大大小小的炭塊夾雜著石塊崩的到處都是,柱子也被砸倒了幾根。父親檢查了一下頭頂的情況,用長钁頭把鬆動的石頭撬下來,我們又合力將木柱頂好,確認安全後才開始清理現場。他們兩個把覆蓋在煤上面的石頭搬走,壘在旁邊的坑壁上,我則拎著大板鍬往鐵礦車裡裝煤。
礦車是我們這裡小煤窯上統一製造的,除了轅杆用木頭,其它都是鐵的,兩根轅杆中間有一個環,用來綁拉帶和掛捲揚機的鋼絲繩。車子裝滿後差不多有七八百斤重,沒有力氣的根本拉不動。而且只有在出坑道的幾百米上坡才會用到捲揚機,在左右分叉的巷道里面全靠人力往出拉。捲揚機設在窯口的正前方,開卷揚機的是窯主的親戚,一個飽經風霜的老者,臉上溝壑縱橫,乾瘦的爪子緊緊地握著操縱桿,背後的石頭上寫有一排名字,每個名字下方划著一行行 “正” 字。 “小夥子多大了?娶媳婦了哇?” 他朝我露出了滿嘴黃牙 。“哦……十九……嗯……還沒。” 當時,感覺我的臉窘的通紅。
剛開始摸不著道兒,不是車子陷在半路就是被煤塊卡住輪子,儘管拉繩已經深深的嵌入我的肩膀,儘管我的額頭上青筋已經暴突,可是車子卻依然紋絲不動,每次都要叫父親他們幫忙推車,耽誤大家幹活。後來,我慢慢才得出經驗:裝煤時,儘量把車停在上坡的地方,用小煤塊支好,裝滿了順勢很輕鬆的就拉走了;遇到坑時要緊跑幾步,避免車子陷在裡面拉不動。最要命的是空車往下帶鋼絲繩的這段路,因為是下坡,我必須隨著慣性跑,貓著腰叉開腿,鴨子似的眼睛緊盯地面,生怕一不留神踩到鋼絲繩。如果不幸踩到了就慘了,輕則會把你拖倒,重則車子會從你身上壓過去,手臉會被鋼絲繩的毛刺劃傷,血流不止。這些,都是悲慘的事情。
當我在洞口進進出出用盡最後一絲力氣的時候,外面又來了一夥人,一樣是焦灼凝固的眼神。他們是來換班的,我們該下班了。我如稀泥般癱坐在地上,看著一個個從裡面出來的人,衣服和臉都是黑的,頭上,背上都冒著熱氣,他們都如我一般軟綿綿的,靠在洞口旁的煤堆上喘著氣。
天也不知道幾時晴了,滿天的烏雲早已退去。休息片刻,儘管很累了,每個人還是挑選了一塊碳背在背上,然後緩緩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山那邊出現了一個個蠕動的黑點,隨後黑點也模糊不清了,一天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