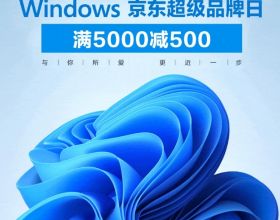第一次見到可樂應該也是這個時候,快雙十一,或者剛剛過完雙十一,大栓給我展示著她給可樂屯的食物,玩具、還有一個做工考究的灰色包包,可樂出門的時候大栓把雙肩包挎在胸前,可樂在包裡,留有空隙,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可樂膽子小,總是瞪著驚恐的大眼睛,怯生生打量著這個世界,如果有人忽然走過來,可樂會惶恐地把頭埋進去。
大栓,是我在這個城市為數不多的朋友,偶爾會一起翹班約著逛公園、聊天、吃飯。我們認識十六年了,時間真快,我對她的記憶總停在上學那會兒。記憶中,那座城市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熱。我們經常一起去學生街吃麻辣燙,宿舍有個多餘的書桌,被大栓佔了,上面堆滿了五顏六色她的衣服,那時候的大栓,是個愛打扮的姑娘,出門隨手拽上件短褲、短袖,汲著個拖拉板,頭髮一挽,看著也挺順眼。她是個白淨的山東姑娘,對人總是一副愛答不理的樣子,其實,剛進宿舍那會兒,我覺得她是最難打交道的人,沒想到,這一處就是十六年。
我見到可樂的時候,大栓結束了一段感情,自己搬出來住了。我知道她為此經歷了多少折騰,心裡壓力也蠻大的,雖然她也經常對我笑,表現出一副沒事人的樣子,但她的笑容裡滿是憂愁,看著讓人心疼。與其在生活的泥沼裡掙扎越陷越深,還不如鼓鼓勁爬出來再說,儘管誰也不知道拼盡全力爬出來以後會看到什麼,但還是先爬出來,喘口氣吧。我不會安慰人,就陪陪她,一起吃頓好吃的。養“可樂”,原本不是大栓的本意,她那時候自己的生活還沒理順,用她的話說,自己都養不活,養什麼寵物呀。可樂是表妹要養的,花了200元錢,從朋友的朋友家裡抱來的。因為表妹經常要出差,大多時候,可樂就由大栓照顧。
可樂是一隻灰色的小貓,大栓告訴我它是英短,最普通的藍貓,我到現在都沒弄明白,明明是灰色的,為什麼說是藍貓呢?可樂頭大臉圓,長著一副好脾氣的模樣,但其實不然,她不喜歡黏人,也不喜歡你莫名地去摸摸它、抱抱它,急了會咬人。我剛去的時候,它一見到我就跑開了。為了解大栓的可樂,我也查看了一些貓貓相關資料,資料上說英短“溫柔平靜,對人友善”可是在可樂身上我怎麼都看不出這種特質,可是每次看到她,我總能想起第一次見到大栓的樣子,這就對上了,有些緣分,真是奇妙的緣分。
人有時候也是循著氣味相識、相知的。我和大栓都是姥姥、姥爺帶大的孩子,她姥爺是教師,據說是個很嚴厲的人,對她管得嚴;我姥姥以前是讀書人家的姑娘,她父親很嚴厲,所以她也是個嚴肅的人。姥姥做什麼都特別認真,她打掃完屋子,一塵不染,看上去整個屋子特別敞亮。同樣的屋子,我們收拾完,看上去總是有幾分黯淡無光。印象中姥姥很講究,頭髮挽起來,在腦後盤成髮髻,一絲不苟。她一直帶著一個她母親傳給她的銀鐲子,樣子特別,像柳葉模樣,上面刻著花紋。她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縫製的,有件黑絲絨,手工盤扣,大對襟的衣服,穿著特別精神,我印象很深。姥姥愛憎分明,她的世界裡非黑即白,沒有模糊的灰色邊緣地帶,她不喜歡扎堆聊天,不喜歡到處串門,朋友不多,一生就兩三個至交。我剛上大學,第一堂心理學課後,老師就問我是不是爺爺奶奶帶大的,我愣住了,這麼明顯,面相就能看出來?後來和老師熟悉了,她說我們上一屆的一個學姐是爺爺奶奶帶大的,我和她的感覺特別像,那時候我不擅長和大人們聊天,當然現在也還是這樣,也沒問老師,那是一種什麼感覺?應該一看就和人群有一種疏離感吧。原來在很久以前我和大栓就有些像。
第一次看到這隻小灰貓,大栓就可樂、可樂的喊它,我很好奇,平時也不見大栓點可樂喝,怎麼就給小灰貓起了個這麼俗套的名字。一說到可樂名字的由來,大栓就興奮了。她在出版社做編輯,自己也喜歡看書,一年買書得花三五千元,現在沙發上、地上不是可樂的玩具,就是各種書,我每次去她那兒都能淘一兩本回來。可樂,來自她喜歡的一本繪本——《奧莉薇》,奧莉薇是一隻精力充沛的豬小妹,她和爸爸、媽媽、弟弟小恩、老狗米花住在一起,還有小貓可樂。你別說,看書上可樂的背影和大栓的可樂還真有幾分神似。大栓的英文名字是奧莉婭,她說以後要養一隻狗,就叫它米花。有一天我跟兒子溜進小區裡一個美術教室,那裡陳列著很多繪本,供在那學畫畫的孩子借閱,我們沒報美術班,屬於蹭讀,在那裡我驚喜的發現了小豬奧莉薇系列。見到了奧莉薇本尊,白色的封面上,那隻打著黑領結,穿著紅裙子 ,斑馬紋打底褲的豬小妹,看著格外神奇。看著繪本,讓我想到王小波的一篇散文——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散文裡說“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定。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定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定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看著看著,我好像有些明白大栓的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