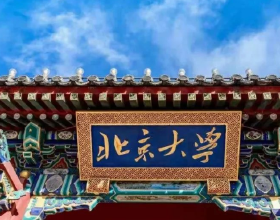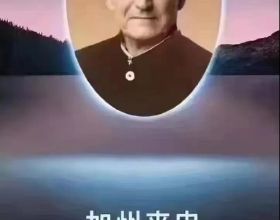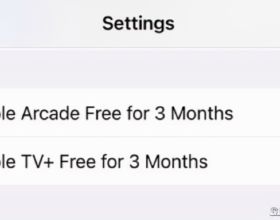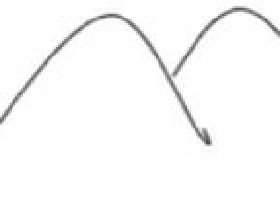多年前某一天在書攤上發現一套三本的勞倫斯散文隨筆,是某省級出版社出版的,但封面設計和印刷質量十分悲慘,便撿起看看,是哪位同行譯者如此慘淡經營勞倫斯譯文。翻開書大吃一驚,那譯文中居然有三分之一強是拙譯。編選者大概不知道我在90年代就用筆名黑馬出版作品了,還選了這之前我用畢冰賓的本名翻譯的一些,於是我就成了這本書中的兩個譯者。再看看那編選者自己翻譯的幾篇,更是令人憤怒,他居然是選了我三篇譯文放在最前面,然後署了他自己的名字,以顯示編選者自己的權威性。
世界上還有如此無恥無理的行為。我怒不可遏地打長途到出版社,接電話者說這書確是他們社出版的,但請與管版權的某先生談。再次打電話時,版權先生在,接過電話說:這事你別問我,出版和印刷都是那位編選者所為。我問那人的地址和聯絡方式,但版權先生不告訴我,要我自己去尋覓。世界上就有這等事,國家的出版社,就這樣明目張膽地為非作歹。我忍住氣,告訴他:這書是以你們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的,書號是你們的,你就是法人,法人就是犯了法要被治罪的人,你懂不懂。你還公然承認是賣書號,好吧,請你把賣書號的話寫下來,我就不找你了,法院和出版署自然會來找你。
對方一聽我這個譯者不是傻子,就說他不寫,但賠款的事要和編選者去談,向那人要錢,至於什麼時候能要到錢他也不能保證。我說:你是不知道我何許人也,還想用拖延術,那就等我把你告到出版署和法院好了。不過我不想費那事,也不想浪費這時間,你就按照一般出書稿酬給我就行,我們私了。至於我是誰,請你就近向你們大名人楊教授打聽一下就行了。對方一聽我居然與楊教授認識,馬上說他是楊教授的學生。等他從楊教授那裡問清我的情況,馬上答應賠償我。過了沒幾天,我就收到某大學的那位編選者的懺悔信。原來此人在大學是個小領導,因為要評職稱當副教授,就出此“高招”,花錢買了書號,不僅用別人的譯文不付稿費,還盜用我的譯文。他在信中十分沉痛地懺悔一番,但又說家中有老母重病纏身,一下子拿不出錢來賠我。還有,這書是花錢買的書號,又花錢印刷,還要自己找路子銷掉才能把錢賺回再賠各位譯者。一邊請我原諒並等他收回成本,一邊求我千萬別告訴他們大學的領導,那樣的話他就名譽掃地,徹底完了云云。總之,是讓我同情他並替他保密,還不要催他賠償。
遇上這樣的人,我這等軟心腸也無話可說了,只好先教育他幾句,又說知識分子“偷書不算竊”。然後就是與出版社核實情況,一切屬實,他確實挺不好過,一旦敗露,他就在那個大學呆不下去了。這就是說我必須當一次雷鋒,成全他們。可又一想不對呀,雷鋒我可以當,但出版社賣書號是賺了錢的呀,他們是零成本白賺錢;那編選者雖然眼下沒收回成本,可他當上副教授了呀,工資提高了,以後的道路一片坦途。只有我這個雷鋒,翻譯了那麼多東西,卻連副教授的職稱都沒評上,還住在臭河邊的經濟適用房裡。不行,這等雷鋒我不能當,我當得冤枉。雷鋒雨夜送大嫂,雷鋒把自己的月餅給戰友吃,他受到了表揚和榮譽,大家都說他是好人,可我卻是犧牲自己成全了別人的犯法行為,這不是學雷鋒。
但我還是不想跟他們學校打招呼,那樣會逼死一個知識分子。我只能盯住出版社了,他們是一個集體,出了事集體負責,不會有人因此尋死覓活。而且現在出版社侵權已經是家常便飯,還會因此耍弄了作者感到得意呢。所以我與出版社攤牌了:你是法人,我就找你,你不解決,咱們只好法庭上見了。
最終出版社還是想出一招,他們看出我這人絕不想毀了那個買書號評副教授的大學老師,知道我是個善良的好人,就“通融”說:你也別要陪款了,我們給你正式出一本勞倫斯作品集吧,用這方式了斷官司。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於是我搜集了當時我翻譯的所有勞倫斯散文隨筆共四十餘萬字給了這家出版社出了一個厚集子,他們付了正常標準的稿費,這事算了了。
朋友們聽說此事當然罵我傻,說那本侵權的書讓侵權人當了教授,讓出版社的個別領導白拿了一筆賣書號錢,我是縱容盜版,實際上我也是壞人。
我就這麼當了一次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