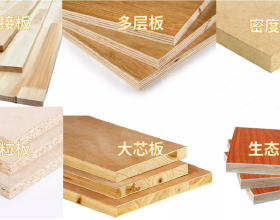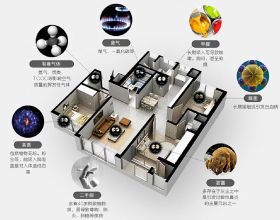前天回原上老家,回來時捎了村上兩個人便車來西安,路上他們說到村裡的事時偶然逮了一句“百世死了”,正開車的我心裡先是一驚,忙插話詢問咋回事,說是都埋了好幾天了,還說百世有福,說走就走沒受啥罪。閒聊已經翻篇了,我的心卻一直在嘀咕,百世叔(按說逝者為大,為逝者諱,不得直呼其名,不過還是不想改變這種生活中的稱呼,望讀者見諒)這麼快就走了。
大約半個月前去狄寨原中雲村買完農家面,順便回南原老家時路過前衛鎮,適逢大集,就碰到老家一位鄰居老人,想著幫幫捎回去,她說還有幾個人,坐百世的車,你的小車也坐不下。再一看,不遠處路邊的百世叔滿頭短短的白髮,斜坐在一輛簡易的蹦蹦車上吃煙等人呢,初秋的寒風中能看出他穿著厚實,魁梧壯實,也看不出有什麼病,這才幾天怎麼就走了呢?
百世叔的去世使我很是傷感,除了走的突然,再就是和我們家還有不少交集。打我記事起,印象中百世叔是弟兄兩人,他排行為小,大約是六十年代末吧,百世叔也就十七八歲,和父母住在土改時分來的房子裡。那是革委會把收來的大房隔成窄窄的溜溜分給窮人的,也沒法選朝向,坐南朝北一小間,地勢有點低,平常陰陰涼涼,下雨天泥濘積水,好久幹不了,出來進去都是穿雨鞋踩泥幾的大人和精腳片的小孩。那時他家的東邊挨著牆凹進去有一間房是隊裡的小衛生室,我的叔父是赤腳醫生,平常就在這裡。我小時候經常來這裡,所以印象很深。在百世叔家房子和小衛生室形成的一塊空地上,總有不少老人夏天靠著牆抽旱菸,有的腳下還有長長的用包穀鬍子擰的火繩,冒著一絲青煙,大家輪著點旱菸。有時靠牆是外來的崩包穀豆的,轟隆一聲巨響,三角地帶,感覺百世叔家大牆上幾塊破舊的黑胡基都要快被震下來。因為百世叔哥哥的孩子和我是同齡耍小,所以來的機會就更多了,印象中百世叔的家裡我進去沒幾回,不過他家裡老人的音容笑貌倒是一直有印象,如今想來,確是我前不久在前衛集見到的百世叔的樣子。
百世叔也算村裡的有本事的人,有一手修理腳踏車、氣管子的好手藝,這都是當時農村不可或缺的事,出門走街串戶,日子過得也不錯。後來娶妻生子,媳婦是四川人,隨著農村落實政策,當年分的房子也清退了,自己靠近山肩椽,在我老家對面澇府邊上蓋了三間大房。當年原上時興取四川媳婦,吃苦耐勞還花錢不多,有句話叫“沒有媳婦下四川,沒有房子進南山”,這兩點讓百世叔都佔著了。後來聽說媳婦身體不好,子女上學,生活很不容易。有一次我回老家閒轉路過他家門前,百世叔一個人坐在門口抽旱菸,摘著從沐浴溝裡剛拔的魚腥草,就說了一會閒話,百世叔說“叔這一輩子命苦,掙得錢不少,都給你嬸看了病”,好在娃們的都大了,分門另住,自己卻捨不得離開澇府沿上的老房子,一直住在這裡,看我看他摘野菜,就說跟娃們的住不慣,又說魚腥草是好東西,清熱解毒,綠色食品,城裡人都吃不上。
還有一次是我回家,其實上了年紀都一樣,喜歡找尋兒時記憶最深的生活點滴,記得小時候生活很苦,難得吃上點好吃的,有一年陽春三月,農民們熬過了過年,盼來了春天;大地年復一年的春光明媚,萬木吐綠,在如今看來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確是貧苦農民最難熬的日子,糧食不繼,青黃不接,唯有大地施點野菜接濟原上的人,母親不知道從哪兒找了一把耳子,就是木耳,用水洗一洗鐵勺放鍋底下籃了一下,吃著非常香,感覺像肉一樣,印象很深。那時的我估計就八九歲,就留意那裡樹上有耳子,便定期採摘,就發現了兩處,一處是隊裡飼養室東邊田先生家的兩顆大皂角樹上有耳子,還有一處就是百世叔家門前澇府沿上一顆不大的構樹上有,每到雨後總要摘上一些拿回家,竟然成了多年的秘密。後來工作了每次回老家,總要看看,後來皂角樹被伐了,就剩下百世叔家門前那顆,幾十年間從小孩手腕粗長到快到碗口粗了,只是那一塊疤痕上的木耳一直還在,年復一年。再後來忽然有一次回老家閒轉過去,不見了那顆構樹,我心裡空落落的,看到門口曬太陽的百世叔,我裝作如無其事的說:“記著你門前曾經有一顆構樹咋不見了?”,他說:“哎,你看我剛砍了,留著也麼啥用,又不成材,把門口罩的不行。”,我一看房子山牆旁邊不遠處果然躺著那顆構樹,葉子尚綠,而且那處長耳子的地方遠遠的正對著我。我說好像這棵樹多年來一直長著木耳,他說就是的,還是你把咱這的事記得清。話是這樣說,卻不知斷了我多年對家鄉草木的一個印記,更何況這棵樹曾經在困難中給了我吃的,算一飯之恩。嘴上不說,心裡卻很難受。轉念一想,在農村到處都是默默無聞的樹木,栽種砍伐也就是舉手之間,自己家裡門前屋後也是栽栽砍砍,隨用而已。只是這棵樹對你有恩而已,已過不惑之年的我早就掩飾住了內心的失落。以後又路過數次,見面問候幾句,不過總會不自覺地看看曾經那顆構樹生長的地方。
其實現在想來我家和百世叔的家有不少相似之處,首先共同的都是當時很窮,再就是百世叔是弟兄兩個,我的父輩也是弟兄兩個,和百世叔拉家常聽到許多父輩和爺輩的事,他總是說“你婆這人好”,說曾經給他過饃吃,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還說那時候我爺爺有打席的手藝,家裡生活能好點;這麼多年常常能聽到我母親唸叨最多的就是百世叔的哥哥養德叔家,說是那年家裡添了老三,家裡生活卻斷了頓,跑了西頭多少家,最後還是在最窮的養德叔家借了點麵粉和雞蛋的,如今母親八十多歲了,也經常說車輪話,翻來覆去的,前幾天回去,說著說著就繞道這事上了,漂母飯信,看來一飯之恩沒齒難忘,現在的年輕人是理解不了的。
百世叔自從搬到澇府沿,就和我母親家離得很近,過去我家這地方是隊裡的最西最南,後來慢慢搬來了幾十戶人,農村都是這樣,低頭不見抬頭見,各人自掃門前雪,大都淳樸厚道和和睦睦,況且現在吃用不愁,就是有點小摩擦也都各退半尺。百世叔一輩子有個愛好就是養鴿子,視鴿如命。我母親上了年紀愛養個貓,這矛盾就來了,經常咬死不少鴿子,就有了點矛盾,每次母親說到這些事我總覺得理虧的還是母親,總勸她,後來她就不養貓了。再後來百世叔年紀大了和兒子住在一起,房子就租給了一個拍抖音的,也是看上那裡的沐浴溝山水和遠處的巍巍秦嶺。
農民沒有退休一說,終生都在辛苦勞作,百世叔也是一樣,早就過了古稀之年,除了農村家常瑣事之外,買了個蹦蹦車,逢二五八前衛集,拉個人補貼家用。其實我們村離前衛鎮不到五公里,是如今寬闊的安亞路的一部分,交通方便,開車就幾分鐘,不過村裡的老人想上集卻不容易,如今的農村大都是留守老人,腿腳不便,一輩子趕集就是個愛好,買不買東西就喜歡趕個集,如今就不容易了,沒了公交,又不想經常麻煩子女,百世叔這個蹦蹦車就最方便和實惠,大家各取方便,惠人利己,大家都不容易。誰曾想天有不測風雲,這寒風中蹦蹦車上抽菸的音容笑貌竟然成了我最後的印記。
有時總在想,一個人的一生總在忙碌著,大到國小到家其實都是一個裡,國是由實實在在的家組成的,家裡的每個人眾生的勞作都在為這個國實實在在的做著貢獻,小道理是娶妻生子,成家立業,大道理是延續民族,富家強國,國與家本就一理,只是如今國家還有國史、地方史,而農村少了歷史傳承,那些曾經屬於農村的文化慢慢泯滅了,沒了村史,斷了族譜,村裡人的家裡基本就剩個神臺;那些曾經代表鄉村文化根址的澇池、老井、村廟都漸漸淡出了歷史,更何況那些終生忙忙碌碌鄉親,好在如今網路方便記錄儲存,是我能透過此懷念村裡的人和事,為他們辛苦地一聲留下一絲歷史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