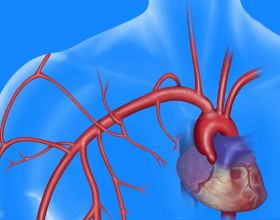電影與旅行常常激發相似的情感,將我們送到過去以及遠方。浪漫旅行電影尤其如此,異國背景可以扮演一個變化無常的丘位元,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對於浪漫旅行電影來說,可能沒有哪個地方像義大利那樣更加讓旅行者和觀眾充滿期待。
羅曼史:永恆之城的承諾
電影中的城市常常與型別相結合。如在倫敦的電影地形學中,東區基本被視為一個前現代的空間概念,吸引了奇幻片與恐怖片導演的目光。與之相反,西區則以浪漫喜劇的形式展現著一個全球化的倫敦。而義大利的城市與景觀因其獨特的韻味被高度讚美,羅馬、威尼斯和佛羅倫薩這樣的城市儲存了這個國家的歷史、熱情與價值觀,其建築遺產延續了一種珍貴的風格景觀,因此被視為浪漫旅行電影這一型別的最佳地點。
一部好的浪漫旅行電影,首先要有一個浪漫的地點。北歐的斯德哥爾摩就不在此列,當這座城市進入敘事時,人們會立刻聯想到伯格曼電影中那些痛苦的人物、冗長的場景和陰鬱的關係。故事的發生地最好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城市,然而也不是所有的陽光城市都適合浪漫。貝託魯奇的《遮蔽的天空》(1990)就是一例,這部攝影優美的旅行電影充滿古怪的大膽冒險,但是北非城鎮的帳篷和有百葉窗的屋子,遠不如托斯卡納的草地或威尼斯的廣場充滿情調。
設定在威尼斯的《豔陽天》(1955),則表現了浪漫旅行電影這一型別的一種幾近程式化的甜蜜場景:一個義大利男子從威尼斯的一條小運河上使勁伸手——他在努力抓住一個美國女子從橋上掉下的一朵梔子花,花溜過他的手。20世紀50年代義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羅薩諾·布拉茲扮演這位男主人公——威尼斯古董小商店的老闆,好萊塢著名演員凱瑟琳·赫本扮演美國中學教師——她為了追尋“生命中缺少的東西”來到威尼斯度過她的第一個夏日義大利之旅。導演是大名鼎鼎的大衛·裡恩,從《阿拉伯的勞倫斯》裡的沙漠、《桂河大橋》裡的森林到《豔陽天》裡的威尼斯,他顯然對浪漫旅行情有獨鍾。
背景中流淌的維瓦爾第與羅西尼的音樂,廣場上的人群、鴿子,咖啡館裡飄出來的卡布奇諾香味,布拉茲為赫本買的梔子花——《豔陽天》展示了所有浪漫旅行電影的基本要素。被稱為“世界上最美廣場”的聖馬可廣場融合了巴洛克與拜占庭等東西方建築特色,主人公之間也存在著不同文化背景結合在一起的所有戲劇性張力,還有一個可愛的義大利小男孩扮演丘位元使者。
事實上,從第一部敘事電影《羅馬之戰》(1905)開始,早期義大利電影就透過重溫這個國家的藝術傳統而確立了自身的國際聲譽,而羅馬的歷史背景在所有城市中是最自然的。因此在20世紀的前十年,一個沒有受到現代工業主義影響的珍貴而“過時”的義大利出現了,這些電影在講述故事的同時凸顯了建築之美與如畫的風光。
到了20世紀50年代,“永恆之城”依然擔綱。《羅馬假日》(1953)再次鑄造了經典。由奧黛麗·赫本扮演的天真無邪的公主,與由成熟的格力高利·派克扮演的記者擁有一段短暫的愛情。這對戀人在這座城市的許多著名景點了解彼此,“真言之口”便提供了一種喜劇效果:記者向公主解釋,可以把人們的手放在石嘴裡測試他們是否誠實,若是說謊,手就會被石嘴吞下。記者將他的手放在石嘴裡並假裝手被石嘴咬住,公主如小女孩一般被嚇著了也被逗笑了。自此,不計其數的影迷前來參觀“真言之口”,重溫這一幕經典場景。隨著假日行進,公主必須回到王室責任中,一個浪漫旅行插曲結束了,但夏日的羅馬在觀眾心中卻成為永恆。
去遠方:自由表達的人格
城市就像人——某些時期代表著其生涯的巔峰。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黃金時代,如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和20世紀40年代的洛杉磯。而在純粹的活力與風格方面,沒有哪個城市能像20世紀60年代的倫敦那樣成為全球年青一代釋放創造力和激情的中心。而20世紀50年代在羅馬拍攝的《羅馬假日》與其他電影,幫助塑造了羅馬以及源自這座城市的“羅曼史”這一術語,也使得義大利成為浪漫旅行電影的首選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國際旅行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去義大利尋找羅曼史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因此電影製片人考慮到跨文化羅曼史的票房潛力是很自然的。不過,有時候文化距離也許會成為破壞浪漫愛情的巨大鴻溝。比如《生死戀》(1955)中兩個人物不得不因“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的文化偏見而爭鬥著。從《叛艦喋血記》(1953)到《南太平洋》(1958),文化的差異有時會對“從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浪漫愛情期許築起一道難以逾越的高牆。
因此,浪漫旅行電影會發生許多主題變奏,如英國的浪漫旅行電影就像英國的很多其他電影一樣充滿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屏障。在背景設置於佛羅倫薩的《看得見風景的房間》(1985)中,一群愛德華時代的英國人保持著喝下午茶的習慣,穿著與當地人完全不同的服裝。然而義大利與英國的差異如此之大,前者的明媚氣候、拉丁風情與後者截然相反,英國人似乎很難愛上超越他們自身身份的人或義大利這個國家。托斯卡納的陽光也不太可能使海倫娜·伯翰·卡特扮演的角色與一個熱情如火的當地人邂逅,只是這個群山環抱的城市為她提供了足夠的文藝復興氣息。
對於旅行者,最冷漠的義大利城市似乎也是威尼斯。如《魂斷威尼斯》(1971)的故事背景便設定在一戰前麗都島上的一個夏天,當地突發瘟疫。義大利電影大師維斯康蒂花了大半生時間,改編這部幾乎不可能改編的諾獎得主托馬斯·曼的小說。一個神經緊張但非常成功的德國作曲家古斯塔夫,帶著喪女之痛來到威尼斯,他一生被理性、完美、平衡與道德所掌控,而一個少年的美使他的感性萌生。古斯塔夫被內心的隱秘情感弄得虛弱不堪,想要離開卻最終死於霍亂。在《威尼斯疑魂》(1973)中,美與死亡再次合謀,徹底挫敗了威尼斯的浪漫。這部電影拍攝的季節——秋與冬,使威尼斯籠罩著陰森而超現實的氣氛,也使主人公的“浪漫之旅”充滿不祥之感。在《熱戀中的布魯姆》(1973)中,男主人公離開洛杉磯的山頂森林,來到威尼斯,在聖馬可廣場摩肩接踵的人群中閒逛,渴望失敗的婚姻死而復生。然而這個傳奇的廣場卻漠不關心,嘲諷著他自我放縱的內心困境。
很少有城市像威尼斯這樣,全然不自知地展現著象徵昔日榮華之物。聖馬可大教堂外立面上的鍍金馬賽克,藝術家天才般的教堂彩繪,商業與征服的戰利品,盛大廣場上舉行歡宴與嘉年華的舞臺,所有這一切都誘惑著電影人,他們如同城市景觀畫家卡納萊託一樣充滿激情地進行創作。然而真正誘人的,也許是這座城市暗藏的憂傷——沒有什麼是永恆的,無論是城市還是愛情。
事實上,對於“什麼是好的浪漫旅行電影”,不同代際的觀眾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上年紀的觀眾喜歡梅麗爾·斯特里普與羅伯特·雷德福主演的《走出非洲》(1985),儘管肯亞的獅群與人物的痛苦也許折損了浪漫;年青一代喜歡伊桑·霍克與朱莉·德爾佩主演的《愛在黎明破曉時》(1995)——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法國人在火車上邂逅並墜入愛河。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這代人有著強烈的主觀意志與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卻遭遇了21世紀初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設定在洛杉磯的當代愛情故事《愛樂之城》(2016),既用“現代生存”改造了古典好萊塢音樂片,也用“現代焦慮”重寫了《卡薩布蘭卡》的經典羅曼史。
旅行者一如進入電影戲劇的觀眾,隨身帶著他們的全部人格。異域之地使人們脫離常規的環境與生活,給予這些人格以廣闊的表達自由。旅行的遙遠與短暫能夠鼓勵我們進行暫時的自我重塑,旅行者可以變成異域城市舞臺上逍遙自在的演員,在肯亞披上獵裝,在遊輪上消遣,或像小說中的間諜一樣潛伏在布達佩斯咖啡館裡。有時浪漫旅行電影中的故事是僅次於現實的最好的事,有時又無疑好過現實。但是隻要浪漫旅行電影存在,旅行者和觀眾就永遠想要自己去探索。
(作者:王田,系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