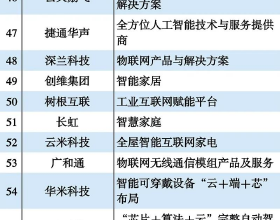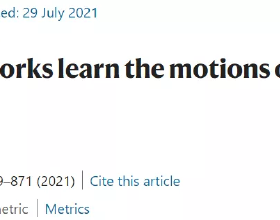最近去了趟非洲,黑人兄弟們給我上了一課,因為,非洲美食可以用奇異來形容。
看過我們《切·格瓦拉的非洲歷險記》的朋友都知道,我對剛果有著很濃厚的興趣,而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踏足這位共產主義唐·吉訶德戰鬥過的土地了。
這片資源遍地、風光旖旎又窮得叮噹響的熱帶叢林,絕對是世界上最魔幻的國家之一。
一離開城鄉接合部客車站般的機場,接待我的朋友——當地的“有力人士”,就僱了名警察把我送去了酒店。
之後的幾天除了四處閒逛,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家典型的殖民地風格酒店中度過的。
每天三點飲茶,不用躺平也很愜意,薩瓦納氣候旱季的大太陽讓人感受不到一丁點兒熱帶的憂鬱。
如同中產階級喜歡模仿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我在酒店裡吃的食物也是剛果“上等人”模仿其宗主國中產階級的標配:西餐。
本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優良作風,在我的強烈要求下,黑人朋友決定帶我去體驗下真正的剛果“人間風味”。
和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在大飯店裡,你只能吃到“面子”上的食物,而世界真正的B面只存在於平民百姓的餐桌或者某個不起眼小館子的後廚裡。

·比如我在黑人朋友家廚房裡發現的這顆蘑菇,差不多有馬里奧那麼大
而剛果的B面就隱藏在它那鬧市區中異常擁擠、嘈雜、髒亂的農貿市場中。
要去農貿市場,步行和騎摩托車是“唯二”可行的交通方式,因為不管你開賓士還是馬自達,都會塞車。
不用真正地走進農貿市場,只要站在它的入口,一種複雜的氣息就會往你的鼻子裡竄。
這是一種混合了烹煮動物和植物油脂的味道,新鮮以及腐敗水果的味道,優質香料和劣質皮革的味道,紅色塵土與黑人朋友的“體香”,魚腥味和下水道的味道。
如果一個香水測評師置身於此,那麼此刻他的鼻子和大腦一定是過載的。
這種氣味兒的“前調”來自於一種黑色的魚乾。
遠遠看去你會把它們誤認為島市老八的主食,但是湊近了你會發現它們大多是某種鯰魚的“木乃伊”。
在這些酷似生物化石的食材中,有些異類會讓你產生一種在挑選異形標本的錯覺。
口感緊實,又散發著腥味兒與碳烤香氣的食物,配合著詭異的外形,足以讓每一個異邦食客產生時空錯亂的感覺:要麼是在吃某種遠古生物,要麼就是在吃某種外星食材。
而配搭這種魚乾的,必須是用5S級壓榨的棕櫚油烹調出的野菠菜濃湯(Mfumba)。

·某歐洲美食網站上的Mfunmba以及市場裡的5S級壓榨散裝棕櫚油
據說,一些已經移居歐洲幾代的非洲人後裔偶爾還會品嚐這種賣相不佳的食物來懷念遙遠的故鄉,但這就像美國唐人街裡墨西哥人做的宮保雞丁,終究是沒有靈魂的。

·而我吃完這碗配著魚乾的濃湯,就與剛果盆地裡人類的祖先——南方古猿的靈魂更近了幾分
當然,如果你覺得濃湯太鹹,不妨去隔壁的攤位上買一隻煮熟的新鮮木薯(Manioc)。
而如果你是一位“嗜臭”的安徽人,那麼這種帶著一絲酸臭汗腳味道的發酵木薯糰子(Chikwanga)可以消解一切肉食帶來的油膩。
如果密集恐懼症患者有地獄的話,穿過市場裡的“乾貨”與“熟食”,在“生鮮區”的每一秒都將成為他們終生難忘的噩夢。
雖然我不排斥蟲子,但是上一次看到用洗臉盆賣蟲子還是在北京的寵物市場裡。
而在國內,不管是東北的繭蛹、山東的螞蚱和知了猴,還是連雲港的豆丹,哪怕是雲南的竹蟲和它們非洲加丹加高原的表親一比,明顯屬於“劣等蟲族”。
一個賣蟲的大哥向我詳細介紹了幾種不同的蟲子。
在這裡,各種蠕動的蟲子統稱為chenille(毛蟲),顏色是區分不同品種的唯一標準,尺寸是影響價格的變動引數。
黑毛蟲屬於大眾爆款,是家中必備的下酒菜。
綠毛蟲更加鮮嫩肥美,崇尚健康飲食的白領可以拿它當作蟲子的輕食版。
紅毛蟲則非常稀有,進補佳品,價格不菲,大概相當於毛蟲裡的海參。
對於普遍營養不足的剛果人來說,蟲子確實是難得的蛋白質來源,北邊的鄰省還搞了一個Kilueka計劃,把蟲子養殖加工變成了規模產業。
不過最後我選擇了一種黃毛蟲,這種大概以玉米為食的蟲子,吃起來也是濃郁的玉米味兒。
雖然我一直認為人類喜歡薯片這類口感酥脆的食物,是源自基因中祖先對燒烤、油炸昆蟲的記憶,但是我的剛果朋友沒有選擇我推薦的油炸方式,而是做了一鍋當地傳統的洋蔥番茄燉大蟲。
但是蟲子裡真正的王者必須是一種被叫作Mposé的白色肉蟲。
這種嬌貴的棕櫚象甲幼蟲通常要放在棕櫚絲中以保證鮮活,而不必像繭蛹一樣忍受火烤屁股的酷刑。
粽子和湯圓都有鮮甜之爭,但只有“刺身”才是唯一尊重Mposé的料理方式。
捏住它黑色的硬質頭部,輕蘸醬汁,讓抖動的身軀在唇齒之間爆漿,淡淡的椰奶香味瞬間就會瀰漫口腔。
但採集昆蟲註定是一種略顯低效且武德不足的飲食方式,只有狩獵動物才是人類進化到食物鏈頂端的標誌。
而市場中的肉類區,註定是個少兒不宜的地方。
哪種食物最美味,這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如果要討論誰吃的食物最“古早”,那一定非剛果人莫屬。
剛果人的部分食譜,繼承了人類的捕食本能,是人類食物史的活化石,也是無人敢爭搶的“老字號”。
而砧板上的猴子就是最好的證明。
風乾的猴子肉,大概每吃一口都能喚醒人類遠古時期同類相食的記憶。
而任何一個剛果叢林之外的人,如果能淡定地吃完一隻猴,都初步具備了成為萊克特·漢尼拔博士接班人的潛質。
如果運氣夠好,你也能在這裡碰到新鮮的猴子,部位任選,整隻購買更佳。如果第二天來還沒賣出去,價格還會腰斬,當然冷鏈儲存是肯定不存在的。

·剛宰殺的動物,只要等待一段抖音短影片的時間,就會成為蒼蠅的樂園
賣肉的大姐強烈建議我品嚐下猴子肉,並告訴我烤猴子肉的味道連小牛肉都無法媲美。
見我面露難色,她道出了剛果人對待食物的樸素哲學觀念:Si ça bouge, ça se mange! 能動,就能吃!
但一想到艾滋病從剛果河流域傳播到美國這個真假難辨的傳說,我還是委婉地表示了拒絕。
剛果的獵人大多是兼職,而上等的獵物往往來自更北方的熱帶叢林。一切進入獵人視野的生物最終都有可能出現在農貿市場裡,即使是剛果河中的頂級霸主也不能倖免。
顯然,這裡的鱷魚擺脫了成為愛馬仕皮包的命運。
但是同為爬行動物,變色龍卻從不會出現在剛果人的餐桌上,在這裡它被一些人視為邪惡與傳染病的象徵。
而井蓋大小的“甲魚”則因為某個外來東方民族的進補傳統而價格飛漲。
剛果盆地每年產出的生猛食材可能高達數百萬噸,對於剛果人來說,這與獵奇或炫耀都無關,它僅僅是一種生存上的考量。
而帶給這片叢林最悲慘與黑暗歷史的比利時人卻把他們曾經的奴隸的飲食習慣帶回了歐洲大陸。
儘管他們嘴上不承認,但這種透過布魯塞爾向歐洲走私野味兒的生意,在剛果人中根本就不是秘密。
結束菜市場裡的“探險”回到非洲友人的別墅,大概是下午三點。朋友家中的打工人沒有飲茶,而是圍坐在門口,就著番茄沙拉、鹹魚還有熱帶的陽光,享用著玉米甜啤(Munkoyo)。
品嚐了一口這種性狀不明的液體後,我只想搞一場吃播,然後發出一聲吶喊:非洲的菜,行!
來源:X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