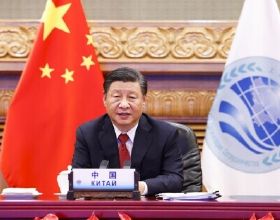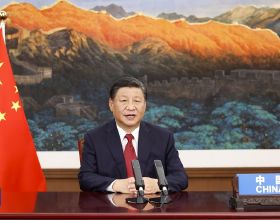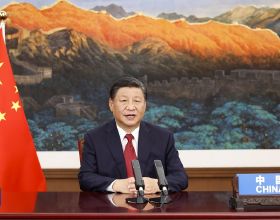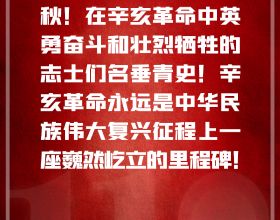(我是喜歡旅行,喜歡記錄的孫九毛。10月初我一個人去新疆旅行,分享我一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事兒,希望朋友們喜歡。)
01
到喀什當天,就遇到一起拼車去帕米爾高原的朋友。
第二天,我們剛剛會面6人一起去高原,分別是司機超哥,小沈,還有婷婷,梅姐,高小姐和我。
梅姐和高小姐之前就出來玩過的夥伴。小沈、婷婷和我,都是單個出來,初次會面的。
02
我們從瓦恰鄉返程的路上,遇到一個塔吉克大叔在路邊招手攔車。
超哥扭頭問我們停不停,我們的車是7座的,還有一個空餘的位置。
我們不約而同地說,載他一段吧!不然他要走到什麼時候,老人家挺不容易的。不過他身上肯定有味兒,讓他坐在副駕駛,反正很快就下車了。
婷婷就從副駕駛上下來,坐在中排,高小姐從中排坐到最後,在我和小沈中間。
塔吉克大叔被高原的烈日曬得一臉黧黑,頭上戴著可以遮住耳朵的翻沿帽,上身穿著咖啡色的加棉夾克衫,下身牛仔褲。
他不懂說中文,連聽都聽不懂。我們給他水,雞蛋,他說謝謝。其他的,問名字?家在哪裡?要去哪裡?全部都是雞同鴨講。
超哥就對他說,前面到了要下車的地方讓他說一下
03
因為做了小小的好事,大家都挺開心。
婷婷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在九年前她到塔什庫爾幹旅行,也是包車,當時五座的車,車上滿滿當當一車的人。
在路上遇到一箇中年男人,他懷裡抱著一個包著褥子的孩子,一看就是很著急的樣子,肯定是孩子生病了,想去塔縣看病。
但是,車上已經坐滿了,再加兩個人肯定不行。他們就沒有停,直接開走了。
可是,九年以來,心裡一直很愧疚。不知道那個中年男人,他後來有沒有搭上順風車,他的孩子有沒有順利看上病。
04
我也想起在6年前,在定陶的時候。當時也是一個冬天的夜裡,那天寒風呼呼地吹著,我穿著羽絨服還有些冷。
我出門拉卷閘門的時候,看到隔壁店鋪門口地上,躺著一個穿著破破爛爛的大叔,地上就鋪著一些廢紙板,他看起來有些神經不正常。
那時候我剛到定陶不多久,褥子、被子都只有一床從家裡寄過來的。
我走進房間,又出來看看。又走進房間,又出來。出出進進好多次,不知道怎麼幫他。
最後,我拉了卷閘門,沒有幫他。
第二天早上起來,只剩下那些破紙板還在地上,大叔不見了蹤影。
六年以來,一直在想,那個大叔怎麼度過那個寒風凜冽的晚上,後來有沒有人幫助他,他有沒有凍壞。
這件事留在心裡,成了永遠的缺憾。
05
後來,我們往前開了半個多小時,到了坎爾洋村,那裡是拍攝《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地方。
這兒是一路上最大的村莊,我們以為他家就在這兒。
結果大叔好像不想下車,他一直說“翻譯”,他想在村裡找個翻譯。隨後,他就下車找翻譯去了。
車上的意見分成三撥,一撥人不想帶大叔,大家出來玩,就是想高高興興,不想再惹出什麼麻煩事。如果大叔有什麼事,我們既然帶上了他,肯定要盡人道主義幫到底。
一撥人覺得反正順路,帶上好了,反正車上也有空位,帶上好了。
還有一撥保持中立,不發表意見。
06
一撥說:“反正他也沒有行李,車上也沒有他的東西,我們就直接開走好了。”
另一撥說:“這樣不太好吧!大叔去找翻譯,回來車都沒了,他心裡多難受。”
一撥說:“誰知道他是什麼人?他身上揹著炸藥呢?”
另一撥說:“怎麼會呢!我們無冤無仇,好心讓他搭車,他炸我們,順便把自己炸死,對他有啥好處?”
一撥又說:“他有沒有手機?做過核酸沒有?把我們一車人都感染了咋辦?”
另一撥說:他就是塔縣下面村莊的牧民,快與世隔絕了,怎麼會有病毒。
“你不知道前一段時間,就是塔縣下面的村莊,有個人感染了新冠,爆發了疫情。”
“在新疆都是一個禮拜做一次免費核酸,總不能把他一個人漏了,再說他已經上車半個小時了,要感染都已經感染完了。”
07
我們一車人正在激烈討論中,大叔帶著一個小夥子過來了。
小夥子估計是他找的翻譯,小夥子說,大叔想搭車去塔縣。
塔縣距離坎爾洋村,還有兩個多小時路程,要和一個渾身牛羊味的大叔坐一起,可能還會遇到各種狀況,是需要一些考驗的。
我說,就讓他坐在最後面吧,和我坐在一起,反正我和乞丐都能坐在馬路牙子上,聊兩個小時的。
最後,我和婷婷坐在最後面,大叔坐在我們中間。
08
一路上,大叔時不時地咳嗽,氣氛突然沉悶,大家都不說話了。有人把窗子開啟一條縫,有人又掏出兩個口罩戴上。
婷婷做出咳嗽的動作,問大叔:”你是生病了嗎?這是要去醫院嗎?
”也不知道他聽懂沒有聽懂,只是“嗯,嗯,嗯……”地點頭。
所有人都沉默了,就算被感染上流感,在三千多米的帕米爾高原發燒,那也是夠受的。
在夜裡八點多,我們順利抵達塔什庫爾幹,大叔也送到目的地。
09
一次小小的搭車,當我們覺得大叔只是短途搭乘的時候,所有人都很高興,因為舉手之勞就能幫助他人。
可是,當我們知道大叔搭車的路程有些遠的時候,那種怕麻煩,怕影響自己計劃的想法,就開始湧上心頭。
這件事,看到兩點。
1、人們都是差不多的,有些同情心,有些熱心腸,也有些冷漠,有些怕麻煩。
2、遺憾,也就是未完成情結。
如果當年我帶著精神病的流浪漢去住了旅館,請他下館子吃了飯。
如果婷婷當年遇到中年男子抱著孩子的時候,她的車還能坐下人,順利把父子送到醫院。
我們還會這麼多年,記憶深處都藏著這件事嗎?
如果我們在坎爾洋不管大叔去找翻譯的事,直接開走,我們會不會在十年後內心負疚呢,我想是肯定的。
(在路上,每天暴走,趕路,晚上寫文章,如果你覺得講得還不錯,分享和轉發,感謝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