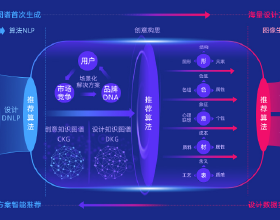前幾日,在英國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
因為名字看起來挺普通,在國內似乎也沒有多少人關注,但其實據有些媒體的觀點看,這可是個重要的會議,堪稱《巴黎協定》簽訂之後關於氣候問題的最重要的會議了。
當然,這個會議的重要既體現在不少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包括美國拜登總統在內,都“踴躍”參了會。當然也可能正好是反過來,因為參會的人“級別”有點高,襯托的會議似乎也重要了許多。
但是,頗為值得玩味的一個訊息是,美國總統千里迢迢飛渡重洋來到歐洲開會的期間,甚至又一次陷入了“拉還是沒拉”的輿論漩渦之中時,其後方卻似乎不是很太平。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斯卡利斯竟然在媒體上對拜登“拆臺”,大有不把總統放在眼裡的意味。
原本美國政治的撕裂,已經算不上什麼新鮮事了,單純從新聞價值的角度看沒有什麼新聞價值了,就像報道“太陽今天又升起來了”這種事情一樣。
但是這個共和黨人的觀點,猛一聽似乎頗有幾分道理,也能唬住一些朋友。既然能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淆和混亂,那麼就值得就此探討一番了。
除去其攻擊敵對黨總統的語言之外,這個人的主要觀點就是:早在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之前,就已經存在“碳排放”這回事了。地球在數以億萬年計算的歷史之中,大氣溫度本身就是在不斷變化著的,有遠比現在平均氣溫高的多的時間段,也有遠比現在低的多的時期,但那時並沒有人的存在。溫度的週期性變化,其實就是大自然的本來面目。
其言外之義其實是說,現在政治家和一些科學家不斷把“碳排放”、氣候變暖、溫室效應的原因定義成人類行為導致的結果,可能是錯誤的。人類活動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別看現在平均氣溫在不斷升高,但地球可能只是處在又一個正常的氣溫變化週期之中而已。
看到這裡,似乎對氣候問題有所關注的朋友,或者是對自然地理有所瞭解的朋友,亦或是親身經歷過什麼自然災害事件的朋友,會覺得這個觀點十分具有說服力。
首先,人類確實很偉大,即使不考慮那種種已然暴露出來的人性缺點,人類的確也掌握了巨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相對於地球來說,人類的力量實在微不足道。
就不說別的,自然演化中很正常不過,也渺小不過的一粒算不上多麼厲害的新冠病毒,就給這個讓人無比自負的人類文明帶來了多麼大的挫敗感,以至於其中的一些發達國家都要“繳械投降”了。
其次,這個氣候變化的週期性,的確是被證實了的科學觀點,並不是什麼民間科學家的臆想,或者是編造的陰謀論。
冰川期的存在是被地質學等科學切實證實過了的。地球大氣的平均溫度確確實實存在著週期性的變化。
因為大氣成分的變化(特別是氧氣和二氧化碳的含量),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几度甚至十幾度、幾十度的時期都確實存在。
那麼看起來,這個人說的就是對的了嗎?
難道“全球變暖”真的就是一個謊言和把戲?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鎖死發展中國家未來發展的“陰謀”嗎?或者就是著名英劇《是,大臣》《是,首相》中揭露的那種“不斷組織各種峰會讓國家領導人出國參加,只是不讓他們去幹擾本國的官僚集團真正去管理國家”邏輯嗎?
肯定不是。“溫室效應”為代表的氣候變化問題的的確確是每個人都應當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
原因當然有很多方面,首先有一個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靜止去比較事物,和動態的比較事物,結論往往是截然不同的。
靜止的去比較,以現在的平均溫度,和地球歷史上的最高平均溫度相對比,確實低的多了,甚至和一些小冰川期的溫度比較,甚至還要低一些,那麼似乎就不需要過於擔心了。
畢竟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總是不太讓人會引起警惕。曾經地球上有過這種平均氣溫,而且太陽現在還在照常升起,就足以說明這件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但其實,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確實地球歷史上有過更熱的時期,但是那個時期適合人類生存嗎?不見得吧,這兩者並沒有必然的因果或是相關。其實由於人類歷史過於短暫,文明史更加短暫,所以根本沒有什麼可以借鑑和自負的經驗。
很簡單的一句話,的確地球有過比現在熱十幾度的時候,以後也會有,這件事的確不稀奇,但同樣對於地球也不稀奇的是,人類不存在於這個地球上這件事。
大氣平均溫度比現在高十幾度如果重演了,但同時人類這種對自然條件要求很高的動物再次消失於這個星球上了,那它的重演對於人類到底是悲劇,還是喜劇呢?不言而喻。
而動態地去比較,我們就很值得警惕這個全球變暖的問題了。
其實,我們並不是主要應該擔心現在的平均氣溫比幾百年前、幾千年前高了一度、兩度,而是要擔心這個溫度的增速太快了。
看似沒什麼,只是計算方式的區別,一個看數值的絕對差值,一個看加速度的變化,但其實性質完全不同。
假如說,地球的正常週期是平均100年升溫一度,但是現在50年就升溫了一度,未來甚至30年就能升溫一度,這就是增速的加速度在提升。
因為這個增速超過了正常,那麼在地球這個複雜無比的大系統的綜合作用下,就會導致出現完全無法遇見的結果。這也是“蝴蝶效應”,系統越複雜,結果也就越不可控。
例如,原本的大氣溫度的增加和降低,都很自然地會淘汰掉一些物種,這是演化論的根本,但因為增速有限,就會給很多物種以適應的機會。
壽命越短、生殖週期越短的生命,透過進化適應環境變化的機會就越多。例如為了適應更高的氣溫,動物可能進化出更多的毛孔以散熱,更白的膚色以反光,甚至類似於爬行動物的特殊的血液迴圈系統等等。但是變化速度加快了,很多原本能夠有機會存活下來的物種,會被急劇的變化滅絕掉,這就會給生物的多樣性帶來災難。
而複雜性通常就是生命對待環境最有力的生存策略,劇烈的變化往往會導致巨大的滅絕。
還有,即使考慮人的主觀能動性,過快的變化,往往也會導致錯誤的模型,錯誤的預期。而無法正確預期,就容易錯誤的決策,錯誤的行動。
例如,原本建立的模型中,伴隨著溫室氣體比例的提升,在大自然平衡的效應下,地球的大氣溫度會有一個上限,那麼人類可能據此做出一個預判,進而進行籌劃和準備,例如開發相關技術,亦或是某種機制約束。
但是猛烈提升的氣溫增速,因為其帶來的不可預見的影響,可能在地球這個大系統的綜合效應下,產生難以預料的結果。
例如原本認為50度就是上限,結果卻可能出現100度的情景,那麼人類為了延續而做的準備可能就變成了巨大的笑話,畢竟你原本準備去考初中數學,結果卻滿頁都是高數題目的話,估計誰都要崩潰的吧。
劉慈欣的《三體》中有過這麼一個情節:人類因為先後見證了兩次“光粒”毀滅星系的太陽,就認為高階文明毀滅低階文明就只有這麼一種方式,於是在太陽系外圍的行星背後建設巨大的太空城市,準備以此對抗文明層面的打擊。孰料“歌者文明”直接用一片“二向箔”就讓整個太陽系變成了二維,幾乎完全徹底毀滅了人類文明。這就是錯誤模型帶來災難後果的一個很形象的例子。
回過來,其實就是一句話,我們不是需要擔心比幾百年前溫度高的那麼幾度,而是要擔心這個增速能不能控制得住。
另外,那個議員的邏輯中,還有一個隱藏的立場問題。他的話,沒有站在人類的立場上去看問題。
的確,對於“全球變暖”這個問題來說,如果站在地球本身的角度看,和站在人類的立場去看,結論也是完全不同的。
站在地球本身的角度,確實溫度的變化沒有意義。在地球幾十億年的歷史之中,最初就是一片混沌的熔岩球,今日雖然孕育了諸多生命,但生命的存在與毀滅對於地球本身也沒有什麼意義。
進而不難理解,平均氣溫地增加多少會造成多少生命的滅絕,是否會導致人類的滅絕,對於地球來說,就是無意義的事情。
但是如果站在人類自己的視角去看,那可就天壤之別了。地球平均氣溫的增加,可不是簡簡單單的讓人類可以少穿幾件衣服而已。
溫室效應導致的海平面上升,雖然不顯得那麼緊急,畢竟把堤壩修高几分,似乎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但極端氣候增加卻已然是不爭的事實。有不少朋友把經常看到什麼動不動“百年一遇”“千年不遇”的水旱天災,當做媒體的大驚小怪或虛張聲勢,其實很多極端的氣候發生的頻率就是伴隨著“溫室效應”的加劇在顯著的增加了。
這些極端氣候對人類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於每個人的福利本身就是會造成直接而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就是切身利益。
對於地球來說,人類的滅亡與否對它並不重要,但對於人類自己來說,地球環境的存亡好壞卻生死攸關。這不難理解。
因為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目前也沒有脫離地球系統生存的能力。那麼恰如溫室效應存在與否、程度如何只是人類自己的事情,與地球無關一樣,環境保護,也是人類自己的事情,與地球無關。
進而可知,環保工作是一項每個人都應當尊重的事情,因為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並且因為是我們自己的事情,那麼我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得更好一點,豈不是更好麼?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每日工作生活之中,做一些對環境更加友善的事情,這並不複雜,也並不困難。
即使現代社會中,個人的排放和工業的排放規模確實已經無法同日而語,但畢竟是力所能及,多做一點就好一點。
我們中國就是如此,我們並不在那裡鼓吹人類應該怎麼做,或者要求別人怎麼做,更不會以什麼“How dare you!”去道德上綁架別人做什麼,而就是踏踏實實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就行了。那消失的沙漠、那新增的森林、那林立的新能源專案,無不解釋著這一概念,我們自己的行動並不需要別人為我們下結論。
即使我們要為一些國家的懈怠和消極而承擔一定的額外代價,畢竟溫室氣體的流動不會在乎那個國界線。
“但行好事,莫論前程”。同時“天道昭彰,報應不爽”,做了好事,自然是能得到地球的報償的。
恰如,那句“我愛你,與你無關”一樣。
我環保,與你無關,與地球也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