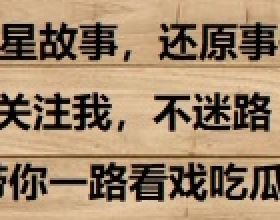精英中精英
阮大鋮的前一段,是一個典型精英式的人物。
他是含著金鑰匙長大的,家世很好,祖上可以追溯到魏晉時期大名鼎鼎的阮籍,到明中期阮家族人也是部長級大官。
他自己也很爭氣,天資聰慧,簡直就是做題家,16歲就中了舉人(范進的棺材板在動?),29歲中進士。
他還是個大藝術家,就拿戲曲來說,他不僅能寫本子,還會演、會導,還能給自己的戲寫BGM(背景音樂),明末有名的鑑賞家張岱就說,阮大鋮的戲真是絕了:本本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要是到現在,估計沒剛子什麼事了。
按道理,就是這麼一個資源、天資、修養都頂尖的人,不指望他像史可法為國為民肝腦塗地,但不能直接投了敵,降了清軍吧?
最起碼也要做做樣子,哪怕是學錢謙益假裝投水自盡以身殉國,然後說水太冷又爬上岸也好啊。
但他投敵投得完全沒有思想包袱,清軍還沒來就在那裡乾等著,甚至可以說是日夜盼著,聽說等不及了還給那邊寫信:怎麼還不來?我等得花兒都謝了。
我們不僅要問:這麼一個精英,怎麼就從好變壞、變質、變節,最後入了《奸臣傳》,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的?
當然,你可以囫圇吞棗的說,這不就是道德水平忒低嘛,道德教育刻不容緩啊同志們。
這是肯定的。
但這個詞兒太大了,框在奸臣頭上可以,框在殺人放火的頭上也可以,甚至框在隨地吐痰、公交車不讓坐人的頭上也很妥帖。
所以這個詞太大太寬了,還得細一點,需要站在當事人的環境中去管中窺豹,這樣或許能給我們一些更貼切的解釋。
申明一下:
我不是來給阮大鋮洗地的,退一萬步講,洗了我都不知道去哪裡收錢,所以沒有動機。且他是漢奸作惡多端證據確鑿,蓋棺定論了。
但如果你硬是要搞幼兒園那套非黑即白,奸臣做什麼都是錯的,忠臣拉屎都是香的,這是你的選擇,我無法可說。
申明完畢。
我們就來看看,這麼一個精英,是怎麼從山頂一路滑到谷底的?
大環境:門裡的小敵人與門外的大危機
一個王朝剛建立時,內部敵人外部敵人,孰輕孰重分得清清楚楚,大家心底有一個共識:
外部敵人威脅度大於內部敵人,內部鬥爭是建立在攘外的基礎之上的。
外部威脅永遠是第一,內部鬥爭排在後面。
這就像兩兄弟吵架,我們倆可以打得不可開交甚至動刀子,但要是哪個愣頭青敢欺負他,我也是要和他一致對外的。
但隨著時間推移,外部勢力逐漸解除,甚至很多很多年都沒有威脅了,兄弟之間的競爭就慢慢上升到第一位,到了以弄死對方為第一要務。
而多年後,當外部勢力再次抬頭,甚至威脅到帝國本身時,思想已無法轉變了——雙方都忽略外部的大危機,還是欲致對方於死地而後快。
此刻,大明王朝的情況正是如此。
頂端的皇帝、下層武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就拿中間這層文臣集團來說,就是這樣的:
先是東林黨壓制閹黨,然後是閹黨反過來搞東林黨,最後是雙方兩敗俱滅。
雙方眼光就像一束鐳射,視對方為唯一敵人,再別無其他——只要你提的建議,不管對錯一概否決,只要是你的人,不管正邪一概打翻。
所有人眼裡,門裡的小敵人永遠排第一,門外的大危機(清軍、農民起義軍)卻排在後面。
這很像很多公司,內耗巨大,大家的精力都在搞內鬥,移個桌子搬個工位都會鬧得不可開交。如果有人想做點事,呸,你是誰的人?
你去外面找陌生人合作都比內部來得順當,且代價還小。如果你身在其中且還有點本事,勸你早點走。
回到今天的主角阮大鋮,他就生存在這樣的環境裡,是文臣集團裡的一員。
正可謂荒唐的環境,造就一群荒唐的人,而他,成了其中最荒唐者。
歷史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山,就是一座山
上篇寫的也是阮大鋮,講他如何高高興興去北京上任,後又被東林黨忽悠了去投靠魏忠賢的閹黨,然後發現閹黨也不靠譜,於是又辭職回家搞他的藝術,這個過程的操作令人歎為觀止(有興趣,文末點選閱讀)。
這一回合,阮大鋮與東林黨結仇。
回去之後的阮大鋮可沒有很老實,他一邊看著戲一邊對北京的局勢瞭如指掌,並揣摩崇禎的心思給在職想要投機的朋友寫了兩份奏摺,讓其見機行事:
1、心思之一:崇禎打一方支援一方。一邊是閹黨,一邊是被閹黨搞殘的東林黨,這第一個奏摺的主題是維護東林黨,打擊魏忠賢;
2、心思之二:崇禎兩邊都不想要。閹黨、東林黨都是木匠的遺老,且東林黨也不乾淨,之前也和太監(王安)不清不楚,這第二封奏摺的主題就是圍繞這個寫的。
確實,崇禎是想幹一番大事的,兩個心思都能立得住,但阮大鋮遇到了豬隊友,遞了第二份奏摺,但崇禎用的是第一種心思。
且這人不僅是豬隊友,還是一個軟骨頭的豬隊友,直接給東林黨招了:不是我不是我,是阮大鋮教我的。
於是,東林黨就起了要往死裡整阮大鋮的決心,但上一篇也說了,阮大鋮做事滴水不漏,只有口供沒有實據。
怎麼辦?
好辦得很,我東林黨乃天下第一,辦個人要什麼實據?說誰有問題他就有問題,沒問題也有問題,說誰是大壞蛋就是大壞蛋,不是也是。
定什麼罪能把人搞得永世不得翻身?閹黨也!
這是一把手崇禎親自抓的案件,只要崇禎不反水、不打自己的臉,閹黨裡的所有人將永不見天日。
那就給阮大鋮定這個罪名。
畢竟,標題醒目、主題鮮明、方便實用、一看就懂,我們一直用它!
於是阮大鋮成了閹黨,處罰是剝去功名、永不再用。
你說此時的阮大鋮有多壞?
還壞不到哪裡去。
但歷史的發展到此,兩黨惡鬥在幾千年裡就是歷史的一粒灰塵,但體現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一座無法逾越的大山,牛叉如齊天大聖,500年也動彈不得。
此年,阮大鋮41歲。
但東林黨不會就此罷休,不會放過他。
舌頭的威力
41歲的阮大鋮這下就回到了解放前,連個秀才都不如,社會地位直接跌入谷底。
但不要緊,我還有愛好,還有藝術,還能組織一個小圈子——中江社,搞一搞詩詞歌賦,寫得好的還能發發朋友圈。
這一發朋友圈(出版書籍)不得了,另一個站在東林黨一邊的復社看到了,你一個閹黨,一個沒有功名的底層,你應該在家老老實實的,怎麼可以再進入文化圈,發朋友圈的質量還比我們好,告訴你:不!可!以!
你們這些和阮大鋮搞在一起的秀才舉人還有沒有點廉恥?還要不要自己的名聲了?都給我散了。
中江社就此散了,大家都不和阮大鋮玩了。
沒辦法,家鄉是待不下去了,那我就去陪都南京,那裡的人不怎麼認識我。去了南京的阮大鋮大受歡迎,這裡文人的數量多質量好,而阮大鋮又有錢又有才還養了戲班子,一時間好不熱鬧,比在家鄉的動靜更大了。
這下復社更火大了,閹黨的人要不被殺、要不被流放,剩下的都是夾著尾巴苟且著,你阮大鋮不僅沒苟且,還大搞詩和遠方,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滿大街給阮大鋮貼大字報,什麼亂臣賊子、什麼閹黨該死,大家不要和這個敗類玩,孤立他遠離他,不要被他汙染了。
鋪天蓋地的“文字獄”威力極大,阮大鋮只能又離開南京,躲在郊外的一個荒山上,惹不起我就躲,算是真怕你們了。
這是1638年,阮大鋮54歲。
悠悠眾口讓這個自恃清高的人竟無立錐之地。舌頭真是個神奇的器官,本是人身上最柔軟的部分,但卻能把人打得骨折筋斷、肝膽俱裂。
有時,我們真的不知道狠話、謾罵、指責的威力,農村那些喝藥的農婦,近期那個喝藥的學生,那些寧願捱餓受寒離家出走頭也不回的孩子... ...。
舌頭就是一把尖刀,請善待身邊的人。
當眾羞辱
到深山就到深山吧,但他自認還是一個知識分子,這一天城裡搞祭孔大典,阮大鋮也去了,也要祭拜祖師爺。
你想,這裡來的全是讀書人,他的“光輝事蹟”就是這些讀書人茶餘飯後的大瓜,流傳度堪比前一陣竹籤凡。
他這一去,很快就被認出來了,你一個閹黨,一個沒有功名的人,怎麼還好意思跑來和我們站在一起?還有臉來祭孔?
打!給我打!
阮大鋮本來有一副非常漂亮的鬍鬚,群毆之下竟被拔得精光,一根不剩。
這是1643年,阮大鋮57歲。
這十幾年阮大鋮就是這麼過來的,但這個過程中他有妥協過、有認輸過、甚至討好過沒有?
有!
比如他聽說復社領袖侯方域是青年才俊,秦淮八豔裡有個漂亮姑娘與你很相配,我出錢給你做妾,好不好?
但跪舔也不行,熱臉貼了冷屁股。
得勢後,就做一件事
鐵柱磨成針,機會來了。
崇禎上吊南明開張後,他使錢透過另一個奸臣周延儒(東林黨)又混進了南明朝廷,後又扶持朱由崧在南京當皇帝,最後做到了兵部尚書,此時就兵部還有點實權了。
過程就不說了,得勢的他並沒有招兵買馬、去北定中原,權力在手的他就做一件事:
出那口壓在心裡幾十年的惡氣,把東林黨當做頭號敵人,打擊、報復、迫害,從個人恩怨來說,這個過程確實很爽。
但帝國僅剩的最後一點元氣,就此被他弄得消耗殆淨。
南明被他搞沒後,他投降了清軍,其實也沒有得到什麼重用,整天和最底層計程車兵在一起,說自己有多牛,什麼我是兵法世家、什麼我運籌帷幄、什麼我的戲倍兒棒... ...
不禁讓人想起老電影《唐伯虎點秋香》裡的臺詞,牆外的人說:
“對不起,我是低等下人,是不能進來的。”
牆裡面的人說:
“哎呀,我哪裡有把你當低等下人了?我只是把你當狗而已。”
無語
到此,我不知道你作何感想?
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說,“看歷史人物,你只有回到他當時所處的情境裡,讀懂了他選擇中存在的哪怕一丁點兒合理性,你或許才算走近了這個人。”
歷史滾滾向前,那些鮮活的生命慢慢演變成一個個標籤,忠臣、奸臣、佞臣、好人、壞人、庸人... ...
但如果你停下腳步,扒開外衣一看,竟是滿眼的無奈。
(完)
相關文章:阮大鋮:即便是奸臣,我還是忍不住為他的城府雙擊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