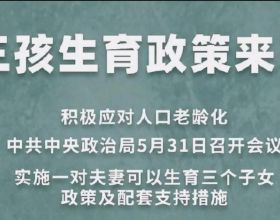光線昏暗的樹林裡,我感覺母親就在不遠處,可是我怎麼也找不到她。撥開樹林,所到之處無不荊棘密佈。突然隱約傳來一陣有節奏的牛鈴聲,“叮噹”!“叮噹”!我張嘴大喊,卻怎麼也喊不出聲音;我拼命的奔跑,可腿腳不聽使喚,再怎麼用力也跑不出一步。耳聽著牛鈴聲漸漸遠去,我急得大哭起來。
又做夢了。
窗外月光如洗,又是好幾天沒給母親打電話。一看手機,正是午夜,得等天明瞭。
怎麼又做這樣的夢?不知母親近來可好?
我再不能入眠,輾轉反側,思緒任性地乘著黑夜的翅膀,飛越幾百裡,回到故鄉,回到那個曾經翻越過無數遍的小黑腦包。
故鄉拖克壩子三面環山,受內陸季風性氣候影響,終年缺水;聽老輩子人講,大躍進時期大鍊鋼鐵,砍光了山上的樹木。土地貧瘠,地裡只能種植糧食作物玉米洋芋和豆類,以保自給;經濟作物只有烤煙。烤煙需要大量的燃料,由於缺乏煤炭資源,我們地方的燃料是山上那些當年留下來的底矮的雜木樹,偶有一些長得快的青松和棵松,又屬於護林保護資源。所以,我的家鄉,還缺燃料。
煙火人間,離不開水和燃料。人畜飲用水,要靠雙肩去山溝裡挑;農民的工作,除了地裡的耕作點種,春播秋收,還有去山上拉柴拉草。
農忙時節,農民們起早貪黑,收割點種;農閒時節,男人們趕著牛車,拉柴拉草,有時還拉水。女人們則聚在一起,打打毛線,納鞋底做布鞋,手巧的繡花鞋墊……手上飛針走線,嘴裡家長裡短,日子過得滋潤而悠閒。
母親也會這些女紅,可她沒空享受這種悠閒,她得像男人一樣,去拉柴拉草。
母親是拖克壩子第一個趕牛車的女人。
那時父親是村幹部,得整天守在村公所值班,可微薄的工資養不活全家,母親得種地栽煙,維持生計。我們姐弟四個,大的正是讀書年齡,小的嗷嗷待哺。家裡要柴沒柴,要草沒草,母親幾番掙扎,套上牛車,每天翻山越嶺,早出晚歸,拉回一車車柴禾,生火、烤煙,或者一車車落葉,積肥、墊圈。
母親主內又主外,每天都要像陀螺一樣,不停地轉。雞叫頭遍,母親就悄悄披衣下床,先去山溝裡擔上四五趟水,把水缸裝滿;然後牽牛喂草,劈柴攏火,煮豬食,做早飯。如果是假期,她就可以不做早飯,飯菜弄好後圍著火堂放好,蓋上碗蓋,以保我們放學回來還能吃上熱飯。
下午五六點鐘,差不多我們放晚學回家的時候,母親也就趕著牛車回來了。
叮——當!叮——當!
晚歸的小黑牛步履蹣跚,晚歸的母親也步履蹣跚。步履蹣跚的母親,強撐著拄起車夾杆卸了牛,又雙手抱著夾杆,輕輕放下頓好車,顧不上洗把臉,又開始家裡的又一輪忙碌……
等到假期,母親就會多一個小幫手,這個小幫手常常是我。我不愛在家裡做飯,太繁瑣了,我做不好。我總是以我力氣大可以多幫母親一點忙為藉口,跟母親上山溜達。姐姐身材小巧,又心靈手巧,會做飯,又可以照顧好兩個弟弟。所以她留守當家,我跟班上山。
那時,我們上山,必經小黑腦包。
小黑腦包。顧名思義,就是坡度陡得像腦門,從下往上一看,總是黑黝黝的讓人心生懼意的一個小山包。從山腦包下來那段路,是一段碎石路,陡,筆直。是一段讓人掉魂的事故多發地段。
路難走也就罷了,我家的牛膘肥體壯,野性十足,就像十多歲的男娃,愛抵架。若在路上遇到迎過來的牛,那廝牛頭一壓,屁股一抬,牛尾巴一夾,四腳一收,“哄”一吹鼻子,箭一般就朝對方奔去。遇到陡坡,它也從來不會耐著性子一步一步穩穩地走,而是撒開蹄子狂奔。直到把車掀翻在地,韁繩絆住受了束縛,才不得不吹著鼻子停下來。
村裡人都勸母親換牛,可她捨不得,她說牛通人性,遲早它總會乖順的。慢慢地,母親摸索出一套辦法:恩威並施。她學別人的樣,給牛套上鼻索,如果牛勁上來,只要一提鼻索,套索處一疼,牛就老實了。如若又在路上抵架,則拉回來牢牢拴在木樁上,去竹林裡砍根竹棍,邊朝死裡打邊問:給還抵架!給還抵架!只打到牛低下頭,眼神也變得乖順,方才罷手。抵一回打一回,抵一回打一回。幾次下來,在路上又遇到牛,那廝終於只吹吹鼻子出口笨氣,再也不發足狂奔了。每天拉柴草平安回來,母親就攪拌一盆包穀面餵它,以示獎勵。遇到青草季節,母親還常常在路上逮空摘把路邊的青草餵它。慢慢地,我家的小黑牛終於被母親馴服了。
可生活永遠不可能一帆風順。
那是一個雨天,雨不大,但淅淅瀝瀝一直下,吃了早飯都沒有停的跡象。雨天路滑,母親本想休息一天,可烤房裡的煙要轉大火,需要大量的柴。
母親套上牛車,輕輕摸著牛耳朵,說,下雨不好走,你可要聽話。然後扭頭對我說,今天你就別去了,跟你姐在家。我不怕,我要跟你去。我固執地跟在後面。
這種天氣,我怎麼放心讓母親一個人去呢。
雨中砍樹,枝頭上的雨水抖落,濺得我們一頭一身。滴著水的樹杆,好不容易扛上肩,就又滑下來。淋了一天雨的活柴,分量比平時重了不知多少倍,母親抬著樹幹的三分之二處,我抬著樹尖,一根一根把扛來的活柴抬上車,差點沒把最後一絲體力掏空。
溼透的衣褲,黏答答地裹在身上,飢寒交迫,我懶懶地抱著雙手,蜷縮成一團,蹲在車旁,看著母親把牛皮索的一頭拴在車身的左前側,理著索子繞到車身後部,在最後一條橫欄的中間繞一下,又拉著索子的一端,整個人撲在車底,翹著屁股,頭貼在地面望向車底,從車底下勾住車樁的一端,又從右側把索子與剛才布好的索子相扣,右側一拉,在柴禾的中間就成了個十字,最後雙腳蹬著左側車輪,雙手扯著牛皮索。整個身子掛上去,雙手拉著索子,索子就使勁往下提,直到整個人即將倒掛在車上,索子又拉出了一大截,再也沒有一絲鬆動,母親才在一側打了個活釦,那時雨已停下。母親臉上汗如雨下,可她根本顧不上擦一下,麻利地從地下撿起一根紮實的雜木樹棍子,在索子上下一撬,左右一旋,又打了個棍子扣。這才算綁好了柴,裝好了車。
母親看看瑟瑟發抖的我,憐愛地摸摸我的頭,脫下她穿著扛柴的厚布褂,穿在我身上,默默去牽了牛,架上車,我們終於踏上了回家的征程。
路面泥濘,一不小心就打滑。母親提著牛鼻索,與牛肩齊,走在牛的右側。我跟在牛車後面,雙手拉著車把,在平路上雙腳一縱跳上車,讓車帶我一截,如果有坡,又是一縱,跳下車跟在後面走。
眼看就到了那給我們帶來過無數次麻煩的小黑腦包,母親拉站了牛,回頭叫我不要跟在牛車後面了,隔遠點。並囑咐我,下坡時千萬不要靠近她,更不要靠近牛。
我聽話的停下來,看著母親和牛車漸行漸遠,才反應過來,這是到了最難的那段了,母親是怕我在旁邊如果出現意外,她顧不上我。我幾步追上母親,在與她平行時我沒停下,繼續往前跑。
我幾步跑下陡坡,停下來回頭遠遠睄著母親和牛車。只見母親提起牛鼻索拉站了牛,順順牛尾巴,抓抓牛的耷拉皮,又摸摸牛耳朵,像是在跟它嘀咕什麼。牛先是一本正經的樣子的聽著,然後搖了搖鈴鐺,那神情像是一個調皮的孩子,在對母親做出一個聽話的承諾。
母親看看遠處的我。確定我在安全距離之後,輕輕一提牛鼻索,輕輕吆喝了一聲“駕!”
得令的牛,一步一步穩穩地朝前走起來。看著它這樣乖順,我稍微放了心,眼神卻還是不敢移開。突然,只見一個打滑!
譁!
母親,牛,和牛車都失去了控制,溜冰一樣極速向下飈去,一直飈……
媽——!
我嚇得魂都掉了,哭喊著往回飛奔。當快要接近牛車之時,我再次驚呆了。
我驚喜地發現,冪冪中似有神助,小黑牛死死踩住一個從土裡露出半截的圓石頭,穩住了身子,鼻孔兀自噴著粗氣,脖子下的鈴鐺隨著晃動,正在有節奏地響著,叮噹叮噹叮噹。驚魂未定的母親,面無血色,形容委頓,雙手掛在夾杆上,半吊著身子,雙腳癱軟在地,
突然發現我站在她面前,母親像是突然得到神助,一下子站穩身子,生氣地吼到:
叫你不要過來!
邊說邊下意識地忙去牽牛鼻索,突然又發現牛正乖乖站著喘氣,才又把頭靠在夾杆上說,天啊!老天保佑啊!差點命都沒得咯!說完喘了兩口氣,一挺身站起來,扭頭再次摩挲著牛耳朵,輕輕道:剛才嚇死我了,得虧你沒有亂跑,回去獎勵你一大盆包穀面。
牛扭扭耳朵,搖了下鈴鐺,叮——當!
母親說了聲“駕!”見我還在原地傻傻站著,臉色煞白,又把牛拉站,邊嘴裡嘀咕著:背時了!怕是嚇掉魂了!邊朝我這邊大聲道:
“小老二,快走回家了!小老二!黑了晚了,快走回家了!”……
聽母親喚著我的小名,我如夢方醒,像是真的還了魂似的,趕緊朝母親和牛車走過去。母親一手拉著牛鼻索,一邊脫下她身上的褂子遞給我說,披著快走,天都要黑了。不要怕!這不都好好的嗎!我木然地跟在後面,不知怎麼走回的家。
那之後,我病了一個星期,母親每天都是把飯做好,給我吃了藥,交代姐姐照顧我後,就又匆匆趕著牛車出發了。母親走後,我躺在床上,一遍遍回想著那驚心動魄的一幕,真擔心母親又發生意外。可我實在沒有力氣陪她一起去,也不可能勸她休息幾天,因為烤棚裡等著燒柴。在提心吊膽的等待中,每當夕陽西下,又聽見牛鈴叮噹,母親差不多總在那個時候又回來了。我的心才又放下。慢慢地,我不再那麼擔心,身上也慢慢有了力氣。我不允許自己再這樣軟弱下去。是每天幾乎定時響起的牛鈴,喚回了我的魂魄,是母親用行動告訴我,人,不能受一次驚嚇,就永遠不站起來。生活總要繼續,我們,只有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