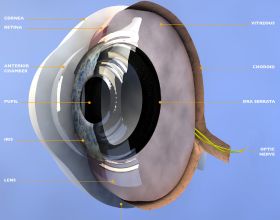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他們把女的當啟蒙物件,寫女的玉潔冰清,看不到女人的複雜性。涓生給子君講雪萊的時候,也許子君正在想,你準備一直住在這個會館嗎?將來又要如何維生?男的完全看不到女的內心,但偏偏對女的外表很重視。白流蘇比子君更小市民,但更有女性的表現。”9月,在上海蔦屋書店題為“張愛玲筆下的愛情戰爭”的活動上,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這樣比較張愛玲與五四時期愛情小說的不同。
如他在《許子東細論張愛玲》中所說的,五四愛情小說諸如魯迅的《傷逝》、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創造》都有戀愛與啟蒙合一的模式:在戀愛故事當中,男主通常是老師,女主經常是學生,男人代表知識分子,女人代表大眾,男女戀愛的背後是憂國憂民的大問題。
張愛玲的寫法與之不同。《傾城之戀》裡白流蘇雖然聽不懂詩經和精神戀愛,但盤算未來結婚、找房子、找女傭還是她說得算。張愛玲看見的是涓生沒有看到的生活細節,女主不講精神戀愛、歐洲文學,關心的反而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許子東說,這是女主人公覺悟的一次降低,也是女性主義創作的飛躍。張愛玲的寫法又與流行的言情小說迥異,她並不像鴛鴦蝴蝶派或後來的瓊瑤、張小嫻一樣主張男女真情衝破世俗壓力,寫世俗壓力細節與現實世俗束縛中的浪漫情感,她寫女人尋找男人是為了“飯票”(《傾城之戀》《留情》),同時他們之間的愛情又是存在的,只不過這愛千瘡百孔,並沒有脫離世俗和功利。
活動上,許子東又由張愛玲的作品出發、提出了從晚清延續至當代小說的兩條線索,一條是青樓的家庭化,另一條是家庭的青樓化。所謂青樓的家庭化,指的是從晚清狹邪小說延伸出來的情節模式,在青樓裡尋找愛情,而非片晌歡愉,“比方《海上花列傳》和《孽海花》等等都寫一個官員喜歡誰就贖出來納妾,愛得深了納妾還不行,還要明媒正娶,魯迅說這是在寫人倫,我說這是‘青樓家庭化’。”這一線索可以在郁達夫的《秋柳》中看到延續,小說講主角到江南某地教書,常去一個妓院,他要找一個長得不好看的、年紀大的、還帶著孩子的妓女海棠,說“救國就是從救海棠開始”,仍是在延續青樓的家庭化。而串聯狹邪小說與五四小說的重要轉折點就是《老殘遊記》,《老殘遊記》用一頓老殘、縣官和妓女的酒局,開啟了知識分子救妓女同時講究憂國憂民、民生疾苦的模式。
至於家庭的青樓化,許子東說,張賢亮《綠化樹》裡寫一個女人綽號叫“美國飯店”,她幫助落難的知識分子,跟他說“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小說評論通常講這表現了知識分子在困境中得到了勞動人民的幫助,可是這位“美國飯店”在村裡有多個男人,綽號“美國飯店”本身就代表著其腐化和墮落,她就是那個年代的“紅塵女子”。家庭青樓化的另一個更典型也晚近的例子是賈平凹的《廢都》。《廢都》中用十幾頁的篇幅來書寫莊之蝶和眾多與他發生關係或者即將有關係的女人的一頓飯,“明明是寫家庭,可是寫得像青樓一樣。”而居於青樓家庭化與家庭青樓化當中的,就是張愛玲的《第一爐香》——葛薇龍的姑媽既是家人又是青樓班主,她的家也是家庭與青樓的高度結合。
在活動結束之後,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對許子東進行了採訪,由張愛玲對五四愛情模式的反抗,聊到了可以由《第一爐香》為線索串起的當代小說,包括賈平凹的《廢都》和蘇童的《妻妾成群》。許子東也重新解釋了為什麼需要重視餘華作品“很苦很善良”“讓人掉眼淚”的部分,以及《平凡的世界》為什麼仍然是無數由鄉鎮到城市的文青的“閱讀聖經”。
01 張愛玲的寫法是對五四啟蒙愛情故事的反抗
介面文化:剛剛在講座上,你提到了五四文學的愛情模式與晚清時期比有一個變化,例如男性與女性的關係變成了《傷逝》中的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係,而張愛玲的寫法是與這種模式不同的。張愛玲是如何不同的呢?
許子東:五四文學的愛情小說模式我們比較容易理解,講的是男的愛女的、男的教女的,男和女是教和救的關係,從文學型別上講第一個層面是愛情小說,第二個層面是教育小說,第三個層面是啟蒙小說——啟蒙和喚醒大眾是五四文學的基本主題。這類小說通常把女性當做大眾來看,男性假定自己是知識分子。這個模式一定程度是從晚清小說的模式發展過來的,轉折點就是《老殘遊記》,在晚清以前男和女通常是才子和青樓女子的關係,因為沒有其他的可能;女的能夠欣賞才子,是不甘墮落有靈性的,這是晚清青樓小說的基礎,到了五四就轉變成了我剛才講的愛情啟蒙主題。
這個模式延續到之後很久,甚至在今天都有可能出現,甚至不單是小說裡,就是在日常愛情裡,女的都希望找到一個男的能夠在精神上高於我——或許女的不一定這麼想,但一個男的不能在精神上提供一點什麼東西,女的就會看不起他;當女的要求男人在學識、文化和精神境界上有她可以欽佩的地方,其實已經中了五四愛情小說模式的影響。
這種模式可以上溯到明清小說甚至更早的名妓故事,現在一路發展到當代小說,如果承認這個是主流,那麼像丁玲、蕭紅和張愛玲就是一種反抗的藝術,她們不是簡單地盲從,而有自己的選擇。但說回來,張愛玲的男主人公也還是比女主人公高的,首先男的都還是要有點錢,第二有點海外的背景,是混血兒或僑生,象徵著對另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好奇和嚮往,女的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是像魯迅小說裡那樣只是被教或等著被救,她很快就清醒地看到男的弱點,跟男的還有博弈,這就是這幾位女作家的作品為什麼好看的道理。
介面文化:博弈的意思是作品裡的女性基於自己的處境去觀察和調整自己在愛情裡的地位?
許子東:不管她是基於什麼,簡單地說,她既希望男的文化和經濟上比她高,但是又不甘於被男的啟蒙教育和保護。她要麼是出於現實的原因,必須要爭奪,像是《傾城之戀》裡的白流蘇,我乖乖跟著你不理我,所以我一定要爭得一個主權;或者說我本來就比你強,像丁玲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女性一開始就覺得兩個男的都不如我,總之不安於男作家所寫的愛等於教和救的模式。女作家形成什麼模式呢,很難說,她們是在挑戰那個主要的模式。這個主要模式的力量之強,楊沫《青春之歌》還是那樣,雖然林道靜是革命戰士,找男人最後還是找共產黨人江華,餘永澤不好因為他相信胡適,江華死了之後我再找一個共產黨人盧嘉川,表面是革命文學,其實道理是一模一樣的——男人給她領路,她不怕犧牲,不是為錢,也要跟著這個男人。
雖然故事很多不一樣,但基本的模式是貫通的,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這個模式有一個古典文學的基礎,有一個青樓文化的轉折。很多人不願意承認這點,但那個時候不是妓女沒法談戀愛,這不僅是小說的情況,也是社會的情況。我作為一個男的要向女的講戀愛問題,只能去青樓。
02 正因為假設女人在農村一直善良,所以要寫她進了城就會被毀掉
介面文化:剛才講到了青樓文化在愛情小說模式中的影響,你在書裡也專門講到,青樓的情節模式可以把當代許多不同作品聯絡起來,比方說《第一爐香》和蘇童的《妻妾成群》、賈平凹的《廢都》,這要怎麼理解呢?
許子東:當代文學和晚清文學本質上已經變化巨大,但有些故事的基本模式竟然驚人地相似,我透過這些相似的現象發現,《第一爐香》在其中有一個轉折的作用——它一面接上了晚清的鴛鴦蝴蝶派,發表在周瘦鵑的雜誌上,是“鴛鴦蝴蝶派”的尾聲;另一方面又和丁玲及許多男作家幻想的局面有所關聯。當然,這是批評家的解讀,不是作家的有意,說實話,把青樓傳統和二十世紀愛情小說連起來講的人本身就很少。
介面文化:順著這點來說,“家庭的青樓化”就是你將《妻妾成群》與《廢都》聯絡起來的相通之處?
許子東:這兩部作品的相通之處就在於滿足讀者——尤其是男讀者——的白日夢。其實不單是男人的白日夢,也引發了女人的白日夢,像是宮鬥劇。《妻妾成群》的主要矛盾照理說應該是男人跟他的女人之間的矛盾,但這個矛盾被淡化了,主要矛盾變成了兩個:女人之間的矛盾——你們看宮鬥劇就是看這個嘛;在這層關係之後還有丫鬟的矛盾。女人跟女人鬥,背後是權力政治的鬥爭。《金瓶梅》寫的就是女人的鬥爭,古人評說人難以齊家。
介面文化:我以為白日夢指的是很簡單化的處理,將無法滿足的願望用一種輕鬆的方式在文字中實現?
許子東:白日夢絕對不簡單,白日夢是你自己不知道的夢,將你無法滿足的願望透過你不知道的方式給滿足了。所以我評價《廢都》,賈平凹也未見得意識到他在寫什麼,為什麼他要把一頓午飯寫兩萬字?莊之蝶的老婆、情人、保姆在一起吃飯有啥樂趣?很多評論家只會評九十年代風氣很差,知識分子沒有責任心、道德墮落。廢話。每個朝代都有道德墮落,問題是為什麼要這樣墮落。
介面文化:你之前比較過三個不同的女性形象,《第一爐香》的葛薇龍、《日出》的陳白露和《啼笑因緣》的鳳喜,你認為,對她們的墮落的不同寫法影響了讀者對她們的同情。為什麼要對比三個不同的女性形象?
許子東:所有的現代文學,凡是寫城市的,核心故事一定是一個女性的墮落。在舊社會任何一派都這樣寫,只是寫法不同。
我將這多種不同的寫法概括為最簡單的三種。一種是她的墮落是因為社會不好,沒有責任,我們同情她,這就是陳白露的故事。第二種是社會不好,女的也有責任,前前後後有因有果有報應,這是通俗文學的寫法,她吃喝玩樂住豪華賓館最後不幸是作孽活該。第三種是張愛玲這樣的,只寫前面,像是葛薇龍好端端一個人明知道事情不對,怎麼會一點點走進去,至於這個社會好不好,她不討論——因為在她看來,社會總歸是不好的:不要說過去不好,未來照樣不好;不要說中國不好,美國照樣不好。張愛玲認為這是人性的問題,墮落無處不在,主要是人性如何克服自己的貪慾和虛榮。貪慾和虛榮是人性支撐點,把這兩個抽掉之後人性怎麼辦,這就是張愛玲。
當代文學大概都可以歸到這三條線索裡,用最粗淺的方式概括就是:革命文學、左派文學教育我們社會腐敗,通俗文學主張有因必有果,張愛玲則是警惕人性本身的弱點。當然,這種分類是文學史的做法。
介面文化:那為什麼都是關於墮落的,而且是女性墮落的呢?
許子東:這就是男性作家或者說社會文學視野的焦點與侷限,就像陳白露的故事為什麼要寫妓女,因為這是熱點題材;人們為什麼關心女性墮落,這後面都有白日夢。寫良家婦女在家裡燒飯帶孩子是寫不下去的,非得出軌了才能編故事。
另外,城市跟農村最大的區別是,城市裡的人的身份變化多,農村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所以還有一種寫女人的方法,就是鄉村題材的方法——寫女人善良,她無論遇到什麼事,男的打人或賭博,她就是永遠善良的,永遠不發牢騷的,扶助丈夫撫養孩子,這裡面最典型的就是餘華的《活著》。
善良的農村女人和墮落的城市女人這兩者之間是有關係的,正因為假設女人在農村一直善良,所以要寫她進了城就會被毀掉,所以城鄉文學也是互相有關係的。沈從文對此看得很通透,他覺得農村的女性墮落了也比城裡太太要好,墮落了也是很淳樸的。
03 中國人的故事很苦很善良,作品受到持久歡迎必有民意基礎
介面文化:你之前在評價餘華時說,他的小說寫的人都是很善良又苦難,讓人掉眼淚的。“讓人掉眼淚”的苦難是很高的境界嗎?
許子東:這是最受大眾歡迎的寫作,餘華寫的時候未必有意。餘華是職業的作家,能夠寫不同型別。張愛玲也試過寫不同型別,但歸根到底只能寫那些她熟悉的事。餘華也有現代主義的寫法,但為什麼《活著》是最成功的?我們要研究的不是餘華,而是中國老百姓為什麼喜歡這樣一個故事,要研究大眾的興趣。
在《鏘鏘行天下》裡,我評價過餘華的寫作“很苦很善良”——“很苦”是有很多的共鳴,“善良”是大家又有希望。在中國,不苦很開心是膚淺的,沒有什麼人家真的像《活著》寫的那樣一家死掉八個人,但都能理解遭災遭難,有什麼事可以這樣銘心刻骨?共鳴之後還能給大家希望,這個希望也不是虛的,不是說明天會更好。以書裡的例子來說,是主角把女兒送到人家家門口,用手摸摸女兒的臉,女兒十來歲不懂也不哭,也用手摸摸爸爸的臉——通俗的寫法一定是女兒哭抱著不肯走,餘華真的厲害——爸爸的臉被她這麼一摸,就不讓她去了,抱著小孩就往回走,走了很久女兒發現不是去那一家的路,又把爸爸摟緊了。
這個細節給人的感悟是什麼?就是雖然中國人這麼多年吃了那麼多苦,但是總可以拉住家人的手,家人沒有背叛,經歷這麼大的災難,傳統儒家道德沒有丟掉,這就是共鳴,官方也喜歡老百姓也喜歡。在西方的宗教裡,上帝是阿拉,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救贖;中國人的宗教就是自己的血緣和家。《活著》銷量這麼高,我想,持久受到民眾歡迎的作品必有正能量在。所以我寫《重讀二十世紀小說》就專門找那些銷路好的小說,因為這些小說有民意基礎。
介面文化:和《活著》相比,餘華最新出版的《文城》是不是更苦更善良了呢?
許子東:《文城》不一樣,除了女主角以外,其他人都是神話般的、非常虛假的、很不現實的。但《文城》的大突破在於一個女的同時愛兩個男的,前面寫小美帶著老公的使命去騙別的男人、去偷錢,但是又產生感情,還生了孩子。一個女的真心地在兩個男的中間掙扎,很少會有作品這麼寫,很多作品寫的都是一個男的在兩個女的身邊掙扎。
作品的整個寫作過程很叫人失望——作家先寫前面,隔了六七年再寫後面,有些地方是經不起推敲的。餘華老寫好地主,主人公都是好地主,很有錢,善良得不得了,土匪都壞得很絕對,我們大部分的作品寫土匪也還是有好的地方。
介面文化:說到選什麼文學作品的問題,你在音訊節目《21世紀中國小說》裡選入了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這是一部非常受歡迎的作品,但它並不是通常意義上認為的純文學?
許子東:晚清小說我還選了《玉梨魂》,這是最早的鴛鴦蝴蝶派,代表了民眾最喜歡的東西。《人民的名義》也是,它拍成電視劇多麼受歡迎,裡面還有官員形象——除了知識分子和農民之外,官員形象是現代文學第三大主要形象,路遙《平凡的世界》也寫了很多很多官員。
我們文學界有個誤解,評論家不討論官員,好像一討論就是批評,其實也不是這樣的,《平凡的世界》《喬廠長上任記》也有歌頌。不光評論界,作家也覺得寫官員就是主旋律,覺得自己低了一等,好像蔣子龍不如餘華莫言。我就是要打破這個觀點,《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寫官員都寫得非常好,是一流作品。作品只有寫得好不好,沒有人物的高低。
04 吃飽了閒著才有張愛玲的痛苦,吃不飽飯的時候不看張愛玲
介面文化:之前說餘華的作品“讓人掉眼淚”,這是不是一種從大眾審美出發的標準?
許子東:文學史研究按理說不考慮作品的銷量,作品銷量多不代表藝術上好;但另一方面,如果銷量能夠加以時間因素考察,如果一本書在五年、十年甚至幾十年裡都暢銷,那性質就不一樣了,說明民眾集體有意識或者無意識認可這樣的作品,或許它就代表了一時的潮流。比如《紅巖》的上千萬(印數)代表了革命教育;比如《家》不僅是巴金的個人想象和創造,也代表了好幾代中國人對家庭關係和代際進化論的想象,簡單說就是,比覺新大的都是不好的,比覺新小的都是好的;年紀大的都是壞的,年紀輕的都是好的。作品被接受不是文學,而是歷史。
很多圈內人乾脆不提《平凡的世界》,我認識的很多作家現在還是說這個書不怎麼樣,我不這麼看,它從過去到現在銷量持續上升,至少說明它的基本讀者小鎮青年進入了讀書市場的主流。八十年代大家看城裡人下鄉,看阿城、韓少功、王安憶;現在是鄉下人進城佔主流的時代,農民工進城,小鎮青年買書是主體,所以《平凡的世界》影響三觀。李敬澤就跟我說過,餘華和路遙對現在的青年影響最大,為什麼呢?因為讀者群的變化。八十年代讀書的是知識青年,現在讀書的可能是小鄉村小鎮來的文青。他們進城站住腳了、買房結婚生子了,照樣做文青,這時候《平凡的世界》就說出他們的心聲。
從這個角度來說,張愛玲作品的持續熱銷就跟中國的城市化有關。過去半個世紀,中國城市人口從百分之十幾增長到百分之六十,張愛玲主要適合於城市人看,裡頭講的愛情的負面、勾心鬥角、虛榮心跟貪慾,相對都是城裡人更具有的。過去張愛玲的作品在哪裡風行?臺灣地區、香港地區、上海,現在可能在武漢、南昌,人們吃飽了閒著才有張愛玲的痛苦,吃不飽飯的時候不看張愛玲。有人說讀張愛玲是小資情調,其實是讀者生態發生了變化。
介面文化:小資情調也是一個有趣的詞,你在書裡也重點分析了張愛玲的小資與小市民觀念。
許子東:張愛玲在《童言無忌》裡寫人朝思暮想想買一個東西,臨到了櫃檯還在猶豫。我讀了以後感到震撼:這不是在講我嗎?我就常常這樣。她說有錢人是沒有這種煩惱的,窮人也沒有這種煩惱,這種拘拘束束的快樂就屬於小資產階級。她把小資和小市民混用了,寫小市民就像紅的綢布條貼在我的胸前。她寫作的背景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當時革命興起,小市民成為普遍的負面概念。沒有一個作家說自己是小市民,說自己是工人、農民、軍隊或流氓的都有,就是沒有人說自己是小市民,張恨水都不說自己是小市民。而張愛玲拼命鼓吹自己小市民,小市民是社會的主要動力,這背後有一套歷史觀,跟五四革命的主流是不一樣的。
在《自己的文章》裡,張愛玲說,五四以來是寫超人的,我是寫常人的;他們是寫超越的、革命的,我是寫和諧的;鬥爭是一時的,鬥爭是為了平平穩穩過日子,這是常人的目標。她的社會觀、政治觀、歷史觀跟當時的革命觀念不一樣,而恰恰是現代的發展所肯定的(觀念)。《中國的日夜》就能體現她的想法,中國的前途是在菜市場買菜的打著補丁的小市民,她的讀者也是社會年輕的主流而不是落後的“小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