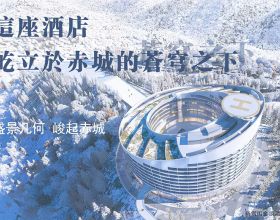草臺戲
文/爾也
在荊楚腹地的天門、京山一帶,草臺戲由來已久,是幾千年來鄉民的主要文化娛樂活動之一。
每逢年節,抑或某大戶人家的喜慶吉日,或在街頭巷尾,或於灣間村頭,以竹木為支柱,以木板鋪檯面,請來戲班子,唱個三五天,這下子成了戲迷粉絲們大飽眼福的極樂盛宴。有的奔走相告,邀朋約友;有的心花怒放甚至神魂顛倒。有個流傳了幾百年的“筲箕‘嘎’(放)反了”的笑話,就是對這些饕餮之徒極為形象生動的調侃。據說有個年輕的當家主婦,是遠近聞名的花鼓子迷,村裡搭臺唱戲了,高興的歌聲連天手舞足蹈。中午飯後開鑼,這婆娘猴急火燎,為了不耽誤看戲,提前燒火做飯。漉(過濾)飯的時候,心裡想著戲 ,嘴裡哼著花鼓腔,如痴如醉,心不在焉,竟把盛飯的筲箕放反了,一瓢“飯生子”倒在了筲箕背上,不斷地往地下“垮”,戲迷卻渾然不覺。這時,隔壁三媽來借東西,一見其狼狽狀,大聲驚呼:“筲箕‘嘎’反了!”這婆娘如條件反射似的立即轉過身來吃驚地問道:“啊!花鼓子臺輾(移動)了?”神魂顛倒,答非所指,依然沉浸於即將開鑼的花鼓戲中,生怕花鼓子臺轉移了,……這個笑話,如飽蘸濃墨的彩筆,幽默而輕鬆地描繪出了農村女人對草臺戲的痴迷。
我的媽媽也是一個戲迷,解放初期,她帶著我四處“趕場子”,不知看了多少草臺戲。儘管似懂非懂,但豐富多彩的鄉土文化,於我則如藍天上篩落下的一縷陽光,滋潤了幼小的心靈,刺激了文學種子和美學意識的萌發。
草臺戲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草臺戲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就是開鑼前要“跳加官”,作為祭神祈福的點綴。為什麼要跳加官呢?這就是幾千年來的一種文化遺存。草臺戲是由社祭發展起來的,我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從新石器時代起,一直到夏、商、週三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尊重土谷之神,正是農業文化的一部分。出於對土谷之神的崇拜,將一年的春、秋兩季看得十分神聖、莊重,這就使“社祭”具有極強的群眾性和社會性。起初,社祭用的“犧牲”,人們不敢與神分享。後來人們覺得把這些新鮮的整豬、整羊棄之太可惜。於是巧立名目,將“社肉”稱為“福肉”,祭祀結束,即將“犧牲”分而食之。同時將蛇酒稱為“福酒”,俗謂飲了“福酒”可以治耳聾。於是,每逢祭祀,人們便可大開胃口,盡興而足。唐朝詩人王駕的《社日》裡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當是人們食“福肉”飲“福酒”後醺醺之態的生動寫照。草臺戲中的“跳加官”保留了對土谷之神的尊重。
上古時期的社祭,到了中古,已由單一的祭神,發展成多元性的群眾歡聚盛會。地處江漢平原的古鄖國,山水秀麗,物阜民豐,社祭尤為盛行。古鄖城所在地石家河,就出土了好幾個祭壇,與其說是祭天祭地的神壇,倒不如說是萬民同樂唱土戲、“跳大神”的草臺。孔子對百姓們的歡聚曾表示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在孔子《家語.觀鄉》中,他回答子貢說:“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的社祭之於祭天祭神已日趨淡化,實際上成為了群眾性的歡慶豐收的娛樂活動。
唐宋時期,社祭除保留殘存的“樂神”古風外,還注入了“樂民”的生動內容。詩人陸游在《遊山西村》中寫道:“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可見春社將近,笙簫鼓樂已齊集高奏了。詩人范成大寫道:“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悉記,大抵以滑稽取笑。”
到了明清,社戲便從社祭中發展出來,成為民間主要文化藝術活動。著名學者焦循,在他研究地方戲曲的專著《花部農譚》中,這樣描述鄉土戲曲活動的盛況:“郭外各村,於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夫,聚以為歡,由來久矣。”社戲演出期間,他自己則“每攜老婦幼小,乘駕小舟,沿湖觀閱。”
所謂社戲,在我們家鄉就是春、秋兩季在廟臺、土臺、或用竹木臨時搭建的舞臺上演出的戲曲,俗稱為草臺戲。魯迅先生筆下的“社戲”亦如是。有些有條件的墟集,場口還建戲樓,如漢川垌冢,天門胡市就有很著名的戲樓,鍾祥石牌鎮的戲樓一直儲存到現在。戲樓大都建在古廟附近,過去天門東南西北四個大廟都建有戲樓,亦稱草臺。
由於草臺戲具有明顯的時令特徵,符合農村的農事習慣,深受廣大群眾喜愛。草臺戲期間,人們像過年過節,邀約親朋好友歡聚,話豐收,敘家常,其樂融融。戲場更熱鬧,立市交易,買賣搭棚,飲食小吃,紙花糖人,風土物產,應有盡有,表現了農村的勃勃生機和盎然情趣。
小時候跟著愛看戲的母親,看了不少草臺戲,有村旁路口掩映於楊柳扶蘇中的土臺,也有廟前街後臨時搭建的簡陋舞臺,印象最深的是在西堤街廢棄的火神廟場地上看的草臺戲,因為這一次我見到了平時人們津津樂道的“攻么臺”。唱的什麼戲全無印象了,唯有“攻么臺”記憶猶新。快要“么鑼”散場的時候,突然鞭炮炸響,黑壓壓的人群像潮水分流迅疾地向兩邊分開,被擠倒的,被踩著的,哭喊聲,叫罵聲一片混亂,都以為發“妖風”了。向後一看,只見一長溜隊伍,頭戴紅帽子,身穿黃背褂,抬著整塊的豬肉,大罈的白酒吆吆呵呵向舞臺邊擁去。這時臺上的戲停了,敲鑼打鼓迎接,班主拱手相迎,給抬東西的人發紅包,好不熱鬧。這時戲雖然看不成了,卻看到了一次從未見過的“攻么臺。”
“攻么臺”是鄉民或者商家、族眾對劇團、特別是名角表示的尊重,“攻”了“么臺”後,就把班子請到他們那裡去唱戲,表示下了“定錢”。有時候,幾處“攻么臺”的都來了,你爭我搶,互不相讓,甚至發生械鬥。
沈山的班子到外地演出,也經常受到“攻么臺”捧場。聽解放後在永興落籍的天門胡市藝人方靖國老先生講,1946年,沈山班子到永興王場演出,也是熱火朝天“攻么臺”,時任國民黨京山縣政府參議員的永興人曾習孔送上了一副嵌有“沈山”名字的捧場對聯:
沈吟人間冷暖能叫滿堂中改顏變色;
三伏世態炎涼直使術臺下酸鼻痛心。
(注:“沈”通“沉”;“三”與“山”諧音)
很有特色,說明了天門花鼓在周圍影響很大。同是古鄖國屬地的京山草臺戲也十分興旺。
光陰荏苒,斗轉星移,倏忽間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一時間宣傳毛澤東思想、最高指示如疾風暴雨鋪天蓋地而來,幾千年來散佈於神州大地的千千萬萬個草臺,成了宣傳偉人思想的絕好陣地。原來新老結合兼唱花鼓戲的各大隊文化室,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吸納了眾多新鮮血液。宣傳隊員在光照模糊的夜壺燈光下,手捧紅寶書死勁地蹦躂。那誇張的動作,那撕心裂肺的口號,那虔誠膜拜的“敬祝”“萬歲”,似驚雷貫耳,如海嘯震天。不由得使人“一閃念”地想起了古人祭天地鬼神的社祭……
人乃高等動物,除“三飽一睏”外,尚需精神寄託。卸卻戰天鬥地“促生產”的勞作風塵後的社員,為了打發長夜的寂寥,也攜兒帶女,提燈籠打電筒,翻山越嶺,齊聚於大隊部黃土壘成的土臺邊,或坐或站,等候開鑼。看似接受教化,實際上是放鬆一下疲勞的筋骨,獲得一種莫名的滿足。

作者下鄉插隊的何畈大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後排右三為作者(1969年)
那時的宣傳隊員的水平略高於文盲,讀錯唱錯是常有的事,老百姓稀裡糊塗,似懂非懂。比如一首歌裡有“好像那,旱地裡下了一場及時雨呀,心眼裡頭熱乎乎哇……”社員們鸚鵡學舌,唱成了“靠牆啦,旱地裡就是要有一點雨呀,新堰裡頭不熱乎哇。”鬧了笑話。
有一次,沔陽毛嘴大隊到永興交流演出,舞臺上,女報幕員一身草綠色軍裝,臉抹的像猴子屁股,登臺就是一個戰鬥姿勢的精彩亮相,以普通話夾雜著土話報幕:“沔陽縣毛嘴區毛嘴公社毛嘴大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現在嘎事嘎事(開始)!”一連串的“毛”叫人剎那間轉不過彎來,突然又被土掉渣的“嘎事嘎事”引發鬨堂大笑。人們獲得了一次堪比《何業寶寫狀》還愜意地暢快,老百姓不懂什麼思想和藝術,只要高興就行啊……
現如今,文化大下鄉,各個村的土臺早已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扶貧宣傳隊自帶的以汽車為載體的組合式輕便舞臺,加上電腦控制的天幕和電子器樂,跳著陽春白雪似的老百姓看不懂的什麼霹靂舞、扭屁股舞和那蹦蹦擦擦的音樂,之於文化藝術素質亟待提高的普羅大眾,有如外星人的群魔亂舞,臺上熱熱鬧鬧,臺下冷冷清清。倒是一些商家的開業慶典,請來的天門、仙桃的鄉劇團在街頭草臺演出的天沔花鼓似乎更受歡迎,臺下萬眾聚集,人頭攢動,喝彩聲不斷,仍然保留著過去草臺戲的喧鬧……
草臺戲,這一由古老社祭演變而來的民間文化活動,在楚風鄖俗依然殘留的故鄉永遠有自己的市場。
(本文參考了範齊家先生的《草臺戲溯源》,謹表感謝。)
202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