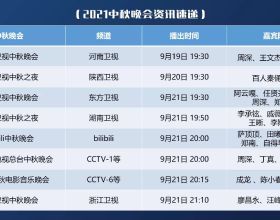郭佳語讓我給她的店想一個名字,這事兒被我拖了整整一個月也沒有結果。說實話這不能怪我,主要是她的店讓人實在不好界定。郭佳語這人從小就心比天高,做什麼事情都想一舉成名。之前她說要休學開店的時候我們勸她別這麼異想天開,結果她還是倔著性子休學在校門外砸重金租了挺大的一個門面。
她是半個富二代,早年她爸投資辦廠失敗,錢全部賠光了,沒多久她爸媽就離婚了,她跟他爸。那個時候我們住在一個大院裡,人多的時候她跟所有人一樣說說笑笑,但只有我們倆的時候她就沉默很久然後說她想她媽媽,很想很想。彼時我們還是十歲剛出頭的孩子,我能明白她內心的荒涼與渴望卻不知道怎麼安慰。上高二時她爸東山再起,生意做得順風順水,沒多久她們就搬去了市中心,在那裡住很大很豪華的房子——當然這是聽別人說的,她沒有告訴過我,我也沒有問過。我看著大院裡空掉的房子,看著我旁邊空掉的桌子,總會很難過。
在大學裡看到郭佳語時我驚訝得老半天沒說出話來,我想我當時的表情一定很精彩,不然她不會傻呵呵地看著我笑。最後我終於從興奮中蹦出一句話來:“咱快去買六合彩吧,晚了五百萬就飛了。”那天我們曠了課去吃火鍋,當然那鍋一上來我們就後悔了,因為這裡是四川,不是我們老家廣東。最後我們吃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給我們端冰水的服務生都煩了,一次給我們端上了六杯,他說:“你們先喝吧,不夠再叫。”
離開餐廳沒多久我們的肚子就給出了光榮曠課的理由,兩個女生在街上捂著肚子找廁所,找完廁所找藥店,最後躺回寢室裡那張不夠溫馨但安全的床上時已經筋疲力盡。我發誓再也不吃火鍋。
之後我們經常在咖啡店小清吧一類的地方聚會,她偶爾也會帶上她的男朋友。
郭佳語的店裝修好之後我去看過。她說:“怎麼樣?有範兒吧?”我往四周仔細觀察了一會兒,說:“不錯啊,還真沒辜負你學了這麼久的設計。不過這格局看起來怎麼這麼奇怪呀?你到底想開個什麼店?”郭大設計師領著我在店裡邊轉邊說明:“這一片是咖啡吧和小清吧,安排得比較小,我想這個還是為來這裡休閒聊天的人準備的,萬一誰臨時想要喝杯咖啡什麼的就不用出我這店了。這一片是書吧,你看這個沙發,坐上面看書絕對舒服,對了,這幾排書架你幫我安排一下。這間屋子是琴行,有人幫忙照看。這兒打算安排幾臺電腦,誰臨時有什麼事兒就用,免費的。怎麼樣?我還是有那麼點頭腦的吧?”
我說:“聽起來是那麼回事兒,但以後會怎麼樣誰都不知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對了,租這麼大個店,你得花多少錢啊?”郭佳語的臉色變得有點奇怪:“多少錢?反正是我爸出,他不是有錢麼?他不是鼎鼎有名的暴發戶麼?”我聽出她語氣裡的意思,剛想勸勸她,她又說道:“算了別管這個了,上樓,樓上還有,給你個驚喜。”
上樓的時候我在想,驚喜就免了,別驚悲就好。她開門,挺大的一套房子,她開啟其中的一間屋子對我說:“以後這間屋子就歸你了,裝了隔音板的,你寫小說啊看書啊沒有人能打擾到你,心情來了嚎兩嗓子也沒有人告你擾鄰的。”
我連忙說不用,我用不著這麼好的房子。她說:“其實就是讓你來幫幫忙,我怕找不到合適的人。而且你住這裡也能熱鬧一點不是。你不會不幫我這個忙吧?”我說那當然不是,你的忙我肯定幫,但真的不用安排房間。
她說:“這點小意思啦,你也別拒絕。過來,看看我的畫室,我打算收一些學生。”我被她拖到了另一個房間,擺放著整齊的畫板、顏料、畫紙。她的男朋友陳雋逸正在畫一張油畫,明亮的色澤掩飾不住厚重的質感,嫻熟的筆法將一片片顏料近乎完美地搭配起來。我和郭佳語站在那裡,靜靜地看著陳雋逸畫畫。
我問郭佳語:“你就打算這樣開個店一直做下去?”她盯著陽臺上一盆長勢很好的爬山虎,沉默良久,緩緩地說:“其實我也不知道,但總要先找點事情做,以後的事兒以後再說。對了,幫我的店想個名字吧。”
後來我給她的店取名為“水色時光”,其實它作為店名有點牽強,讓人不知道是做什麼的。郭佳語非常高興地自己設計了招牌,淡藍色海水之下,“水色時光”四個字長出交錯的藤蔓,是協調的嫩綠色,周圍泛出大大小小的水泡,陽光斜斜地打下來。
“水色時光”正式掛牌時已經營業了很長一段時間,絕大部分的人都是我們從學校里拉來的。漸漸地,不用我們拉,也會有三五成群的人來店裡,一坐就是半天。校園裡也能偶爾聽見有人說:“走,去郭佳語的店裡坐坐。”
郭佳語週末教幾個高中藝術生畫畫,樓下交給做兼職的甜甜和做全職的景添負責。甜甜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大一,勤工儉學,找了好幾份兼職,聽她說週一到週五就有三份家教工作。景添連續兩年高考失敗,都是離重點線不到五分,不想復讀,又不想去一般的大學,就乾脆出來找工作了。
我把宿舍裡的東西全部搬到了“水色時光”的樓上,擺放在郭佳語給我安排的屋子裡。沒有課的時候我會在“水色時光”裡幫幫忙,其實也沒有多忙,找找書,遞遞咖啡,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我在沙發上看書。這些書是我和郭佳語在網上訂的,送貨上門,貨車開到店門口,兩個搬運工來回搬了二十多分鐘。我們在店裡忙著拆箱子,清點,然後分門別類放上書架,五個人整整弄了半天才弄好。新書的香味很濃,把咖啡都蓋過去了,我們坐在沙發上看著一整架一整架的新書,傻笑著。
週一到週五生意不是很忙,郭佳語也不用教畫畫,她和景添兩個人就行。晚上我回店裡時,景添已經下班,我陪郭佳語看店到十一點左右。陳雋逸會在上完晚自習後回來,和郭佳語打鬧一番,然後拿出夜宵,有時候買多了也會送一些給常來店裡的客人。
週末客人比較多,郭佳語負責畫室,甜甜負責衛生,景添負責吧檯,我幫客人找書,琴行交給一個師兄幫忙,給客人試音、挑選。那個師兄是我們在一次藝術節上認識的,後來聽說郭佳語開店,自薦來幫忙,他提的條件是讓郭佳語贊助他的樂隊,說好以後樂隊能賺錢了會分紅。我私下跟郭佳語說起這件事兒,我說別對以後的事抱太大的希望。她笑著說賠錢也沒有關係,現在追求理想的人太少了,能幫一把就幫一把。
兩個月下來,郭佳語說賺錢了大家去吃一頓。我們去了海鮮店、大排檔、小吃街,郭佳語是想拉我們去吃日本料理的,但我們都知道他這個店要賺回本錢都要花很長時間,就拉著她在人群裡擠著搶各種小吃。其實如果真的把我們帶去吃日本料理,我們倒會因為不會吃什麼弄得很尷尬。小吃好吃又便宜,樂得自在,當然開心。
然後我們去了那個師兄的樂隊,在城南的一間地下室裡。我記得看過的小說和電影裡這樣的地下室一般都潮溼並且骯髒,到處是菸頭和酒瓶。真正下去後才發現不是那樣,很乾淨,樂器擺放整齊。我們都是第一次看到樂隊的其他成員,有著和師兄差不多的氣質。那天晚上他們演唱了很多首歌,有安靜的校園民謠,也有激烈的搖滾。午夜的街道,眾人四散。我記得那晚的星光格外明亮。
暑假,學校一下子就空了,回家的回家,旅行的旅行。郭佳語的畫室裡擠滿了學畫的高中生,不得已,將書櫃推到了一起,沙發搬到樓上,騰出空間來做畫室。陳雋逸在樓上教,郭佳語在樓下教。咖啡吧裡生意好了很多,多半是高中的甚至是初中的小情侶們。
我成了唯一沒有事情做的人,偶爾有一兩個人來看書時招呼一下,後來這工作也被小昕代勞了。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房間裡看書寫東西,要麼就是倒在床上神遊四海。有一天我發現我的窗戶推不開了,跑到陽臺上才發現原來那樣栽到花盆裡的爬山虎長勢太好,已經覆蓋了很大的一片牆壁,把我的窗戶遮了。
隔天便借了很高的腳手架,爬上去把我的窗戶剪出來。看著被剪掉的爬山虎,總覺得有些過意不去。那扇窗戶我再也沒有關過,任爬山虎把推出去的窗板慢慢遮蓋起來,爬到我的視線裡來。
夏日的陽光總是那麼漫長。午後一兩點的時候是沒有客人的,大家聚在空調下聊童年、理想,聊一些細碎無章的話題。也有時候各自打盹兒,以此抵抗外面洶湧的熱浪以及枯燥。
郭叔叔來過一次,出差到成都,順便看看我們。郭佳語的態度很冷,除了必要的話不肯多說一句。郭佳語不在旁邊的時候郭叔叔就唉聲嘆氣,他對我說幾年沒見你都長這麼大了,停了一會兒,又自顧自地說,也對,和佳語同齡嘛。我從他的臉上看到無法掩飾的哀傷。
郭叔叔走了之後我問郭佳語:“你難道真的不打算原諒他?”她盯著杯子看了很久,說:“其實已經原諒他了吧,他那個時候一心做事業也是為了讓生活好一點,只不過不如意罷了。但是,不知道怎麼-—可能是習慣了-—就是做不到。”
暑假要結束時我們給郭佳語過了生日,陳雋逸買了很漂亮的蛋糕,插上蠟燭讓郭佳語許願。一屋子人都玩瘋了,奶油弄得到處都是,然後醉了累了就擠在沙發上睡了一覺。
高中生們開始補課,“水色時光”又恢復了原來的格局,但因為大學開學比較晚,整間店都很冷清。郭佳語說有一個美術比賽,她和陳雋逸打算參加。
有一個好訊息是師兄的樂隊開始在酒吧演出了,而旦反應很好,正式從地下走到了地上,是在離“水色時光”兩條街的地方。那天我們早早地關了門,拉上一些老主顧去給師兄捧場。環境比較雜亂,正準備登臺的他們看上去很興奮。
場內靜下來,吉他撥響,樂器的聲音隨即如颱風過境般降臨,震懾人心。快節奏的搖滾一首接一首,很好聽,但也能看到師兄他們滾落的汗水。但我想他們是幸福的吧,那麼久的努力得到認可,並且還能帶給別人快樂。
最後一首歌由在場的觀眾點,景添被幸運地抽中。他點了首《同桌的你》,算是幫師兄們保留一點體力等待狂歡。
他們下場後酒吧老闆走了過來,笑嘻嘻地說:“不錯不錯,以後每個週六晚上來,專場,價錢好商量。”然後讓服務生送了幾箱啤酒過來。
時光就像這個店名一樣,簡簡單單清清淡淡地向前滑。我們早已習慣這樣的生活,時而忙碌時而清閒,和一群朋友在一起,感覺很好。
不知道是我反應遲鈍還是什麼原因,我居然是最後一個發現的。甜甜和景添一閒下來就坐在一起聊天,隔挺遠看,景添比比劃劃的,甜甜笑得很開心。忙的時候他們也會照顧對方。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平時甜甜沒有來的時候景添老是發呆出神。
我是在經過郭佳語的點醒之後才觀察他們的。某天他們聊得很開心,我無聊,想湊過去一起聊,郭佳語一把把我拉問來,她朝天花板上明亮的日光燈眨了一眼。第一個瞬間我沒有弄明白,第二個瞬間我恍然大悟。郭佳語小聲說:“現在你是店裡唯一個單身的了。”
大四開始後不久我就去實習了,是在城市的另一端的一家報社。每天都要穿越最繁華的東西向幹道去上班,擠在洶湧的人海里,走在自己的路上,卻總是莫名奇妙地覺得沒有方向。
實習生就是廉價勞動力,這在我上班的第一天就成了真理。辦公室裡的人都把各種各樣的活兒往我身上推,然後在自己的桌前慢悠悠地喝茶或者咖啡。
我挺害怕這樣的生活,公式化,日復一日,我相信時間一長我就會被它打磨得像一顆光滑的鵝卵石。17路公共汽車,報社旁邊的小花園,擁擠的人流,不斷重複的工作,相似而又陌生的臉孔,每天都一樣的日程表。我一想起這些就會在腦子裡想象出一條漆黑的無盡頭的巷子,一腳踏進去就永遠沒有走出來的一天。
有時候會被叫去做採訪的工作,採訪那些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詢問他們的成功經驗。心裡是止不住的噁心,因為受訪者滑稽的姿態,開會一樣的談話,以及橫飛的唾沫。
我的輔導員安排我做三個月的實習,彙報工作感悟同時寫畢業論文,然後就可以準備畢業了。我想等我把這三個月做完,把最後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混完,我就必須得像所有的上班族那樣過日子了。我們總有一天會變成我們曾經討厭的那種人。
“水色時光”的生意依舊不錯。我說:“你還真是塊做商人的料。”郭佳語說:“你應該說我做什麼都是塊好料。”我喝完一口咖啡,說:“現在打定主意了沒有?是一直做下去,還是回去準備接手郭權叔的產業?”
郭佳語又一次沉默了,每一次提到這個問題她都要沉默,她說:“我只怎做自己喜歡的事。”
實習結束前主編找我談過話,他說:“你畢業後就應聘到我們報社吧,我們都很看好你。”我嘴上說著“會好好考慮,謝謝關心”一類的話,心裡想的是立刻就能離開這個地方的興奮。原來我也已經學會了口是心非圓滑處世。
秋天一點點被落葉覆蓋。
師兄的樂隊漸有名氣,參加了一個比賽,一路過關斬將,殺到了最後的三強比賽。比賽的前一天郭佳語收到了一封郵件,是那個美術比賽組委會發來的,通知她兩個星期後去上海參加現場複賽。
我說:“得,你們都有事情幹了,都邁到夢想面前了,哪像我,夢想還在天邊掛著。“郭佳語安慰我說:“別急,一步一步來,你還怕到不了嗎?”
我們去給師兄作親友團,在人海里尖叫狂呼。後來我在一個轉瞬即逝的鏡頭裡看到-臉興奮的我,那樣子就像自己的夢想實現了一樣。
師兄的樂隊拿了亞軍,和一家唱片公司簽約了。那天午夜我們回“水色時光”開香檳,把大廳弄得一片狼藉。我記得恍惚中誰說了一句話,似乎是“夢想原來這麼觸手可及”。
那以後師兄就不常來店裡了,他有了新的目標,併為之奮鬥。
郭佳語也在著手準備比賽,但是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因為陳雋逸沒有收到複賽通知。那幾天我們都在祈禱,祈禱陳雋逸能和郭佳語比翼雙飛。陳雋逸非常沉默,大部分的時間都把自己關在畫室裡畫畫,我們不知道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怎麼樣。
最後的希望被複賽名單剿滅,上面沒有陳雋逸。他得知這個訊息的時候非常平靜,坐在椅子上喝水,然後站起來擁抱郭佳語,他說:“你要連我的那份一起努力。”我們安慰說“那個評委年紀大了眼神不好,你別怪他”“評委是看你太有才華了怕你以後搶了他的飯碗,所以才不敢讓你去”。
然而郭佳語最終也沒有去成。她接了一個電話,然後收拾東西,還讓我幫她訂回廣東的機票,越快越好。我問她到底怎麼了,她說她爸爸中風,情況不太好。
臨走時,她說“水色時光”就麻煩大家幫忙照看一下。
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不停地給她打電話,問情況。幾天後郭叔叔的情況好轉,郭佳語坐飛機回來,我們給他接風洗塵。她把所有的人都叫齊了,坐了兩大桌,她站起來說:“來,為我們最後的晚餐乾杯。”大家都有點疑惑,但也都早有預感。她繼續說:“不好意思,我要回去了。水色時光也要關門了。”
第二天開始陸陸續續地收拾東西,進門的顧客都挺驚訝的,因為這個店的生意一向很好。收拾東西的時候我們都不出聲,怕引起不必要的尷尬。
看著空蕩蕩的屋子我就有一點難過,郭佳語正在把牆上的油畫一幅一幅取下來,她的動作很慢。
學校組織了最後一次出遊活動,目的地是川西高原,看巨大的原始森林,高大的山,還有一個剛開發出來的冰川。那個冰川遠遠看上去讓人感覺走到了極地,寒冷一陣一陣侵襲。
再回成都時原本的“水色時光”已經變成了一家服裝店,琳琅的服飾標著令人驚訝的價格。郭佳語離開的時候我正在看冰川,其實我可以推掉學校的活動,但是我害怕離別的場景,害怕我會不由自主地哭出來。
郭佳語留了兩箱書在我的寢室,還有一塊牌子,翻過來,是“水色時光”。
我們在微信上聯絡,瞭解彼此的近況,互相鼓勵。景添被甜甜勸回學校再補習一年;師兄他們出了第一張專輯,封面是郭佳語設計的,雖然她大部分的時間在打理她爸爸的公司;陳雋逸給我所在的雜誌社畫很多插畫。
也許我們的水色時光已經結束了,但總會有一個新的時代到來,總會有夢想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