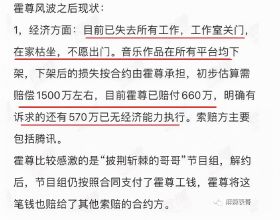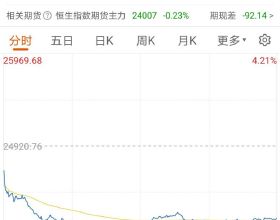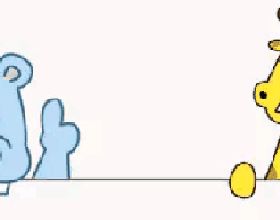爺爺彌留之際,喚我守在他的床前,家裡其他成員一概不得入內。我知道爺爺有話要告訴我了。這一天,爺爺精神特別好,喝了一小湯碗參茶,竟靠著床檔坐起來了。爺爺持續兩年臥床不起,拒絕我們請醫生診斷,僅自己間或開帖方子,由我的母親熬了藥湯,一日三劑維持著,只是不見有好轉的跡象。爺爺突然精神振作,怕是迴光返照了。
爺爺終於說開了:早先,鎮裡,我是外地人,半路出家。未曾受過名師傳授,只是喜歡看些醫書,慢慢揣摩出門道,學得傷科,卻沒有掛牌行醫。我落戶鎮裡,那是後話了。
當時,鎮裡已有個傷科郎中,叫劉妙春,郎中世家。不過到了他這輩,家業已漸漸衰落。可是,他憑祖宗遺傳下來的名氣,四鄉八鎮聞名遐邇,連外縣外省慕名前來求診的人也絡繹不絕。我大他一肖,卻也年輕氣盛,知道能在鎮裡留下來捧住飯碗,必定要有衝突。我只是暗暗瞅著機會。
劉妙春開了個“劉氏傷科”寶號,醫寓的四壁、樑柱,懸掛著“妙手回春”“華佗再世”的金字匾額。我卻借宿鎮上一爿小旅店,私下替人診病,並不大張旗鼓。間或幹些賣柴的營生,勉強維持生計。劉妙春自然沒把我往眼睛裡擱,於是,兩廂相安無事。
劉妙春有個習慣,上午坐家門診,下午去鎮中的一株古銀杏樹下設攤。這一帶,曾是武林高手出沒的地方,大概他拜過武林門派,學得一身拳腳。一面打拳習武,一面賣狗皮膏藥,除了風雨寒雪,他總是在古銀杏樹下出現,數年如一日。那成了鎮裡的一大景觀。
記得那天,久雨初晴。下午,鎮裡的大人小孩都聚集在古銀杏樹下,因為,劉妙春已早幾天放出風聲,要表演氣功絕技。那天,圍觀的人裡三層外三層,觀眾時不時地鼓掌喝彩。
劉妙春用一條五公分厚的鐵板,毫不費力地搭在胳膊上,像卷彈簧似的纏了兩圈。他的情緒高昂,得意揚揚,說:俗話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本人不過玩了一手小技。
我終於憋不住了,撥開人群,入了場地。我五短身材,耷拉著右肩,佯裝痛苦,央求道:劉醫師,我這條胳膊痛得舉不起,求你行個好。
劉妙春伸手一擼,不假思索地說:脫臼了,小菜一碟,三指上骱,五指接骨,你立穩嘍。他三指用力一按,說聲:妥了。
我的手果然能伸屈了,可是,沒退兩步,右肩又耷拉下來。我瞥他一眼,說:劉醫師,怎麼又不對勁了。
他詫異地瞧我一眼,又三指下力一按,說:妥了。
我甩甩胳膊,右肩卻又垂耷下來。
大概劉妙春察覺我故意出難題,他擺出架勢,滿額沁出汗珠。這下,按了兩回,都沒接妥。
我頓時笑了,丟出一句:想不到這根小小的胳膊,就把個名醫難住了。說著,我猛地身體一矬,雙肩向上一聳,“咯嗒”一響,右肩立刻伸屈自如了。我揮舞胳膊像風車一般旋轉了一陣。
劉妙春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圍觀的人群一片啞然。我見劉妙春傻了眼,一甩袖口,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兄弟,俗話說,滿飯好吃,滿話難講。
我退出圈外,人們自然而然讓出一條道兒。我回頭說:兄弟,身子有了不適宜,七天之內來鎮東的小旅店找我就是了,過時我可就不在了,切記切記。
我有意講給眾人聽。那以後的日子,劉妙春沒再露面。我整日不接診,不砍柴,單候他的出現。我已聞知他的妻子出來買藥。我知道,他那傷,非我的方子不可。我想人命關天,他該放下架子來求我了吧。
第七天,我終於失去了耐心。包了事前配妥了的十二帖藥,來到“劉氏傷科”的屋宅。
劉妙春已臥病在床。我擺了藥,說:一日三帖。
劉妙春強打精神,坐起,怒衝衝地說:大丈夫寧死也不服你的藥方,否則,我對不起列祖列宗,劉氏傷科的招牌也砸在我的手上了。
他妻子一再勸慰也不抵事。據說,劉妙春臨死竟拒服藥劑——他唯恐妻子煎了我送去的藥劑。
當晚,劉妙春突然連連嘔血,大叫一聲:愧對祖宗!
他的死,一直像塊巨石一樣壓著我。我不過想殺殺他的威名,卻不料他抱著那塊寶號固守而死。那之後,我棄醫從商,開了爿藥鋪,只是不接門診。你大概猜出來了,你奶奶就是劉妙春的妻子。我那一掌,拍破了一個家庭,我甘願照應他們。你奶奶早十二年離開了我,我對不起他們一家。(作者 謝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