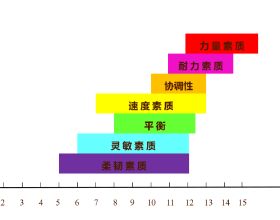(一)
離千禧年還些日子的時候,謝老爺子帶著全家從海外回到了祖宅,推開厚重的大門的那一剎,芍藥搖曳生姿,往事繽紛踏至,謝老爺子站在門外感覺恍如隔世。
謝家這一輩最得寵的是一對龍鳳胎,謝三老爺的孫孩,才不過五歲,儼然有了小大人的風範。
謝家在解放前是名門望族,祭拜的規矩多之又多,小小孩子自然不耐煩,看著掛在牆上的那幅像,忍不住嘀咕:“這是誰?我憑什麼拜她?”
沒防備地,謝老爺子一柺杖抽到他腿上,帶著怒氣說:“你今天就在這裡跪三個小時,反省反省自己。”
祠堂裡的大大小小晚輩都不敢說話,謝老爺子已許久不發這樣大的脾氣。
謝如是知道自己二伯的脾氣的,可是看著跪在地上的兒子,這三個小時哪裡說跪就能跪的?他只好把求救的眼光投向父親。
奈何謝三老爺也是一反常態說:“晚輩不懂事,該跪該罰。”
他急得團團轉,把女兒叫過來:“你等會去給大爺爺泡杯茶,替弟弟道個歉。”
那個小女孩把茶送進書房後柔聲替弟弟道歉後,謝老爺子嗯了一聲便不再吭聲。
老爺子的書法尤其好,千金難求,小女孩單看那厚厚一沓,便知這是成千上億的數量。
半晌,謝老爺子坐在椅子上嘆氣,她探出頭看到白紙上寫著: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居易的《長恨歌》,她啟蒙得早,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看來今日弟弟確實犯了大錯。
“大爺爺。”她輕輕喚了一聲。
謝老爺子沒有理她,喃喃地念著:“何歡,何歡……”
何歡?
她沒有多大記憶,只是覺得這個名字不精緻。
“倘若有致遠和有晴,應該要比你大些。”
大爺爺一生孤寡,致遠和有晴這兩個名字對於她來說太過陌生。
只是那語氣太苦澀,苦澀到她真的希望這兩個人存在。
(二)
1923年的某一天,本該是個尋常日子。聽說謝家二少爺謝懷宇從日本來了信,一封寄往謝家,一封寄往何家寄予何歡。
可他忘了,何家小姐何歡一直信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條例,她是不識字的。
於是這封信便直接落到何歡父親的手中。
誰知父親看完之後,眉毛都要豎起來了,“好個謝懷宇,居然要退親。”
何歡正在喝茶,愣了一下神,杯蓋噠的一下落到杯口上,半晌,不鹹不淡地說:“謝家怕是也不讓。”
父親這才反應過來,謝家和何家的生意往來已經不是一朝一夕了,他們兩家哪裡是幾句話就能說清道明然後退親呢?
“只是,”父親欲言又止,“那孩子如今這樣的心思,你以後嫁過去可怎的好?”
何歡也想,是啊,以後要怎的好?可怎樣也是以後的事了。
打那以後,謝懷宇每封家書都要提起此事,每次都要囑咐父母儘早退親。
不知道謝家是如何處理此事,但對於何家而言,只要這謝家一日沒上門來說及此事,何歡依舊是謝家沒過門的媳婦兒。
年歲大了些,身邊的姑娘都成了親,生了孩子,何歡多少也是要被拿來比較的,母親成日唸叨:“這像什麼話,難不成他永遠待在日本不回來了?”
何歡好性情,一邊繡著花一邊回頭安慰母親:“別擔心,他總歸是要回來的。”
當媽的看見自己的女兒自然是又心疼又心憐,聽了這話疑惑地問:“你怎麼知道?”
是啊,她怎麼知道?
就走了這麼一下神,針就扎進了肉裡,她疼得一下子放開手。
母親問她怎麼了。
她笑著說:“沒事。”
沒事肯定沒事,可她盯著這白色的布匹上的一滴血,終歸是毀了,可惜了她這麼長時間花的功夫。
管家從外面進來,說:“夫人,小姐,謝家二少爺回來了。”
何歡沒什麼大的反應,只是想著,終於回來了。
何歡見著了自己這個名義上的未婚夫,他穿著筆挺的西裝站在廳堂裡,擲地有聲地說:“我要退婚。”
“混賬東西!”謝父拿著柺杖狠狠地抽在謝懷宇的身上,那一下著實不輕,謝懷宇悶哼了一聲。
緊接著不過就是,什麼忤逆雙親、不孝不義的戲碼。
父親給她使眼色,讓她上去拉一下,替謝懷宇求個情。
何歡把茶杯拿起來,急什麼?平白無故地讓我等了這些年,這一頓打,幾刻時光他還捱不過去了?
她慢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又仔細想了晚上吃什麼,才站起來說:“謝伯伯,別打了。他剛剛回來,打壞了您不心疼我還心疼呢。”
謝父順著臺階下來了道:“謝懷宇,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別的不說,就衝這一句話,我謝家就只有她這個兒媳婦。”
謝懷宇還在地上跪著,何歡走過去扶住他的胳膊說:“趕緊起來吧,別把膝蓋跪壞了。”
他沒有說話,回頭狠狠地瞪著何歡,一雙眼睛裡都是怒氣。
何歡卻笑開了,連帶著整個眉目都生動起來,“我好心救你,你卻如此不領情,你我從未深知過,為何要這麼恨我?”
謝懷宇垂眼,她說得沒有錯,只是以後要和一個字都不認識的女人生活,他該如何是好?
(三)
謝家與何家的婚事定下來了,八月底,金秋時光。
母親時時感嘆:“所幸謝家父母還是喜歡你,否則你這婚事怎麼能成?”
何歡知道母親說的是什麼意思,這場婚事是謝母以死相逼才促成的。
婚禮的前一天,何歡在家喝茶,突然跑進來一名女子,怒氣衝衝地質問她:“你就是何歡?就是你要同謝懷宇結婚?”
何歡細細地打量她,早就聽聞謝懷宇有一個鐘情的女子,北平人,和謝懷宇很是志同道合,應該就是眼前這位了。
沒想到謝懷宇喜歡的竟是這樣的生動朝氣。
“是。”
她又問:“你知不知道他不愛你?”
何歡點頭,“知道。”
“既然知道,那你怎麼能同他結婚?你連字都不認識,他說詩詞你能明白嗎?他說政治你能懂嗎?”
何歡站起來重新打量她,而後笑了,“我是不懂,但是我問你,你會管理生意嗎?謝懷宇學醫,你懂醫術嗎?你會下廚嗎?繡花呢,會不會?這個世界沒有誰比不上誰,日子是過出來的。”
遠遠地看見謝懷宇過來,何歡馬上背過身,婚禮前不見面這是規矩。
謝懷宇可以不避諱,只是這何歡一生的婚姻,她不能不避諱。
“灼灼,跟我走。”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何歡雖然不認識字,卻也聽過這首詩。
他們都說,這是一首賀新娘的詩。
何歡是難過的,誰願意自己先生心裡有其他女人呢?可她早就知曉的,謝懷宇並不喜歡她。
次日大婚,是中式婚禮,她以為像謝懷宇這樣留過洋的人都喜歡西式婚禮。
謝懷宇後來告訴她:“有些東西是丟不得的。”想想又搖了搖頭,“我和你說這些做什麼,你又不懂。”
她蒙著蓋頭,母親告訴過她規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
何歡緊緊揪住衣服,成婚是人生大事,斷不能走錯一步。
蓋頭挑開的那瞬間,那個男子面無表情地看著她,最後嘆了口氣說:“我會忠於自己的婚姻,像昨天那樣的事不會再發生了。”
何歡點點頭,臉突然紅起來。
這是他們的新婚之夜。
何歡醒的時候是半夜,她翻了個身,看到和自己的手距離不過兩公分的來自另一個人的手。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讓他握住。
可她又明白,謝懷宇握住的是那個叫灼灼的人,而不是自己。
他忠於自己的婚姻,不是源於愛,也不是源於她,是他源於對自己的責任。
這些她都明白,可心底的希望如同春天的荒草一樣瘋長,填滿她整個心。
“這麼晚不睡做什麼?”
靜悄悄的房間裡只聽到這句話,嚇著何歡立馬抬頭對上那雙黑漆漆的眸子,有瞬間的失神,“沒什麼。”
“早些睡吧。”
何歡閉住眼說“嗯”,她知道未來還很長,她祈盼著萬事皆有可能。
(四)
何歡同謝懷宇成婚一個月後,謝懷宇決定去上海。
這個小小的地方裝不下他的夢。
可父母如何肯?謝家大少爺不學無術,三少爺天性不羈,只有這二少爺才能挑起這整個家族的重任啊。
他剛剛去同父母商量這件事,便又被說一頓,回來的時候正好瞧見何歡正在拔院子裡的草,他心煩意亂,“你拔了有什麼用?來年它還是要長的。”
何歡應聲:“可我見家裡這些枯草總是太亂了。”
家裡?
謝懷宇心裡一動,不論如何,這個叫何歡的女人是他的另一個家。
於是他問她:“我帶你去上海可好?那裡……”他想形容形容上海是什麼樣子,那裡有哪些何歡喜歡的東西,想了半天,他卻不知道何歡喜歡什麼。
這是他作為丈夫的失職。
何歡滿懷期待地等著,半天也沒有聽見謝懷宇說話,便放棄腳旁的草說:“我覺得很好,需要帶些什麼東西?我去收拾收拾。”
她雙手抵住膝蓋,準備站起來,輕輕呀了一聲。
“怎麼了?”
何歡臉紅,有些不好意思地說:“腿麻了。”
謝懷宇沒有說話,走到她身旁,牽住手,陪她一步一步走,“多走幾步就好了,去上海的事還沒譜呢,爸媽怎麼著也不同意。”
何歡只能拼命點頭,臉越發地紅,低頭看著謝懷宇的手,是那樣的不真實。
日子好像從此變得香甜,有股芍藥的味道。
次日一早,謝懷宇是在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音中醒的,睡眼惺忪地坐起來看著左右忙活的何歡問:“你在幹什麼?”
“昨天晚上爸媽已經同意我們去上海了,我回來看見你睡了,就沒有告訴你。想著提前把東西收拾好,免得到時候手忙腳亂。”
謝懷宇像做夢似的,忘記了欣喜若狂,有些呆滯,“他們真的同意了?”
何歡還在收拾東西,道:“真的。”
他們到上海的那一日是1月1日,新的一年新的一月新的一日。
謝懷吟來接他們,何歡知道這是謝家三少爺,謝懷宇的弟弟,結婚的時候她蒙著蓋頭,沒有見過此人。
“二哥,嫂子。”謝懷吟衝他們招手,好看的酒窩在臉上綻放。到了跟前,便直接拿過何歡手上的行李,笑道:“二哥這是怎麼了,還要嫂子拿行李,一點都不懂憐香惜玉。”
何歡自然是紅了臉,這裡天氣冷,又聽了這番話。
謝懷宇取下圍巾給她戴上,一圈一圈地圍完以後,在尾端輕輕地繫了一個結,“這是我弟弟,貧嘴慣了,你不要介意。”
她哪裡介意?這是謝懷宇的家人啊。
謝懷吟去給他們接風,他是上海的浪子,眉宇間都是風流倜儻。
“二哥,我給你租了房子,格局不錯,上面住人,下面開藥房,倒符合你的要求。”謝懷吟說得眉飛色舞,像是哄著何歡開心一般,“最妙的是,它有一間書房,直接對著後面的院子,嫂子,這個書房你留給著自己……”
謝懷宇打斷他:“你嫂子不識字。”
這是何歡第一次聽見謝懷宇說這句話,陳述事實一般說出來,有沒有嫌棄?何歡不知道,只是覺得自己丟了他的臉,他是那樣優秀的人,自己的妻子居然不認識字。她從未有過這樣的感覺,當初灼灼上門質問的時候,她也自信沒有誰比不上誰,可如今卻生生覺得對不起謝懷宇。
謝懷吟愣了幾秒,笑了,“那有什麼?你教便是。”又衝何歡說:“倘若我二哥忙,你也可以來找我。”
這些話便到此為止,夜裡回家,她睜著眼躺在床上,看著謝懷宇的側臉,心裡總歸是不好過的。
(五)
何歡以為謝懷吟來教她識字是句客套話,可沒有想到他真的買了筆墨紙硯上門來了,邊走還邊讚歎自己的眼光是如此的好,選中了這樣好的一個房子。
何歡輕輕地笑開了。
謝懷吟挑眉,“你笑什麼?我的眼光向來是很好的。”
謝懷吟問她想學什麼。何歡想:是啊,我想學什麼?
“不如先學著寫你二哥的名字吧。”
謝懷吟筆還沒有停就招呼她過來看,何歡看著紙上的字,一筆一劃,那麼神奇似的就代表著謝懷宇。
“這是你的名字。”
謝懷宇,何歡。
她把兩張紙放在一起,她是認不得這五個字的,只是想,一定要記下來,記在心裡。
謝懷吟有些驚訝,“你哭做什麼?”
何歡聽了這句話,才發現眼角已經溼潤了,不好意思地說:“見笑了。”
謝懷吟擺手。“你是我見過最特別的……”最特別的什麼?他想了半天沒有想到詞,就說,“我哥有沒有說過,你笑起來有種如沐春風的感覺,連帶著表情都富有生命似的。”
她搖搖頭。
謝懷吟笑,“我的眼光是真的很好。”他的酒窩還沒有完全顯出來就收了回去。
何歡卻只想著,這毛筆要怎麼才能拿好?
謝懷吟也看到了,本想著握著她的手,可男女有別,便拿著一支筆做示範。
大概是三個月後吧,謝懷宇在藥房裡診病,那日人少得緊,何歡便拿著毛筆練字,謝懷宇倒了杯水回來,便看見了這樣的場景——
何歡側著身子,右手拿著毛筆,一字一字在紙上寫他的名字,謝懷宇,謝懷宇……
他心裡一動,有些酸澀,她不識字,第一個學的竟是謝懷宇三個字,不知道怎麼想的,輕輕咳嗽了一聲,嚇著何歡一抖,那滴墨點便留了下來,像極了當初白綢緞上的紅點。
何歡回頭看見是謝懷宇,臉一下就紅了。她本是想著把這張紙藏起來,奈何謝懷宇手快,立馬就抽走了。
“是誰教你寫的字?”
“三弟。”
謝懷宇搖搖頭,“他的字向來寫得不好,如今可好,你練敗筆都和他一模一樣。”
何歡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謝懷宇已經替她做了決定:“從今日起就不要和他學了,以後我來教你就是。”
就算為了這滿紙的謝懷宇,他也不能負了她。
何歡不知道他們兄弟兩個在裡面說些什麼,她送茶進去的時候,謝懷宇說:“凡事都有先來後到。”
謝懷吟點頭,“二哥說的有道理。”
“何歡。”
準備出去的何歡愣在原地,一臉茫然地看著叫她的謝懷吟,“你再笑一個。”
這算是什麼要求?這哪是說笑就能笑的?
沒等她笑出來,謝懷吟先笑了,“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何歡才剛剛識得字,詩現在是萬萬讀不懂的,反倒是謝懷宇一下子黑了臉道:“天色已晚,你儘早回去吧。”
那天,謝懷宇大概是生了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氣。
何歡什麼也不懂問:“你怎麼了?”
謝懷宇怒極反笑,“我怎麼了?我盼著你能懂點禮義廉恥。”
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謝懷宇說的是什麼意思,天地作證,她對謝懷吟是沒有那個心思的。她是委屈的,自己一心一意愛的人怎麼這樣想?這份愛如此不值錢,所以能夠朝三暮四?
何歡放下準備給謝懷宇熨的衣服說:“還記得你新婚當夜對我說過什麼嗎?”
謝懷宇也愣了,回頭之後發現何歡已經出去了,從衣服裡掉出來他多年前和灼灼的合影。
灼灼如今在北平抗日,這是他們曾經共同的夢想。
這是他也心上的傷,如今卻又被翻了出來。
他說過像那樣的事不會再出現,自己卻在唸念不忘。
(六)
上次的事過後,謝懷宇當真是每日教她讀書認字,從《三字經》到《詩經》《史記》,何歡學得很快。
五月十七那一天的中午,謝懷宇拿著書問她最喜歡哪一句詩。
何歡還沒有作聲,衝一旁嘔酸水。
謝懷宇怕她吃壞了東西,伸手給她探脈。
何歡趁著這個光景,把剛才的那個問題給回答了:“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謝懷宇呆了幾秒,半天說不出來話,而後盯著她的眼睛說:“何歡,你懷孕了。”
正在等藥的病人聽見了笑,“謝大夫,自己媳婦有喜了,你還以為她吃壞了,不夠關心啊。”
是啊,我總是不夠關心她。
而坐在另一頭的何歡摸摸自己的肚子,問:“幾個月了?”
“兩個半月。”
何歡輕輕地笑了,她的開心用不著任何詞能形容。
像一般初為人母一樣總是問:“謝懷宇,你喜歡男孩還是女孩?”
“都好。”
何歡躺在搖椅上,拿著針線繡衣服說:“十月懷胎,現在才五月,孩子出生的時候大概是一月,天氣還冷,我先給他做幾件衣服備上。”
“不如你先給孩子取個名字吧。”
謝懷宇想著孩子還沒有出生,現在取名是不是太早了,抬頭看著何歡期待的眼神,又不忍拒絕道:“男孩就叫致遠,取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女孩叫有晴,‘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何歡懷孕之後,謝懷宇便忙了起來,除了病人之外,他似乎有更重要的事,整日整日的在外面。
那日下了很大的雨,何歡在樓上看見謝懷宇要出門提醒道:“你帶把傘。”
說完,她便從樓梯裡拿了一把傘送下去。
剛踏出第一步,便踩空了。
後來就是血,還有疼。
醒來的時候是在醫院,何歡看著還沒有來得及換下那件帶血衣服的謝懷宇問:“我的孩子呢?”
謝懷宇告訴過各種各樣的病人,你的身體出了什麼問題,有沒有病入膏肓,他站在醫者的角度,冷靜地分析別人的生死,卻不知道怎麼告訴何歡孩子保不住了。
何歡眼淚止不住地流,“謝懷宇,你說話啊,你怎麼不說話?”
他緊緊地握住何歡的手說:“孩子,不在了。”
何歡抽出手,冷冷地看著他,說:“謝懷宇,你騙人,你怎麼能拿我的孩子來騙我?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
謝懷宇抱住何歡,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失子之痛,他也難過。
(七)
何歡那段時間很消沉,謝懷宇便天天陪在她身旁。
好轉起來已經是冬天了,她穿著很厚的棉襖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大雪說:“家裡是不是從來沒有這樣大的雪?”
冬末春初的時候,何歡在謝懷宇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封信。
上面無非寫著北平的天不熱,她將在六月初三到達上海,希望彼此能不失約,記著當初說的話,末尾添了一句“我很想你”。落款,灼灼。
六月初三,她流產的那日。
何歡把信疊好,放進那件衣服的口袋裡。
這麼些年過去了,她只是他的妻子,能和他風花雪月,煮酒談詩的人,始終不是她。
只是她的孩子何其無辜?
上一秒還在討論孩子的名字是什麼,下一秒就要出去會見那個人,而後又告訴她,孩子不在了。
你怎麼能這樣,謝懷宇!
她質問謝懷宇時,依舊用的這番話。
“何歡,我不會違背自己的話,我和她已經過去了,我說過我會忠於自己的婚姻,而且那天,我也沒有準備去見她。”
她大笑,“我不曾懷疑過你的為人,也知道你千好萬好,可是謝懷宇,感情的事我怎麼才能信得過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你要我怎麼相信你?”
謝懷宇瞭然,原來她的心結在這裡,“何歡,我們已經結婚了。”
所以是讓我知道我得到的已經夠多了嗎?
何歡苦笑,“是啊,我們結婚了。”
這件事就這樣不清不楚地過去,你問何歡信謝懷宇嗎?她信,只是她心裡這個坎怎麼邁也邁不過去。
(八)
上海的好日子並不多,淪陷之後,只能在租界裡討生活。
日本人找上門來時,謝懷宇出去進貨,藥房裡只有何歡一個人。
“謝太太,你好。”
她是膽大的,坐在那個日本軍官對面問:“你們想幹什麼?”
“我想請謝先生替我的上司看病。”
何歡冷笑,準備出言拒絕,謝懷宇就從外面回來了,面對一屋子拿著槍的日本人,他竟然出了奇地冷靜,看著何歡問:“你還好嗎?有沒有事?”
“沒事,我很好。”
聽過這句話,他才偏頭說:“不知各位有何貴幹?”
知道來意之後,便笑了,“你讓我考慮考慮。”
日本軍官站起來,拿槍指著何歡的腦袋說:“好,我們陪謝先生一起考慮。”
謝懷宇愣了,馬上站起來說:“你想幹什麼?”
“我們只想請先生去看病而已。”
他想都沒想說:“好。”又對何歡輕輕笑開了,想讓她放心般說:“做好飯等我回來。”
一群人轟轟蕩蕩地來了,又轟轟蕩蕩地走了,一起帶走的還有她的先生。
何歡一個人坐在藥房裡,等到天黑了,她慢慢地站起來,告訴自己:謝懷宇一定會回來,我要做好飯等他回來,謝懷宇一定會回來。
他確實回來了。
他悄悄地走到廚房裡看著何歡做飯,看著她拿著勺子輕輕地攪動著粥,然後又切薑末,拍蒜,熱油,下菜。
他還沒有回國前,就聽說何家小姐,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做得一手好菜。
奈何那時候別人說她怎麼好,謝懷宇都覺得她不好。
結婚這麼多年,她做菜確實是好吃的,他只要在外面吃一頓飯,就會格外想念何歡的手藝。
“你回來了。”何歡看見他差點喜極而泣,跑過來,像是要抱住他似的,張開手發現這樣不好,臉紅了。
謝懷宇走過去,輕輕地摟住她,在她耳邊說:“嗯,我回來了。”
飯菜上桌,糯糯的白粥配上小菜是他們的晚飯。
“何歡。”他叫她。
“嗯?”
“我們過些時日回家吧。”
何歡夾了一塊豆腐給他說:“好,走之前我在松樹下埋了兩壺我釀的酒,回去我們共同嚐嚐。”
“你還會釀酒?”
“是啊,我會的可多了。”
謝懷宇突然發現這多年,他還是不瞭解何歡。
他喝了口粥說:“我們還有小院子,不如種點東西。”
“好,”何歡應聲,“我喜歡芍藥,到時候多種點。”
“我們再生兩個孩子,就叫致遠和有晴。”
何歡紅著臉說:“好。”
謝懷宇靠著椅背,想想這樣的生活真覺得美好,什麼家國大義,什麼國家興亡,和他有什麼關係?
他只想和自己的小妻子花前月下看芍藥,考考致遠和有晴的功課。
可亂世,哪點由得自己?
灼灼說:“我們必須殺了那個日本人,否則我們在前線的戰士怎麼辦?他手裡掌握的是生化病毒啊。”
他由不得自己,時代替他做了決定。
何歡問他準備怎麼辦,他不說話眉毛輕輕擰成一個結。
何歡想起父親當初看上謝懷宇是說他有家國氣概。
(九)
謝懷宇跪在地上,那個日本人已經死了,他知道自己離死亡也不遠了,心裡卻難得的安寧,只是想何歡知道自己死了會有什麼反應。難過還是解脫?
他看到何歡的那一刻以為自己做夢了,像是知道了什麼,大喊:“你來做什麼?快回去!”
何歡看都沒有看他,直視他面前的日本軍官,“人是我殺的。”
“你胡說什麼?”
“人是我殺的。”何歡說,“昨天晚上我偷看了藥方,在已經抓好的藥加了砒霜。”
日本軍官皺眉,“人人都知道謝夫人不識字。”
何歡笑了,這麼些年,她終於可以反駁這句話了。
“誰說我不識字?再說,不識字難道就不能加砒霜嗎?”
“原因呢?”
“原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日本人踏的每一寸都有我們國人的血跡,憑什麼還指望我們來救你?”
何歡被拉出去,緊接著就是一聲槍響。
“何歡!”謝懷宇大叫跑過去抱著她,她全身都是血,他行醫多年,從來沒有看見這樣多的血。
她眼神開始渙散,捉住他的手,問:“家裡有沒有這樣大的雪?”
他抵著她的頭,“有,我們回去看,好不好?”
何歡死了。
他回家之後,桌上擺著一碗粥,一如從前精緻。
旁邊放在一封信。
先生:
我從來沒有這樣叫過你,怕你不喜歡,同床共枕這麼多年,我知道你的決定。
最近我總是想起灼灼說的一句話,她問我:“你知不知道謝懷宇不愛你?”我說知道。在你還沒有回國之前,人人都告訴我:“你是謝家的媳婦,你是謝懷宇的未婚妻。”我也是這般想的,所以拼盡法子地嫁給你。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糾纏了那麼久,才發現我耽誤了你這麼多年。倘若今天是灼灼,也許又是另一番境地。
只是今日是我,我有我的決定。
從今以後,你好好過。
只願你的下半生得償所願。
落款,何歡。
謝懷宇拿著信哭出來,你怎麼能不知道我愛你?你怎能見到她時,就感覺她笑得真美。
他也沒有告訴她,他不喜歡謝懷吟對她那麼好,因為謝懷吟喜歡她。
甚至沒有告訴她,他和灼灼如今只是革命戰友。
那她又如何得知他愛她呢?她這個傻瓜,什麼都不知道。
何歡,世世代代你是我的妻。
他一生到此,隨著何歡的離開,已分崩離析。
(十)
謝老爺子在千禧年死去了,活得久了對死亡沒什麼懼怕。他躺在床立遺囑時,一眾侄兒女泣不成聲。
他偏頭看著謝懷吟笑了,“我終於可以去見她了。”
“凡事都有先來後到,你始終比我幸運。”
按照遺囑,把謝老爺子埋在何歡的旁邊,把埋在松樹下的兩壺酒取出來倒在墓碑。
從前,我們說要共同品酒。
如今,芍藥正好,酒香濃烈,不算食言。
文/東辰東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