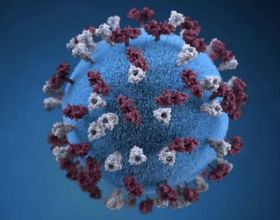( 上 )
徽山妻子昨天晚上沒有來由地対徽山說了決絕的話,而且說話的神情異常地平靜,她的聽者自然也波瀾不驚。又是把借錢遭到羞辱的事要在徽山這裡找回去,繼續羞辱徽山,她辦不到。舊話引起的話是什麼呢?
她說:“她和徽山不管誰死在先,都要和徽山針鋒相對地幹下去,即使她先死也在所不惜。”類似的話她說得太多了,只是沒有這樣決絕,說了十幾年了,這次是升級版,達到了新高度。一點點不同的是,這次她說了她就是先於徽山死也無所謂了——死幹到底。尤其還特別強調了死前定要跟徽山離婚的斷語。死都死了,離不離就那麼回事!徽山不屑地這樣想。
徽山乜了一眼妻子,話都懶得說,大不了,一個半死人而已,繼續看他的紀錄頻道。他對她諸如這樣的東西已經免疫了,全方位免疫的那種。他只是靜靜地等著她的行動。
灰色的天空
之前,她和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而沒有說出的論斷:沒有意外的話“徽山會先於她去見馬克思的”。
生活的美好,吃喝玩樂也好,職場揮灑青春也好,人生的酸甜苦辣鹹也好,徽山深深地切身感受過了,他很享受這一切。
當孤寂都成了自己習以為常的愛好和享受的時候,它當然也是他閱讀的美好時光和必要的氛圍,也合了他的所好。他也很享受。
收穫的秋季
在這個世界上,徽山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只是有些遺憾和對耄耋父母的虧欠,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過勞失能,自顧不暇。過勞致死、過勞失能,它已經是身邊一種見怪不怪的現象身邊有,媒體上也有,例子舉不勝舉。畢竟和他身體狀況一樣積勞成疾的人、包括他的朋友,他是個幸運兒,他活著。他也是最厲害的之一,比跟他情況相似的醫生朋友的叔叔還多活了十餘年,夠本了,知足了。
體驗一下不可預知的新生事物不是也很好嗎?很多人還沒有這種體驗呢。人的歸宿都是一樣的,早晚都是墓碑一個,放馬過來吧!
親戚朋友間借錢,在徽山他們家族裡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只要誰提出這樣的事,特別是他們姊妹間,大家只需要問清楚,需要的人什麼時候要,就能力按時準備去了,不問出處,不問原由,借錢的人對被借的人也不會開口說第二次,沒有阿來白來的事。
與之對應的另類借錢,他沒有經歷過。
大約四五年前吧。妻侄大學畢業,有個別人羨慕的工作,收入比處級幹部還高,進了別人想進都困難的單位,工作一年餘後,對朝九晚五的模式很感到索然無味,毅然辭職。在“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潮流下,在自己喜歡的行業領域創業,幾年下來乾得很不錯,風生水起,便想起擴大再生產的事情來了。
在他們賣掉他們大房子的幾個月後提出借錢。借錢不是向他們一家借,還有一個身價億萬的地產大老闆。
賣了房子後,徽山妻子曾就告訴過徽山,不要給姥爺姥姥講。他說你說了算,他不明就裡,但心裡覺得怪怪的,說或者不說與他們,又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可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
轉過去,她把買房的事說給她家,然後就有了各種扯不清的腌臢事,借錢的事。她纏不過他們,來和他糾纏,扯不清的腌臢事和他無一毛錢的關係。她直轄市的企業家舅舅也跟著湊熱鬧借錢,舅家的事在這裡就不提了,她父母沒有說話表態,最後沒有借。
侄子借錢的事,在徽山看來,既然內侄開口了,妻子儘可全力以赴去做,即使徽山反對。為什麼需要那麼多的人開口說話?有這個必要嗎?!開口的人、保證的人多了,徽山心裡反到泛起疑惑的嘀咕。
開口的全部人都是說給徽山妻子的,她完全可以不告訴他,她一慣是這麼做的。這次很意外她告訴了他,這是為什麼呢?她家的事他沒有想知道,他更願意理解為:這事與她無關,她不是這個家的人,她是孃家的人。
依照徽山妻子話語搬運工的特點,徽山知道了借錢的婆煩事,先是新當了父親的侄兒提出的,接著是她哥嫂子開口的,再接著是姥爺(有錢人)開口說的,最後是姥姥開口的。沒有錢的權威姥姥開口時,那個答應幫助的大老闆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錢,據說還沒有到位。
姥姥開口說情,這在徽山妻子看來是天大的事情,當時怎樣的場景他想象不到。姥姥都開口了,高度有了,如果不借,心臟不好的姥姥出了問題,要為徽山是問。她的話就是這個意思。這可不是一般的事了,也不是小事兒了,生死攸關。
沒有錢的姥姥打包票的舉動,可笑地成了她對他的最後通碟,他被裹挾其中。姥姥出了事,他就完蛋了。這樣的壓力,她也算到他的頭上了,他不屑一顧,不置可否。她的這話,他的耳朵沒有進去一點。
一個多月過去,他隱隱地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他們都也知道,但是他們誰也不挑明。他不挑明是不想給她折騰他的理由,她不說是想找他的後帳和可能事情的解釋。
他強調了那句一言以貫之的話:“你家的事你說了算”,說得斬荊截鐵,“錢在你手裡,你說了算”。他知道不管怎麼樣她都會為此鬧上幾回的,他在這方面是保護自己免受或少受叨擾的老天爺,是她讓他成了自己這方面的先知,他只想靜。
賣房的錢她那裡有一大半,借與不借,按照她的做事習慣,她跟本就不會和徽山說,她的所有事都是這樣乾的,最多是告知一下徽山,事後出了問題的例外。這次說了,美其名曰這事他得知道,但是姥爺姥姥的保證讓他費解。有那個必要嗎?!恰恰是他們的保證,是她的不安所在,畢竟她還有孩子,自己一輩子也存不了那些錢,也是她後話可能的說詞和叮噹打鐵的需要。
徽山很有自知之明,也知道自己說了和不說都一樣的,即使有不同意見,妻子該咋做還是咋做,他的所有言行都可能成為她事後算後帳的一個幌子。他躲都來不及呢,又何必介入其中呢。這些事他跟本就不想勞神,也勞不起這樣的神。所以,從第一次聽到她說她侄子借錢的事之後,他始終就一個態度:“你們家的事,錢在你手上,一切你自己做主就好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