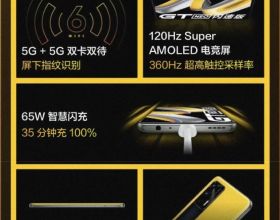導讀:人類很早以前就開始思考:在浩瀚的宇宙中,其他天體上會不會有生命,是不是有文明?這些問題既是無數科幻作品的基石,也吸引了歷史上許多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們。 不過,這些科學家是不是“不務正業”?科學與科幻的邊界在哪裡?科幻是否能推動科學的發展?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穆蘊秋,與該院首任院長、交大講席教授江曉原此前梳理了關於地外文明的主要“科學幻想”和科學探索,相關成果於近日出版。觀察者網科普作者岑少宇就這本新書《地外文明探索——從科學走向幻想》與兩位學者聊了聊。
【採訪/觀察者網 岑少宇】
觀察者網:這本書是以穆老師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的。應該說,2004年研究開始時,人類對地外文明探索的熱情,與巔峰時期相比已經大幅消退。當時為何選擇這一切入點?
有沒有覺得,既然探索地外文明已經不那麼熱了,是時候做個“階段性總結”了;還是說,更多地由兩位對科幻的興趣推動。
江曉原:我那時候想把對科幻的科學研究學術化,學術化的指標之一,當然是發學術文字了,當時我已經發了若干篇文章。那學術化的下一個指標,是要弄一個博士學位出來,所以要找一個人做這個課題的博士論文。
穆蘊秋那時候是我的在讀博士,她看過好多科幻電影,看電影比我還資深,所以建議她來做這個課題。她考慮了一陣之後,就決定做這個題目。
但要真的做科幻的題目,還得考慮學術性,而不是考慮冷的熱的,有些熱的東西,它是很難學術化的。
相對來說,地外文明探索它是一個能學術化的,即使在今天的天文學前沿中,地外文明探索仍然是有一席之地的,選它來做,學術化會有保障。
穆蘊秋:我來稍微補充一下,因為科學史這門學科下面其實分很多方向,而歷來最強的就是天文學史這個方向。
其實我當時做科幻,一開始進到這麼一個大方向裡以後,不知道做什麼,很長一段時間也是很迷茫的,因為有那麼多科幻。最後找來找去發現,地外文明探索這個東西和天文學史這一塊的介面是最緊密的。
論文做出來以後,還面臨一個審稿的問題,要有學科的“合法性”,如果和科學史本身的專業聯絡不是很緊密,那要出問題的。而地外文明探索,一下子就可以和天文學史結合起來。
觀察者網:距離我們最近的月球,肯定是人類最先集中想象地外文明的地方。伽利略和開普勒都曾“放飛自我”,想象月球的場景,探討是否存在生命。伽利略選擇“對話”的形式(《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以下簡稱《對話》),開普勒選擇“夢”的形式(《月亮之夢》)來展開,是不是意味著在他們的年代科學與科幻其實已經有了某種區隔?
江曉原:不能這麼說,那個時代根本就沒科幻。科幻這種概念或者說產物,在伽利略和開普勒的時代是不存在的。只不過在今天已經有了科幻概念之後,我們會覺得開普勒的《月亮之夢》那個作品是科幻。西方有些人還把科幻追溯到更早的時候,比如古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
《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圖片來源:wiki
觀察者網:但他們是不是有意選擇了一個“非正式”的文字呢?即使當時沒有科幻的概念,但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存在著形式、內容等等差別巨大的兩類作品,一類不那麼正式的,接近於我們現在理解的科幻,另一類文字更為正式的,接近於現在理解的科學?
穆蘊秋:伽利略的腦子裡面沒有任何“科幻”的概念,這是確切無疑的。他為什麼會在《對話》裡討論月亮上適不適宜居住這個問題?對他來說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因為他是第一個拿望遠鏡指向天空看月亮的人,然後他就會思考這樣的問題。在伽利略這裡,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個科學問題。
開普勒寫《月亮之夢》其實也是一樣的,但開普勒風格跟伽利略不一樣,它有一些神秘主義的道道在裡面。後來人們再回頭去看《月亮之夢》,有些學者把它作為科幻開山之作的備選。我們通常認為第一部科幻小說是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而在西方,很多人認為《月亮之夢》才是正宗的第一部科幻小說。但是討論月亮上的生物之類,對開普勒來說也是很嚴肅的,並沒有說把它看成一種“科幻”。
1634年版與2017年再版的《月亮之夢》,Somnium是拉丁語的“夢”,圖片來源:wiki和亞馬遜
江曉原:那個時候,人們心目中科幻和科學探索之間是沒有界限的,他們是非常認真地在討論月亮上的人、火星上的人,甚至太陽上的人,不會認為是非正式的。他們這樣討論的時候,沒有科幻的概念,其實就是當作科學前沿問題在討論。
這一點是我們在書裡想強調的。因為很多現代人認為,如果當時他們在想這個東西,他們就是在做科幻,實際上在那個時代這些不是“科幻”。
觀察者網:現在的界限已經很明顯了,對普通讀者來說,或許很難回到過去的語境裡看他們的老作品。
穆蘊秋:可以說是現在人為的區隔。給你舉兩部經典著作的例子,作者來頭都很大,一個是法國的弗拉馬利翁的《大眾天文學》,另一個是紐康的《通俗天文學》。
弗拉馬利翁的《大眾天文學》,第四篇《行星世界》,圖片來源:catawiki
這兩位天文學家在寫大眾科普讀物的時候,非常認真地來討論月亮上是不是適宜居住,月亮是不是另外一個小地球,它是不是和地球類似。
在他們寫書的時候,這就是一個科學問題,後來我們國內引進這兩本書的時候,出版社都把有關章節刪掉了。為什麼刪?因為覺得兩個名頭那麼大的天文學家討論這樣的問題很荒誕,留在他們的經典著作裡,感覺會損害他們的形象,所以乾脆把它刪掉。
觀察者網:那麼對現在的很多科學家來說,會不會因為時代背景的變化,自己在心裡也有了科幻、科學這樣明確的區隔?有意識地去迴避某些內容?
江曉原:今天的科學界,即使在他們自己心目中,科學和科幻已經有區隔了,但是這仍然不排除,人們事後發現某些科研活動和科幻之間的界限仍然是不清楚的。
特別現在什麼腦科學、人工智慧裡頭的很多前沿理論探討,在未來可能又會被視作科幻,這個可能性仍然存在。這與你腦子裡有沒有把這兩個東西區隔開,沒有必然關係。
觀察者網:在書裡還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佔了很大的篇幅,就是《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編造關於月亮生命的新發現。天文學家約翰·赫歇爾確實去南半球觀測了,但《紐約太陽報》借這個由頭,連載了大量編造的內容,“躥升為美國報業界一顆閃亮的新星”。這裡面好像就體現不出本書想要強調的科學與幻想之間的良性互動,感覺科學只是被單方面地利用了一把……
江曉原:你這個感覺我覺得是對的,因為媒體就是要利用別的事物的,一直到今天,媒體也仍然毫不猶豫地把科學當作利用的物件,這個是正常的。
《紐約太陽報》最初的月亮騙局報道,宣稱赫歇耳在好望角的觀測有了大發現。圖片來源:hoaxes.org
觀察者網:我們觀察者網沒有這樣的利用吧……
江曉原:你應該有才對,沒有就不對了,這是正常現象。媒體就是找各種資源加以利用,科學當然也是資源之一,用一用沒關係。
當然《紐約太陽報》那個連載,那樣利用完全超出了我們今天通常認知的某種規範,比如說你們觀察者網肯定不會這樣搞的。
它這樣搞了之後,赫歇爾成了“受害人”。他曾想要給對方寫封信。但最後這封信是在他們家族博物館裡被發現的,根本就沒寄出。也就是說,他也沒覺得這事兒對他有多大傷害,否則他就寄這信了。
這也許能說明,這件事情跟赫歇爾其實關係不大,也許他覺得——當然這是我的猜想——這事兒並不壞。
穆蘊秋:倒是可以為江老師這個推論找一個證據,證據是赫歇爾太太瑪格麗特為這件事情也寫過一封信,是寫給卡羅琳·赫歇爾的。卡羅琳是約翰·赫歇爾的姑姑,也是個天文學家。信裡談到了月亮騙局這個故事,她在信裡面沒有說生氣,而是說這件事情很有意思,可惜不是真的,她只是表達了遺憾。
《紐約太陽報》售賣的印刷品,圖為號稱用藍寶石建造的廟宇,圖片來源:hoaxes.org
觀察者網:不過,媒體是否一定要抱著“利用”的心態?難道就不能像介紹一個朋友那樣,去向大家介紹科學發現嗎?
穆蘊秋:問題是赫歇爾沒有足夠吸引人的發現。他的望遠鏡是很厲害,但他就是去南非數南天空的星星,把恆星分等之類的。他獲得的這些發現,如果如實介紹的話,公眾對這些是沒興趣的。
江曉原:有時候真實的發現是很乏味的。所以有可能他覺得這事兒也挺好玩,也許他跟太太說,他們真是有點過分……但也沒生啥氣。
另一幅描繪月面生物的作品,圖片來源:hoaxes.org
穆蘊秋:你回頭去看,《紐約太陽報》設的局,其實是非常精緻的。連載裡面虛構的用望遠鏡獲得的成果很有想象力,除了月亮上的生命,還包括銀河系外行星。銀河系外行星什麼時候發現的?1995年,多超前啊,100年!這顯得赫歇爾的望遠鏡非常厲害。而且赫歇爾當時遠在南非,別人也沒有辦法向他求證,公眾就有可能相信。
赫歇耳在南非的20英尺望遠鏡,圖片來源:G.H. Ford所作版畫
觀察者網:這個關於月亮生命的連載,本身也可以說是劃時代的科幻作品了。
但我想到另一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裡面,也有一些關於月亮的故事,比如說嫦娥奔月、廣寒宮,但是我們後來好像就沒有什麼對月亮上“文明”的想象,書裡也沒有提及中國後來的科幻作品。
江曉原:這是原本研究的題目決定的,要是“地外文明探索”。晚清有不少中國人寫過科幻作品,但那是不一樣的,那些晚清作者知道自己在寫科幻小說,而我們這裡討論的很多例證,人家是作為科學前沿在討論的,也發表在學術刊物上。
這種情況和他自己意識明確地寫科幻小說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並不認為是在寫科幻,而認為自己是在搞科學研究、科學探索。中國當時確實沒有這樣的人。
晚清作品《月球殖民地小說》
觀察者網:可不可以提出這樣兩種說法:一個是中國人在接觸近現代科學後,想象的內容發生了文化上的斷裂,無法產生具有中國特色的“地外文明”想象;另一個是中國人在接觸科學的時候同時接觸了西方的科幻,想象空間已經被佔據了,至少在近代,寫科幻跳不出西方的框框。
穆蘊秋:關於文化的問題,我倒有一個想法。像“月亮幻想”這種文字,大概是從17世紀開始出現的,從那時候一直到近代,大概有成百篇這種想象到月亮上去的文字。但是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在17世紀之前這樣的文字沒有出現?
到目前為止,有一個解釋我是能接受的。17世紀之前在西方也好,在中國也好,沒有出現這種月亮旅行幻想的文字,這和宇宙觀念有關係。17世紀之前的那套宇宙觀念,像中國古代一直以來主要是“渾天說”,就是不利於產生這種文字的。
江曉原:我覺得還是第二種說法更好。已經有很多人編過清末的科幻作品選集,我從選集上看,他們實際上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來模仿一下。
當我們開始模仿西方作品的時候,其實意味著它已經把空間佔掉了,你只會往它那個空間裡走,而我們原來的世界觀跟它是不一樣的。
西方人的這種世界觀,哪怕是托勒密的時候,就認為外面的東西是一個外在的世界,那個世界本身是一個靜的、沒生命的東西。
可是古代中國人認為,我們之外的整個自然界,它是一個有生命、有意志的東西,是“天”,好像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生物裡,所以我們不會把這個“生物”想象成外在的。為什麼我們要講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因為我們覺得它不是外在的,所以我們幻想的路徑跟他們也是不一樣的。
觀察者網:但當基督教興起後,一切都是上帝創造的,那種內外有別的托勒密世界觀發生改變了嗎?還是說只是有了一個“形式”上的內外統一?
江曉原:對他們來說,其實“外在的世界”這個觀念的存在,和基督教的產生沒有必然聯絡。上帝創造的那個世界,其實跟原先基督教出現之前、沒有上帝概念時的世界是一樣的。
觀察者網:“外面的世界”骨子裡仍然還在,還是有內外之別……
(未完待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