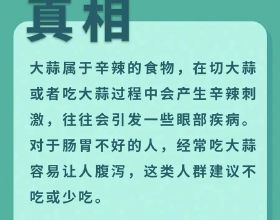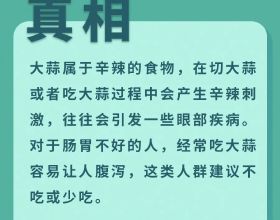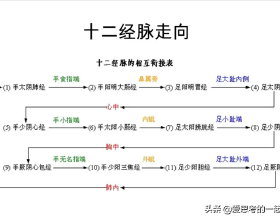(一)
在浩若煙海的古代文獻中,對巴國曆史的敘述大都十分簡略,有些還模糊不清,但成書於東周時期的《山海經》卻有五篇有關巴國、巴人的記載,它可以說是揭開巴國起源之謎的鑰匙。巴國尋蹤就首先從《山海經》開始。
《山海經·海內經》載:“西南有巴國。太莫生鹹鳥,鹹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
可作佐證的是宋人羅泌《路史·後記》上的一段話:“伏羲生鹹鳥,鹹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後煙後炤生顧相,降處於巴。”
從上述引證可知,巴人歷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我國上古的傳說時代,而且還與太莫、伏羲這些傳說中的氏族部落首領人物有親緣關係,巴人的出現應該更早一些。
我國著名民族史學家蒙文通教授在他的《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的地域》 文指出:“《大荒經》中曾四次提到巫山,這也是《山海經》其餘中所不見的。”蒙老指出巴國、巴人的記載也僅見於這部分。管維良先生在新出版的史學專著《巴族史》一書中認為:“巴國,巴人起源與巫山 、巫巴山地有直接的聯絡。”
近幾年,考古工作者還在今重慶市的雲陽、奉節、巫山及豐都和湖北巴東、秋歸、興山等地發現了數十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到了新石器時代,這一大片山地,氏族林立、部落棋佈,最著名的有忠縣哨棚咀和中壩,奉節老關廟、巫山大溪、大昌壩遺址;秭歸朝天咀、柳林溪遺址:宜昌中堡島、楊家灣遺址等等
(二)
關於巴族的記載,繼《山海經·海內經》之後,便是《山海經·海內南經》了:“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孟塗)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此事《竹書紀年》卷三亦有簡略的記載:“帝啟八年,帝使孟塗人巴涖訟。”
孟塗淮訟的地方就是巴人聚居的地方,這是解開巴人之謎的關鍵。有兩說:一是晉郭璞對《海內南經》這段話,註文:“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束七里,即孟塗所居也。”二是宋人羅泌《路史·後記·十三》的註文:“丹山之西即孟塗所埋地。丹山仍今巫山。”《巫山縣誌》卷十七亦云:“孟塗祠在縣南巫山下。”看來,孟塗斷獄訟的地點又進入今重慶境內了:實際上以上兩說並沒有矛盾,上古人的地理概念並不如現在這麼科學、精確,古代巫山的範圍比現在要大得多。這兩處地點都應在巫山範圍之內。上古時的巴人就生息、壯大在這裡。
目前要從考古學上證明夏代以前的巴文化其條件尚不成熟。然而,夏商之際的巴
文化遺存在巫巴山地則比比皆是。近幾年來,我國從十多所大學和一批文物考古研究單位調集和組織了六百多人的專業考古隊伍,配合三峽工程,在三峽庫區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勘查。新發現了 60 多處舊石器時代遺址,80 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更令人驚奇的是還新發現了 100 多處古代巴人的遺址和墓地,有關巴族的遺存及巴國的起源線索,現在越來越明朗了。
三峽地區夏商時期的文化遺存非常豐富,但以西陵峽河段發現的材料最多。文化面貌最清晰,文化序列最齊全,巴蜀文化的特徵最為突出,它是破譯巴文化之謎的要點。
西陵峽內夏商時期文化遺存,與四川、重慶地區發現的同期文化遺存關係極為密切。如陶器中燈座形器、鼓肩罐、卷沿圓底釜,竹節柄豆、尖底羊角杯、鳥頭柄勺等一組器物群體。而這些器物在西陵峽以西的江津王爺廟、忠縣井溝、巫山大昌壩、雙堰塘、火爆溪等遺址中也是常見之物;遠在四川廣漢三星堆、成都羊子山等遺址中所出土的器物類及其造型特點也基本相同;甚至與陝西南部漢江上游的“白馬石型別”的陶質器形和紋飾也相同或相近。如果按照巴蜀文化的考古學分期,三峽地區巴發現的這一類遺存,似可歸人三星堆文化系統,即早期巴蜀文化系統。那麼創造這支巴蜀文化的主人是誰呢?多數學者認為,很可能就是巴人的祖先。古代文獻透露,在我國夏商時期,巫山地區,即長江三峽地區,確實活躍著一隻被稱為巴的部族,他們很可能就是創造巴文化的主人。讓人驚歎的是,這一支巴文化遺存的時代和分佈區域,竟與《山海經》有關記載及郭璞的註解基本吻合,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也同樣基本吻合。據此,可以認為,夏商時期的巴族,大致是活躍在今川、渝、鄂、陝交界和接壤的地區,其中心應在長江三峽,這裡就是巴人的源和根。這裡是巴族立國的基地。
(三)
《左傳》衰公七年載:“禹聚於塗山......會諸候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晉。”由此可知,巴國和蜀國已是當時萬國中的諸候國,立國的時間比楚國為早,因殷虛甲骨文中已有“巴方”一名。
到了殷商之際,據《華陽國志·巴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戈後午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常璩所記這些史料,可以作為歷史的依據。因為它在先秦兩漢的史籍中,都得到了印證。
《左傳》昭公九年記周王室大去詹桓伯說:“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十也”由此可見,
當時巴國已統一到周王朝的政治勢力之下。西周初年,成王大會諸候於東都洛邑,《逸周書·王會》記載這次盟會上,巴人曾向周天子貢獻比翼鳥。由周王室宗族分封建立的巴國,還和楚國有婚姻關係。《左傳》昭公十三年:“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壁見於群望日:'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壁於大室之庭。”參與此次選擇楚國君王接班人這一大事的巴姬,就是屬於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巴國君主的貴族婦女,因此才有巴姬之稱。
巴國和楚國的政治與文化的聯絡是相當密切的。《左傳》桓公九年記:“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這件事發生在東周初年,可見降至春秋不久,由於周王室衰敗,楚國逐漸強大,巴國不得不依附於楚:但這時楚國並沒有完全控制巴國。楚文王時《史記·楚世家》說:"楚強,侵凌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到楚成王時,“布德施惠,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這時,楚國實際上已成了南方夷族和越族各部落和小國的仲裁者。
(四)
春秋時,楚國的疆域逐漸擴大,而且主要是向北面、西北面和東面延伸。從《左傳》所記聘鄧、伐申、滅庸、伐楚、圍以及與鄰近來看,這時巴國地望,大體在楚與鄧國之間,其中心地區在丹、淅二水與漢水交匯之處。後來又發展到了漢中、巴山。《戰國策》中“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是巴國在漢水流域的明證。《牧誓》所舉西戎八國皆近漢水,故巴國實為漢水上游之國。至於清江流域的巴族和五溪蠻中的巴族乃戰國時受楚逼的情況,史籍上是清楚可考的,另作專論,這裡不必贅述。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欒貞子對晉文公重耳說:“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說明漢水北面的周初分封的各姬姓國,當然也包括巴國在內,都被楚國滅掉了。不過,古代滅國,並非滅絕其國家,往往仍保留其宗國地位,達到征服的目的而已。所以這時巴國依然存在。
作為土著居民的巴族,透過兒百年的時間,在巴山地區不斷繁衍,最終因受強秦、強楚所迫,幹是向川東川北和川南發展,繼續與秦、楚、蜀三國抗衡。
《華陽國志·巴志》認為:“秦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實際上,這時的巴國已逐漸成楚國的附庸國了。《十道志》記:“楚子過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五溪,各為一溪之長,號五溪蠻。”此事可能發生在楚威王時,即公元前 339 年至 329 年之間。其時已進入戰國中期晚段。《郡國志》記載:“巴城在漢南江,楚襄王滅巴,封其子為銅梁侯,故有此城。”《輿地紀勝》也有同樣的記載:“禁襄王滅巴子,封廢子於濮江之南,號銅梁侯。”又據《方輿勝覽》所記:“五照南里,有巴子城,乃周武王封其支庶處,在涪江南銅梁山下。”由此可知,在銅梁的巴族後裔,仍屬周王室支庶的一系。這一支巴人既不願流人五溪,而又服屬於楚,所以才回到封地,按慣例照舊管領巴人。
又據《華陽國志·巴志》載:“蜀王伐苴候,苴候奔巴,巴為求救於秦,秦惠王遣司馬錯伐蜀,滅之,並取苴與巴,執王以歸。”這件事較楚成王滅巴稍晚。據《史記·秦本紀》和《史記·六國年表》記,在公元前 316 年,秦滅的巴,即楚威王滅的巴國之流散者建立的一個國家。秦昭王三十年,秦奪楚巴,黔中,深入楚境,進一步佔巴國和他新封的巴國。蜀國滅亡後,和巴國一樣,數百年間,蜀國的宗族支庶,還有安陽王子和青衣王子的存在。《史記·越王勾踐傳》記楚成王滅越後,“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朝服於楚。”瞭解這些史實,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幾個巴國的存在,就不足為奇了。
如前所述,至戰國之時,巴在受到楚國和秦國的不斷強大的威脅下,急劇地在今四川發展,並建立了一個較大的領土製國家。對此,《華陽國志·巴志》說:“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其疆域是“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在這個巴國疆域範圍之內,還雜居有濮、富、苴、共、奴、禳、夷、蛋等多族落,他們大多還是處在父系家長奴隸制階段,但其中也有 :些首領稱王或稱侯的。
(五)
秦漢以來,相傳巴為廩君之後。《世本·氏姓篇》雲:“廩君之先,故出巫誕。”誕與蛋通,或作但。《說文》謂:“蛋,南方夷也蛋”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徐中舒先生在《論巴蜀文化》一書中認為“巫是地名,蛋是族銘。”“巫”是指巫山、巫峽 帶,當然包括三峽;“蛋”是指在船上生活的民族,為漁民。巫蛋與廩君有親緣關係,均屬巴。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在清江流域定居的巴人,其祖先同出於巫蛋。巫蛋中的巴氏與清江的群蠻結合,併成為廩君巴或稱虎巴。
范曄所著《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說:“巴郡南郡蠻共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拐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不蟲,與諸蟲群飛,蔽掩曰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曰。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乎君於夷城,四姓皆臣之。”
此說出自《世本》。《世本》相傳是西漢劉向所作的書,這應是廩君巴族最早的傳說。儘管所述多帶有神話色彩,沒有足資稽考的確切年代,雖不能視為信史,但仍可作為研究巴國曆史的參考。
如果按照唐人章懷太子注所說廩君之後的活動路線,大致是:“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注中所指清江,古名夷水,源出利川縣,經恩施、巴東、長陽、宜都(今枝城市)而入長江。戰國時巴為楚所逼,退居於此。以後巴人就沿著這條路線而逐漸向西發展。《水經·夷水注》說:“若廩君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衛。”《江水注》又說:“捍關,廩君浮夷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借險設關,以相形捍。”捍關,史家原考定在長陽,其說有誤,徐中舒等考定在今奉節。弱關,在今秭歸縣之西,即瞿塘峽、巫峽所在地。捍關原為巴國所置,但旋即為楚所得。《史記·楚世家》說:公元前 377 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捍關以拒之,”捍關的屬楚,當去此後不遠。《史記·秦本記》說:“楚自漢中,南有巴黔郡。”捍關既屬楚,則遠在捍關以東的弱關轉入於楚就更不待言了。《太平寰宇記》於板木盾蠻下說:“其在峽中(即三峽)、巴、梁間,則為君之後。”由此可知,戰國時代捍關和弱關的屬楚應是宗主權由蜀轉入楚,其居民仍屬巴族,這一情況,降至唐宋時期,也沒有變更。
《華陽國志·巴志》在述及巴國的故都時說:“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閩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東突峽下畜沮是也。又立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裡是也。其郡東枳,有明月峽,廣穗嶼,故巴亦有三峽”。這應是戰國時巴國的舊都。其最東的平都,即今豐都縣;枳,為今涪陵市;江州今為重慶市;墊江為今合川縣;閩中今仍名閬中。由此可見,巴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應在今四川重慶境內是不容置疑的。
綜上所述,巴國的歷史可追溯到我國上古的傳說時代。巫山地是其發源之地。夏商時期巴人大致是活動於今川、鄂、陝交界地區,其中必在長江三峽一帶。商末,巴國曾隨周武王伐紂,後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降至春秋之世,巴國地望與楚國,鄧國為鄰,即今丹、淅一水與漢水交匯之處。因受秦、楚所逼,巴國又從漢中、巴東等地向川東、川北、川南發展。進入戰國,“七國稱王,巴亦稱王”。隨後不久,楚襄王滅巴,封其子為銅梁侯。巴國故都在江州,巴先王陵墓多在積。
清江流域的廩君,也是出自巫蛋,但並不是巴人的遠古的祖先,只能是巴族中的一支。從時間的先後次序分析,從地理位置看,原川東、今川北、川南等地巴人,清江流域的巴人,貴州烏江、五溪的巴人,很可能是今漢水上游的巴人向東南遷徒移動的結果。他們可能都是“巴方”的後裔。巴人起源之謎從本世紀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史學界對“巴”字的含義和巴人的起源有多種說法。其中,有的認為“巴”指動物,如蛇、蟲、蟒、魚、蠶;有的則將“巴” 解釋為對山、水、石頭的稱呼。近年有學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稱呼老虎的一種發音。據史書記載,巴人認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圖騰,因此巴人自認為是虎之族,以虎為崇敬物件,自稱“虎(音巴)人”。於是,中原及與巴族為鄰的人,皆稱其為“巴人”。
巴族的構成,主要有兩大部族集團。一是從東方遷到今渝、鄂、湘、陝交界處的廩君族:二是原來就生活於此的土著部族,如:濮、苴、共、奴、口(左亻右襄)、夷等。巴的核心廩君族來自什麼地方呢?早期的姓氏書說,巴與秦、徐、鍾離等一樣,同源於一個“嬴”姓祖先或氏族部落。我們知道,秦、徐、鍾離等是源出“東夷”的民族,其發源地在今淮河流域至山東半島一帶;既然巴與秦、徐皆出於“贏” 姓,那麼巴人廩君族的最早的居住地,應當到東方去尋找。
關於廩君族的形成,史書上是這樣說的:巴氏、樊氏、口(左目右覃)氏、相氏、 鄭氏五姓 ,共同生活在一個叫“武落鍾離山”的地方。五姓的首領聚在一起時,定出了選舉共同君長的兩個辦法。一是看誰能將短劍擲中半山腰的石穴,二是看誰能乘陶船於江中而不沉,皆勝者即為君。競技的結果,是巴氏年輕的首領務相連勝,他於是作了五姓共同的君長,史稱“廩君”;這五姓結盟形成的部族共同體,就叫“廩君族”。
當然,巴人真正成為一個有共同疆域、同一語言和文化的民族,還是在廩君族西遷到今鄂渝交界處以後的事情。在這裡,以巴氏等五姓為主構成了巴族的“核心”,可稱之為“內五族”,而以原居於渝、鄂、湘、夷、濮等被廩君族融合或征服的土著部族,構成了巴的外圍部族,而當時的史書把他們均稱作“巴人”
近萬件文物及墓葬 證實“巴人”故里在清江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其先祖巴人的發源地卻一直未得到考古學界確認。最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善才證實,中國最早“巴人”起源於清江長陽。
巴人是開創“巴蜀文化”的“主力軍”,早期歷史在距今 4000-3000 年間,其起源眾說紛紜,有“巫山起源說”、“陝南漢水說”、“甘肅天水說”、“丹江說”、“湘北嶽陽說”等,但都未得到證實。
王善才說,考古隊在位於長陽漁峽口鎮東南清江北岸的“香爐石遺址”,挖掘出石器、陶器、骨器等近萬件文物,以及一批早商時期的巴人墓葬。獸骨、魚骨和陶網墜等文物,具有典型的巴文化特徵,時間也正好與我國早期巴人的活動時間吻合。由此證明,鄂西清江流域,為我國巴人起源和頻繁活動地區。
該考古發現,部分解決了我國土家族的族源問題,也揭開了我國古代早期巴人故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