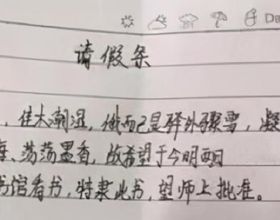近日,微信上讀到紀念許國璋先生的文章,不覺想起三十幾年前的往事。
當時,母親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系教書,我家住在北外西院19樓4單元。許國璋先生原住西院北樓,那樓住了不少老教授,像周珏良、危東亞、柯魯克和伊莎白夫婦等。八十年代中期,學校新建了幾棟宿舍樓,給幾位居住面積不達標的老先生,每人補了個一居室,許先生也得到一套,位於19樓1單元1層。於是,我有幸跟先生成了一棟樓裡的鄰居,與他常在樓下或院裡相遇。
圖:許國璋先生在家中。(圖片來自網路)
那時的許先生應該是七十歲左右,喜歡穿件絳色粗呢西裝,足蹬牛筋底白皮鞋。記得一位熟識的英語系女生說,有一年,先生從香港講學歸來,跟系裡學生們講話,其中說道:女生應該把高跟鞋扔了,運動鞋配裙子才美。她還說,每年開學,許先生都自掏腰包,用稿費買漢英詞典,每個新生,一人一本。當時,先生主編的“許國璋英語”,火遍全國,年銷售幾十萬冊,他從所得稿酬拿出不少用來資助英語教育。
圖:“許國璋英語”書影。(圖片來自網路)
許先生是北外校園的一景。
每天下午四點左右,是先生休息的時間。常可看見,他坐在面對學校大門的樓前花壇水泥圍牆邊,手裡拿著剛從小賣部買的紙杯冰激凌,津津有味地吃著,看著過往行人和車輛,怡然自得。時有路過的教師或學生,認識先生的,就會駐足跟他聊上幾句。
當年,出了北外西院大門左拐,人行道邊有一溜賣菜的攤販。一次,見許先生走到一處魚攤前,一言不發,那魚販立即從盛滿水的黑色塑膠大袋裡,撈出一條活蹦亂跳的大草魚,用草繩穿好,遞到先生手上。先生提起魚,掉頭就走。我驚詫魚販不稱重、先生不付錢,便好奇地小聲打探,魚販笑答:“他一個月一結。”又有人問:“這是誰呀?”魚販得意地說:“他是北外最有名的教授。”
有時,可以看見許先生和許師母一起出行。總是許先生走得快,許師母走得慢,落在後面幾步。師母走路不太靈便,她那雙腳彷彿是解放腳,即小時被纏過足後又放開的。許師母,瘦高個兒,細白面板,鵝蛋小臉,大眼睛,仍能看出當年風姿的綽約,聽說年輕時她在上海做過舞女。
圖:許先生、許師母和學生。(圖片來自《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
一居室是許先生的一塊飛地。他每天從北樓過來做事。有時,飯點兒,許師母過來叫他回去吃飯。有時,做事做晚了,他也住在那裡。
許先生在飛地的小院裡,種了些花草菜蔬。小院近旁的道路略高於樓前地面,站在路上可以望見院中情景。常見許先生站在路邊,微笑著欣賞自家院裡的蔥蔥郁郁,並不時和路過的人討論幾句。一次,見他站上路邊矮牆,傾身檢視小院裡面的植物。那院裡生長的荷蘭豆,曾讓季羨林先生讚不絕口:
“他(筆者注:此指許國璋先生)在自己的小花園裡種了荷蘭豆,幾次採摘一些最肥嫩的,親自送到我家裡來。大家可以想象,這些當時還算是珍奇的荷蘭豆,嚼在我嘴裡是什麼滋味,這裡面蘊涵著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詞彙來形容,什麼‘鮮美’,什麼‘脆嫩’,都是很不夠的。只有用神話傳說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藥)一類的詞兒,才能表達於萬一。”(季羨林《悼許國璋先生》,《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0頁)
季先生的描述絕非誇張,八十年代,荷蘭豆對於很多城市的居民,確是特別稀罕的美味。我們第一次吃到,還是在昆明的叔叔、嬸嬸,乘飛機來京時帶的。碧綠碧綠的顏色,清脆甜嫩的味道,在當時蔬菜匱乏的北京,真令人嘖嘖稱奇。上海的姑奶奶也嘗過這來自昆明的饋贈,一次叔叔又要去上海,老人家特別叮囑:“再帶些像翡翠似的菜吧。”
許先生還種了些爬牆虎。飛地在19樓東端,爬牆虎順著高樓東牆,向上攀緣,長得飛快,不知什麼時候,就從一層爬到了頂樓六層,枝繁葉茂,差不多鋪滿了整個牆面。夏日,一牆青翠;秋來,滿目殷紅。
1993年某天,聽說許先生夜裡從飛地的行軍床上摔了下來,中風了,就此一病不起。又聽說是因先生此前赴歐講學,過度勞累所致。第二年秋天,許先生過世,享年七十九歲。
圖:《許國璋論語言》書影。
記得八十年代末,當時社會上還殘留著一些極左文風,文章開頭不乏“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等套話。導師張志公先生曾對我說,一次應邀參加許國璋先生博士生論文答辯,看到文章中有“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語句,便在提問時請那學生把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簡要說出個一二。許國璋先生聞之驚愕:
“還有這個?我怎麼沒注意到。”
拿過論文,翻到出處,抬頭對學生說道——“你把這句刪了。”
圖:《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書影。
手上的《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是1997年在北外西院大門外學校出版社讀者服務部買的,從書中文章瞭解到,許先生雖去過很多國家,可從沒機會到訪歐洲大陸,一直念茲在茲,心馳神往。那次,本來說好由一學生陪同,最終不知何故變成隻身前往。他萬里走單騎,講學遊歷了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義大利、瑞士、俄羅斯等國。畢竟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怎麼禁得起如此辛勞的旅程?
圖:1993年5月,許國璋先生在蘇黎世湖上。(圖片來自《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
再次翻閱《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眼前出現先生在“大如劇場的電教館”演講的身影,鏗鏘的話語震響耳邊:
“我教學生,從來不以教會幾句英語或教會一種本事為目標,而是要教怎樣做人,是英語教育,用英語來學習文化、認識世界、培育心智,而不是英語教學。我們的理想要高一點,要做一個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只想練些應酬英語,到合資企業去跑腿,去做翻譯,目標太平凡也太庸俗了。你就是做了合資企業經理,舉止是不是要有修養些?談吐是不是要更典雅些?寫作時筆下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文化內容?否則你每月掙成百上千,我也很鄙視你。我一般不隨便跟人說話。你要跟我說話,我首先要看你有多少文化內涵。否則我這樣一個教授,來陪你練英語?
現在外國人來,不論老太毛孩,一律號稱專家。專什麼家?有的不過會說外語,不要把他們看得太了不得。他們是專家,那麼美國大街上走的都是專家了!他們見了我還是畢恭畢做的,不敢在我面前放肆,妄議‘你們中國人如何如何’,因為他們知道我的語言水平比他高,分析問題比他深刻,他受的教育、讀的書不能跟我比啊!”
(傅傑《這就是許國璋教授》,《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85頁)
這真是空谷足音,廣陵絕響。
許先生和許師母沒有小孩兒。
許先生走後,在校園裡很少見到許師母了,那滿牆的藤蔓也漸枯黃衰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