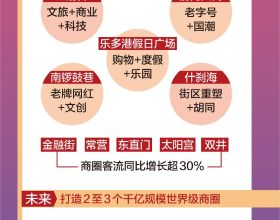很思念一個人的話,晚上會夢見。
去上海看望她,那座著名的艦艇式建築,四樓,你敲門,她開門,笑逐顏開,謙恭地叫一聲“王老師好!”她會招呼你“進來進來”。抬眼,總是那麼神清氣爽,容光甚好,眉目淡雅,言笑晏晏。尤其是那對眸子,很少有老人擁有如她那般朗潤清澈的目光。她會叫你坐下,讓你吃茶几上備好的各色小零食。你若只是口中答應,而不伸手,她就塞到你手裡,然後開始問你工作好不好,身體好不好……
這一切,原本是現實,而今成了夢境。
記得之前每次給她打電話,最後的結束語肯定是:“您一定要注意身體,我沒什麼別的要求,就是要求您一定要注意身體,年紀大了,懂不懂?”語氣苛刻,近乎“教育”。掛上電話,方才察覺自己太不禮貌。但她應得很好:“我曉得的”。我偶爾也擔心她是敷衍,但我“小人之心”了。她理解你的誠意和關切,便不會辜負。有一次我跟她說:上海最近霧霾天,您去劇院之類的公共場合,記得戴口罩。她照例答應。幾天後我在微博上看到有博友拍到她,真的帶著口罩,於是放心。有時候,她接起電話,我還沒開問呢,她自己先“彙報”起來:“前段時間我感冒,住院一個月,現在已經出院了。”“前段時間我病了,動了個小手術,現在已經好了。”一句話語,聽在耳中,驚心動魄,我那一刻的心電圖大概是一幅凌亂的正弦函式。
其實王老師的身體一直不錯,又是積極樂觀,單純開朗,溫和善良的脾性,甚至還有點孩童般的狡黠和淘氣。原本,這樣一位精神矍鑠,神采奕奕的老人直到期頤之年,不在話下,然而……
越劇《孟麗君》
王文娟——孟麗君
都說“人生識字憂患始”,我在識字的年齡便看戲了。“我鯉魚真是眼睛亮,草堂燈下選才郎”,她在大銀幕上水袖漫卷,歡快地唱著,令我驚為天人。但我不知道那“鯉魚精”的扮演者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她還有一個更為家喻戶曉的角色是“林妹妹”——那時候,我所記住的只有她的樣貌。
大人總覺得小孩子的喜歡,三分鐘熱度。我的這份喜歡卻很持久。有人問過我:你怎麼會堅持喜歡越劇這麼多年?我糾正:不是“堅持”,堅持是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是需要意志力的積極參與的。我不是,我是自然而然,樂在其中。可一個學齡孩童看《追魚》,也看大不懂的吧?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有意義啊,哪怕我是將神話當童話在看,那裡面也有對孩子真善美的啟蒙。起碼讓人明白:在兩個一樣花容月貌的女孩中,善良,多情,不離不棄的那個更可愛也更可貴!
彼時我雖年輕,卻不顢頇,知道少年人的喜歡易盲目。什麼是盲目?沒邏輯,不思考,無理由。畢竟我對她的所有美好感覺,都來自那個婉約的劇種,那方神奇的舞臺。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我無從得知。
直到後來,我有機會認識了她。
越劇《孟麗君》
王文娟——孟麗君
去見她之前,也擔心,也害怕,也焦慮,也忐忑,待真正接觸到,發現:她根本就是個慈祥,溫和,逗趣,可愛的老奶奶。所有心理上的猶疑和負擔,瞬間冰釋。而且就她的觀察能力,絕對能感知到我的拘謹和侷促。她總有辦法消除你那些不必要的緊張。總之:和她在一起,如坐春風,如沐暖陽。
她的敬業精神是自不待言的。我問過她:“那一年,你喉部長了息肉,為什麼動完手術,就去唱《則天皇帝》了?”
“票已經賣出去了麼!”
我“爭辯”:“票是賣出去了,可您還沒痊癒呀,那戲的戲份又多,要是把創口唱開了,怎麼辦?”我盯著她的表情看。
她似乎不以為意:“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
“那個時候”指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彼時特別強調公而忘私,個人服從集體。甚至可以說在集體面前,個人的利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我暗暗嘆息:自己和她到底不是同時代的人,無法感同身受,焉能求全責備。但就情感而言,我還是有些不平,於是心裡嘀咕:“‘那個時代’啥樣呀,哦,下了手術檯,就上舞臺的時代啊”。好在,她吉人自有天相。
我所記得的大都是她快樂的樣子。那種生動活潑的表情,那種開完玩笑,還給你解釋一句“好白相呀”的樣兒。有時候,她也會露出一些哀愁,情況不多,我記得的也不多。那次是因為什麼呢?哦,是因為很忙很累,事情非常多,她說晚上都失眠了。我說那不行,總要想想辦法。“也沒有什麼辦法好想,吃安眠藥咯”。大概我不由自主地鎖起了眉頭,她見我那樣,倒過來安慰我:“做人麼,有時候就是這樣的!”我當時不解,這算啥解釋?多年後回思此言,在她對人生的痛苦艱難貌似淡然,實則堅韌的接受上,有著一種老子哲學的深邃智慧。她也許不讀《老子》,可她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理解了這些最悠久最致用的道理。
先生孫道臨老師走了之後,她很低落,有一次跟我聊起老先生生前的病情轉折,言辭間雖沒有特別表露情感的話語,但偶有語音顫動,那份傷心其實一覽無餘。有好幾次,見她差不多已經淚盈於睫了,我便相當不安,惱恨自己無能透頂,白活了這麼久,居然沒有積累丁點安慰老人的經驗。
對不起,我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思緒挺亂的,所以絮絮叨叨,斷斷續續,東拉西扯,缺乏條理,想起一點寫一點,不過點點滴滴都是生活中的王老師,樸素且真實。
還有一次是我們隨便聊著,有人敲門,進來個男的,把一袋東西放在桌上,道了聲“王老師,那我先走了哦”,便兀自離開。我覺詫異,心想:“這人誰啊,怎麼自說自話,放下東西就走人”。王老師倒見怪不怪,站起身來,走到桌邊,回頭向我招了招手,臉上帶著種又樂呵又期待的表情,把那袋東西解開。
我探頭問:“是啥呀?”
“燒餅!”
“額,他為什麼特地給您帶燒餅過來?”
“我喜歡吃燒餅,附近的不怎麼好吃,我知道有個地方的燒餅好,他經過那裡,就幫我帶過來了!”
說著,她遞給我一個,我趕忙接著。因怕芝麻落在客廳地上不好,我提議去廚房吃。然後一老一少,就坐在她家廚房餐桌旁啃燒餅,想來那場景也蠻有趣。
剛咬了沒幾口,她忽然問我:“你那個是甜的還是鹹的?”
我楞了下:“鹹的。”因沒想到她會問這個問題。
她說:“我這個甜的,蠻好我這個也是鹹的喏。”
我說:“您喜歡鹹的,換一個吧!”
她說:“不好浪費,甜的也好吃的。”
我在她的眼中,大抵首先還是個孩子,一個喜歡越劇,喜歡她的藝術的孩子,畢竟我和她的年齡差了半個多世紀。但她從來都是將你當作一個平等的個體,是不會因為你年輕就輕視你的那種長輩。這一點殊為不易。我見過太多年長的人,儘管表面上平等,潛意識中依然存在著對晚輩意見及情感的漠視,王老師則從來沒有過。而且我發現,若是在公眾場合見她——有時候她去參加某個活動,我有時間會去看她——她會和你握個手。我那時候哪裡有握手的習慣呀。秋冬之交去看她,天寒,我手涼,她一握:“喔唷,儂手介冷,出門來衣裳要多穿點的。”我趕緊“嗯嗯”,心裡甚是溫暖,想著,我自己沒心沒肺,她卻在關心我呢。後來我每次見她前,總會記得先把手呵呵暖,搓搓熱,別把她凍著,那時候真的是曲裡拐彎的小孩子心性啊。
王老師很美!生活中典雅端莊的自然之美,舞臺上精益求精的藝術之美,還有日常交流中,諧趣生動的人情之美。我去看望她的機會其實並不多,每次都事先約好,上午九點左右到,近午時分,不便多擾,我即告辭。她約莫是看出我掩藏不住的留戀。一次,她說要去參加個活動,正好這個點也得出門了,讓我等她一下,她換件衣服一起下樓。她在鏡子前比比這件,依依那件,回頭還衝我笑:“臭美伐?”把我給樂的。然後我就安心等著她。心想:您多挑一會兒吧,我就這樣坐著看您,看到地老天荒才好呢。我正胡思亂想,她驀地又回頭:“你覺得,我穿綠顏色格件好,還是紅顏色……?”我脫口而出:“紅色的好,紅色的喜慶”。我不愛拘束,說話喜直接。所以經常說錯了話,得罪了人,亦不自知。這毛病多年來改不掉,後來也懶得改了,愛咋咋滴。偏偏在她這樣一位大藝術家面前,反是徹底輕鬆,心裡怎麼想,嘴裡就怎麼說:“紅色,您穿大紅色的,最好看了!”她大概覺得我是年輕人愛誇張,“噢喲”了兩聲,轉而又問:“是伐?”“是啊是啊”。其實我還想說“您穿什麼都好看”,但這種話,即便完全發自肺腑,真說出口來,總會叫人覺得傻乎乎的吧,算了,憋回去。
她的“美”還表現在一些若不經意,你便發現不了的細節裡。和王老師一起坐電梯,當時有不少人,我性子急,見人家進電梯,我也要進。王老師拉住我:“他們先上,我們等一歇好了。”而等電梯門再開,我見她進去後,用一隻手輕輕地攔在了門檔處——她是為了防止電梯門自動關閉時,夾到還想進來的人。像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越劇《紅樓夢》
王文娟——林黛玉
徐玉蘭——賈寶玉
王老師願意給人一個好的印象,可她毫不矯飾。某次,見到她以後,發現她老是用手捂著右邊腮幫子。我納悶:“王老師,您怎麼了?”
“我這裡一顆牙齒拔掉了,要過兩天才能去裝好。”
“那您別捂著了,老抬著手,怪累的。”
她不好意思起來:“現在這樣很難看的呀!”
我在心裡笑她,老人家這愛美的小心思喲:“拔牙了麼,很正常的,不難看,真的一點都不難看!”
然後她就把手放下來。
“那您牙齒疼不疼?”
她說“疼倒是不疼的。”
“嗯,不疼就好。”我邊說邊拿茶几上的小零食吃——這麼不把自己當外人,都是她的好脾氣給慣的。
王老師和徐玉蘭老師參加完央視《藝術人生》不久,我正好打電話過去。她問我:“你從電視裡看,覺得我那件衣服好看麼?”
我說:“挺好看的。但以前沒見您穿過這件,新做的吧?”
她說是,然後又問:“你有沒有感覺這件衣服顏色太沉了?”
我很認真地想了想,那衣服的顏色是紫色和橘色的,圖案較大,她這麼一問,好像在色彩上是過於沉穩。但什麼沒感到滯重感呢?略琢磨一會,我告訴了她我的真實感受:“顏色客觀來說是略沉,但您不說的話,我都沒意識到。這可能是衣服不對稱的設計式樣使然,那種貌似不和諧的搭配,反而形成了一種輕靈感。於是就不會讓人覺得顏色沉了。”
她似是同意我這個看法的,在電話那邊若有所思地“哦”了幾聲。
越劇《紅樓夢》
王文娟——林黛玉
我還曾帶了她早年的一盒磁帶去給她聽。她居然邊聽邊皺眉毛:“嗓子不好,唱得也不行”。
我自是不同意這評價:“明明就很好麼”。我覺得說“很好”還不足以強調她的唱功,再加碼:“很好,非常好!”語氣簡直是倔強孩子硬要跟大人唱反調。
她笑,一臉“你這孩子,無可救藥”的表情,轉而用考驗般的眼神看我:“個麼,儂講啥地方好啦?”
我說:“味道好,韻味多好!您再聽聽?”
這次她可能覺得我的話並非全無道理,唱戲唱味,她順著那調子搖頭晃腦了幾下,沉浸在了旋律當中……她那個情態,真像一幅畫啊,淡墨寫出無聲詩!
後來,我便很少去看她了。她那時候,快近九十了,我怕太過打擾。
“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朱顏辭鏡是不怕的。其實當你由衷尊敬,喜愛一個人的時候,外表根本不算什麼。只要你知道那個人,她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開開心心地生活在某個地方,你就是滿足的。
我如今也是馬齒漸增,人生遇事亦多,終是浮雲過眼而已。想想,什麼是喜歡?就是總想著能為她做點什麼,就是,想起她,對著空氣也會微笑,就是,明明見不到她,知道她一切好好的,過的開心舒適,便無所他求。王老師是那種,你越是瞭解她一點,就會越喜歡她一點,你越是喜歡她一點,就越會覺得自己幸福,幸運的人。
我也並非沒有見過人間生死。可當知道她真的已經離開,霎時間,多少回憶,紛至沓來,多少情感,決堤而出。我知道面對這一切,所有人都無能為力。我們每一個人,無論彼此有多深情,有多愛重,最後終將分離!我們終難突破的就是那道生死的關隘。但謝謝您,謝謝您帶給我們的那些美妙旋律,動人演繹。願您在那個世界依然有著美好的笑容!我喜歡鯉魚精,喜歡孟麗君,喜歡林黛玉,我更喜歡您!
前生今世之事,想來荒誕無稽。可自您走了後,我破天荒地希冀能有來生。如此,便能將這一世對您所有的牽掛和不捨,償之來生……
▲
-END-
文 | 清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