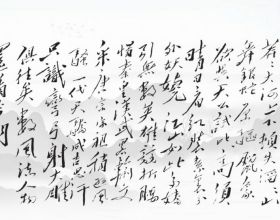這天上午,沙河鎮美蝶毛紡廠業務員白玉蘭回廠裡彙報與臺商商談情況,踏進廠門,她便覺得有些異樣,平時見了她都親親熱熱客客氣氣的同事,此刻好像換了副面孔,不是怔怔看著她,就是對著她嘿嘿冷笑。她心裡不由納悶,但一時也顧不得細想,抬腿便跨進了廠長辦公室
四十多歲的嚴廠長正在打電話,看見白玉蘭,先是怔了怔,然後放下電話,不自然地笑了笑說:“你回來啦。”“廠長,我…
白玉蘭剛開口,嚴廠長便擺著手說:“別的改日再說,現在最要緊的是,你先回家好好休息,最好能去醫院看看。”
“什麼?”白玉蘭似乎沒有聽清嚴廠長說的是什麼。
“玉蘭同志,這是廠裡領導對你的關心!事到如今,你也不要太難過了,還是好好治療吧。”嚴語氣顯得沉重。
“廠長,你的話我怎麼一句也聽不明白呀?”白玉蘭猶如跌進了雲霧中,茫然不知所措。
嚴廠長依舊不緊不慢地說:“玉蘭同志,你就別裝糊塗了,我知道你是為了我們廠才弄成這樣的,我們也不會見死不救的。”
白玉蘭越聽越糊塗,看著廠長半天也反應不過來。
嚴廠長轉身對一位二十多歲的高個青年說:“小何,你開車把平詩同志送到縣醫院去”
小何是廠長小車的專職司機,聽到廠長盼咐,便走到白玉蘭身邊,說:“白大姐,我們走吧。
“我沒病!”這時,白玉蘭突然大聲叫喊道,雙目圓瞪,白淨的臉漲得通紅,隨即一把抓過廠長的手,急切地向道:“廠長,你要說個明白,我究竟得的是什麼病?
“別,別這樣!”嚴廠長像見了鬼怪,驚得往後退,一邊大聲吩咐:小何,還不快把她送走!”
小何也不敢上前拉她,連聲懇求白玉蘭隨他上醫院。白玉蘭只好上車。
上車後白玉蘭反倒安靜下來了,她整整凌亂的衣衫,平心靜氣地說:“小何這裡只有你我兩人,不要顧忌,告訴我,我究竟得了什麼病?”小何沉默了片刻說:“白大姐,不怕你怪我,我也是聽大家說的,他們說你得了艾滋病。是你跟臺商鬼混,給傳染上的。”
“啊!”好似一聲驚雷,震得白玉蘭渾身顫慄,頭腦嗡嗡作響。這太突然了,想不到自己為廠裡日夜奔波操勞,如今竟落得個蒙冤受辱的下場。委屈、痛苦交織著,一陣緊似一陣撲向她,同時一股怒氣襲上心頭。自己沒招誰惹誰,是哪個缺德鬼暗箭傷人,陷害無辜?她要去廠裡問個明白,於是叫嚷著要小何停車。
小何只當沒聽見,照樣把車開得飛快:“大姐,你不要太難過了,事到如今,還是想開些吧。”
“小何,快停車,我求求你了!”白玉蘭俯身去奪小何手裡的方向盤為防意外,小何只得把車停下。
下車後,白玉蘭急匆匆返回廠裡,小何要帶她同走,她心裡有氣不願再坐車,小何只得開車先回廠裡。白玉蘭走著走著,突然犯了嘀咕,唉,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縱然有千百張嘴也說不清了呀!你越是急著解釋,大家越是當真,事情也就越糊塗。不如聽廠長的話,去醫院,有病沒病,一檢查便可知曉,然後把檢查的結果公佈於眾。到那時,有了真憑實據,大家總不會再胡言亂語了吧。想到這裡,白玉蘭轉身走向醫院。
出乎她的意料,在醫院門口,白玉蘭竟然見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怎麼會來這的?他得了什麼病?頓時,她急不可待地追問丈夫。
丈夫名叫徐華,此刻正滿臉憂鬱,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好像不認識白玉蘭似的,低著頭默不作聲,自顧往醫院外面走去。
白玉蘭忘了自己來的目的,緊走幾步,趕上丈夫,然後扶著他,關心地問:“徐華,你得了什麼病?為什麼不告訴我?”
徐華厭惡地甩脫她的手,緊閉著嘴,不說一句話。
白玉蘭的心被狠狠刺了一下,眼睛裡不由含滿了淚花:“你為什麼不說話?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你快說呀!”
“你做的事,你自己明白!徐華終於冷冷地說了一句。
“我不明白。”
“你想害死我!”
聽到丈夫這麼說,白玉蘭頓覺迷惘:“徐華,你犯的是糊塗病吧?我是你妻子,怎麼會害你呀!”
徐華厲聲說:“我問你,你在賓館幹了些什麼?”
“跟臺商談投資的事呀。”
“真的這麼簡單?”
這時,白玉蘭心裡已經全然明白了。她不禁冷笑一聲,說:“你是想說,我跟臺商睡覺,而傳染上了艾滋病,然後我再傳染給了你,你就來醫院檢查,怪不得說我害死你呢!”
“哼,你終於明白了!”
“你……”白玉蘭嚥著說不下去了,眼淚止不住往下掉。
夫妻倆吵吵鬧鬧回到家,晚上,徐華抱著兒子小帆睡到了沙發上。白玉蘭獨自蒙在被窩裡流了半夜的眼淚。
第二天,白玉蘭來到賓館,但她並沒有立即跨進賓館大門,而是在大門外躑躅徘徊。猶豫半晌,白玉蘭昂首挺胸,毅然走進了賓館大門。
臺商名叫霍振庭,原籍就是這裡沙河鎮,他是回鄉考察投資環境的。他六十開外的年紀,身體清瘦,臉色憔悴,稀疏的頭髮貼向腦後,戴副金絲眼鏡。他把白玉蘭讓到沙發上,接著給她泡了杯茶,然後仔細地端詳起她,張了張嘴,欲言又止,顯得有些為難和煩躁,突然響亮地咳嗽幾下。
白玉蘭微笑著站起身,走到霍振庭身後,輕柔地在他背上捶著:“老先生,你好像有什麼話要說,這裡沒有外人,你儘管說就是了。”
霍振庭輕輕嘆息一聲,說:“你使我想起了一個人。 “誰?”
“我的女兒!
“你女兒?
“是啊!我女兒長得跟你簡直一個樣,而且年紀也跟你差不多可惜她不在人世了!”
“為什麼?”
“她五年前給汽車撞死了。”說罷,老人眼睛裡閃出了淚花,深深地陷入了追思中。
白玉蘭深表同情,同時她也看出了老人的心思,於是不加思索地說:“老先生,我就做你的乾女兒吧,你願不願意呀?”
霍振庭“唰”地從沙發上站立起來,精神振奮,目光炯炯,激動地說:“願意願意!說實話,你說的就是我要說的心裡話呀!這幾天你在我身邊問寒問暖,真是比我的親生女兒還要親哪!看到你,我就想起了我那死去的女兒,更引起了我要重新得到女兒的願望。現在我如願了,我終於又有一個女兒了!”老人興奮而感慨地說著,從上衣口袋裡摸出一隻精緻的小方盒,交到白玉蘭手上,“這是我給乾女兒的一點見面禮請收下吧!”
白玉蘭連忙推辭:“別,別這樣乾爹,我不能要你的東西,再說我們單位有紀律,不能利用工作關係收取人家的東西“這次是特殊嘛,多少算作我的一點心意吧!”霍振庭把小方盒開啟,取出一隻寶石戒指,抓過白玉蘭的手,硬要給她戴上。
正在這時,門突然被重重地推開了,徐華滿面怒氣地站在門口。白玉蘭吃驚地看著丈夫,一時說不出話來,不一會,她恢復了常態,對霍振庭說一聲:“我有事出去一會。”然後拉著丈夫來到了外面樓梯口,低聲說:“你怎麼來了?”
徐華嘿嘿冷笑著,沉聲說道:“想不到吧,我破壞了你們的好戲。”“徐華,你聽我說”
“少廢話!我原來還不大相信你會幹這種醜事,所以特地來這裡看個究竟,想不到你還真的不要臉!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你胡說,我還是那句話,我們之間是清清白白的!”
“算了吧,兩人拉拉扯扯,就差沒睡到一個被窩裡去,還說什麼清清白白,傻瓜才會相信你說的是真的!”
此刻,白玉蘭知道,再跟丈夫解釋也是白費口舌,索性閉上嘴一言不發。徐華叫嚷幾聲後,便無可奈何地離開了賓館。
眼淚順著白玉蘭的臉頰往下掉。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但猛聽到幾聲劇烈的咳嗽,連忙擦乾眼淚,返回霍振庭的房間。
下午,白玉蘭帶著疲乏的身體回家,推開大門,忽見地上有一張摺疊著的白色紙塊。她彎腰拾起紙塊,展開一看,玉蘭,我雖然恨你,但我們畢竟做了幾年的夫妻,因此,我應該對你說一聲。我走了,把小帆也帶走了!小帆還小,跟你在一起,你會傷害他那顆幼小的心靈的。至於我們去什麼地方,你就不必操心了。你好自為之吧!
徐華
×月×日
看到這裡,白玉蘭脆弱的心靈徹底地破碎了,兩天來的委屈和痛苦,這時終於火山般地噴發而出,捂著臉,再也忍不住地大哭了起來。丈夫拋開她不算,還要帶上兒子,這未免太殘酷了說實話,她愛兒子勝過了愛丈夫。她常年在外,難得跟兒子在一起,因此對兒子百般地疼愛,以此來彌補失卻的母愛。她不能沒有丈夫,更不能沒有兒子。如今,丈夫沒有了,兒子也沒有了,她覺得活著真是受罪呀!
白玉蘭越哭越傷心,越哭越不能自制。突然,桌子上的電話嘟嘟地響了,她竭力止住哭泣,無精打采地抓起電話。立即傳來了嚴廠長的粗大嗓門:“玉蘭同志,請你明天一早去賓館,別忘了,啊。”
“我不去!”白玉蘭回答得很乾脆。
“玉蘭同志,你聽我說,剛才我把霍老先生接到廠裡轉了轉,看了看,他表示可以考慮投資,同意明天上午在賓館簽訂合同,但必須有你在場。說實話,他之所以投資,一半是看在你的面上。你不去,這戲就唱不下去啦!”
“我說不去就不去”白玉蘭斬釘截鐵地說著,擱下了電話。她沒心思跟他多說,剛才的打擊對她太大了,此刻她想好好安靜一會。於是坐到沙發上,不知不覺便睡著了。
不知什麼時候,幾下急促的敲門聲把她驚醒,伴隨著粗獷的叫聲“玉蘭同志,開開門哪!”聽聲音,她知道是廠長,不大情願地起身把門開啟。
嚴廠長風風火火的闖進屋:“姑奶奶,你的架子真大呀,非要我親自出馬不可!
白玉蘭冷冷地說:“不敢當,我又沒有請你來。”
嚴廠長哭喪著臉說:“唉呀,我的姑奶奶!我知道你有情緒,但鬧情緒不能影響工作嘛,你畢竟還是廠裡的一員嘛!”
白玉蘭悲憤地說:“說得好聽,其實你們已經不把我當作廠裡的一員了,我像個皮球,給你們踢來踢去。你們還把我當作廠裡一員的話,就不會這樣對待我了,你們害得我像狗一樣夾著尾巴做人。要是你們還有良心的話,就不會再來麻煩我了。”
嚴廠長的臉紅一陣白一陣,說不出的尷尬,只得放下臉面低聲下氣地懇求。
看到嚴廠長這副模樣,白玉蘭滿腹的怨氣不由消退了一大半,反倒同情起了他,要想再拒絕,也沒那個勇氣了,於是她換上和藹的語氣說:“你回去吧,明天一早我就去賓館。”
第二天,白玉蘭按時來到賓館,嚴廠長以及鎮有關領導都已在座。霍振庭見她臉色蒼白,忙問她是不是不舒服。白玉蘭搖搖頭。嚴廠長連聲說:“不礙事就好!不礙事就好!”隨即宣佈就合同問題進行討論。正在熱鬧,突見白玉蘭身子一歪,倒在地下。
大家紛紛起身,霍振庭哆嗦著連聲叫著快送進醫院。嚴廠長轉過神來,忙命小何抱起白玉蘭,噔噔噔奔向停在賓館外面的小車,把白玉蘭放到車上,以最快的速度馳向縣城醫院。
多虧搶救及時,白玉蘭終於轉危為安。當她睜開眼睛時,看到霍振庭和嚴廠長都在,使她更為驚喜的是,丈夫徐華和兒子小帆竟然也在這裡。
原來,徐華昨天一時衝動,帶著兒子出走。但到了縣城汽車站,他又後悔了。如此一走,該去哪裡落腳呢?兒子又不停地叫著要媽媽,吵得他心煩意亂。無奈只得先暫住旅館,然後再作打算。剛才他去醫院旁邊的一個售貨亭買香菸,剛巧遇上了也在那裡給白玉蘭買補品的嚴廠長。從嚴廠長那裡聽說了妻子遭遇不測的訊息,頓生側隱之心,急忙帶著兒子來到了醫院。
白玉蘭張了張嘴,又閉上了,眼淚奔眶而出。醫生診斷說是精神受到壓抑,以至崩潰,從而導致身體極度虛弱。
霍振庭轉問徐華:“徐先生,你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徐華猶豫片刻,便把妻子得所謂艾滋病的事情說給霍振庭聽。霍振庭聽罷,氣得渾身發抖,氣喘吁吁:“誰這麼可惡,無辜中傷她?有天作證,她是個清白女子!徐先生你是聽誰說的?
徐華向嚴廠長瞟了一眼,霍振庭看在眼,轉向嚴廠長:“嚴先生,你這樣做,是何居心哪!”
嚴廠長慌神了,結結巴巴爭辯說:“霍老先生,你冤枉我了,我是聽徐華說。”
徐華道:呸,你胡說!我什麼時候對你說過這話的?我是吃了迷魂藥,糟踐自己老婆呀!”
嚴廠長針鋒相對地說:“那天,我想問道玉蘭投資的事跟霍先生談得怎麼樣了,我打電話去賓館,她不在,我又打電話到你家,你說她不在家,我就問你她為啥還不回廠,是不是得病了?你說她得的是艾滋病。我耳朵靈著呢,不會聽錯的。”
話音剛落,徐華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大家面面相覷,都感到莫名其妙。只聽徐華說道:“誤會天大的誤會!嚴廠長,是你聽錯了
“什麼,我聽錯了?”
“那天你打電話給玉蘭,她在裡屋跟兒子小帆玩捉迷藏,她讓我代她接電話,既然你問到她得病,看到她跟兒子的親熱樣,我就順口戲語一句得了‘愛子病’,誰知你竟誤成了艾滋病,然後在廠裡傳開,我又從大家那裡聽說。這一環扣一環的,一時怎麼解得開呀!”徐華緩緩說道。嚴廠長紅著臉,窘迫地說:“怪我酒後胡言,委屈了玉蘭。
此刻,事情已經真相大白。徐華俯身攥緊白玉蘭的手,愧疚得說不出話來。
霍振庭聽完,氣憤得咳嗽不已。他沒想到這位嚴廠長頭腦會如此簡單,遇事不加分析,反而散佈謠言。“我,我決定取消同貴廠簽訂合同!”霍振庭指著嚴廠長說道。
嚴廠長一聽,沮喪地低下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