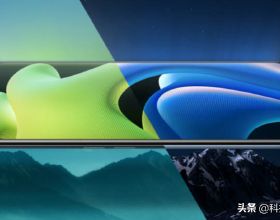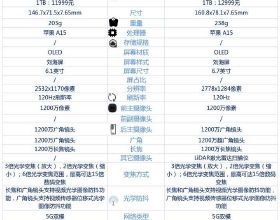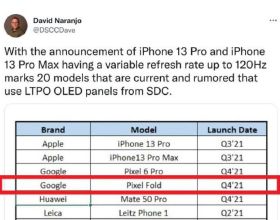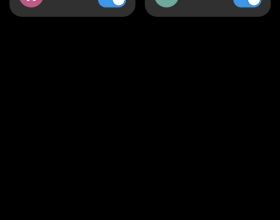那一夜月亮好圓好亮
楊屹樓
一九六七年,我在洞口茶鋪農校上學。十七、八歲的大男孩,消化功能很強,俗稱“吃長飯″。雖然我們每月有三十六斤米,每歺四兩。但過不了一兩個小時就感到餓了,三十六斤米一月雖不至於餓死,但人總是處在一種飢餓的狀態中。尤其是一到晚上,真的是餓得翻來覆去睡不著,有的同學甚至擠牙膏吃。那時向家裡要得最多的東西就是豬油,開飯的時候趁熱挑一勺拌在飯裡,好香的。六七年是文革施行的第二年,社會秩序比較亂了,下鄉知青偷雞摸狗的事也時有發生,故事就發生在這種大背景下。
一天晚上,一個和我玩得比較好的同學,走到我床面前問我想不想吃紅薯。我一翻身從床上爬起來問他:“哪裡有″。他把手從背後伸到我面前,端著個碗,原來他一直藏在背後,只是為了給我一個驚喜。碗裡大概有七八根紅薯,小的一根手指大,大的也不過一個雞蛋大,我問他哪來的,他說你莫管。紅薯還是熱的,散發著誘人的香氣。我狼吞虎嚥,片刻便一掃而光,舔舔嘴唇,餘味未盡。他問我好吃嗎?我說:當然″。他說明天我帶你去。
第二天晚上十二點多鐘,我們四個人每人提個鐵皮桶子,拿把栽鋤出發了,早把“志士不飲盜泉之水″的古訓忘得乾乾淨淨。那天晚上月亮好圓好圓、好亮好亮,她毫不吝嗇地把光芒撒向大地,地面一片銀色。一行四人,踏著月光,輕手輕腳,好像生怕把這片銀色踩碎。夜是那樣靜謐,偶爾傳來幾聲蟲鳴。
走進紅薯地,地裡隨處可見枯萎的紅薯藤,看來他們已多次“光顧″過這裡。他們三人輕車熟路,很快就找到長勢比較好的地方,開始動手了。我是第一次去,沒有他們熟悉,等我找好地方,準備動手的時候,三個同學那邊傳來一陣小小的騷動。我聽到有人輕聲說了一句:“有人來了″,他們提起桶子就跑。等我反應過來的時候,一高一矮的兩個人已到了我面前,壞了,我被逮個正著。我慢慢站起來,看到我面一老一小的兩個人,老人有七十多歲了,削瘦的臉上留著一束山羊鬍子,花白的鬍鬚上掛著幾滴露珠,看來他已在這裡守候多時了。嘴唇輕輕地顫抖著,眼睛裡流露出一種憂鬱、一種無奈、甚至有些絕望的眼神。那個小孩大約五、六歲吧,一直躲在爺爺的身後,兩隻小手緊緊地抓著爺爺的衣服,從爺爺身後探出個腦袋,露出一雙大大的、充滿驚恐的眼睛。
第一次做這種事就被逮住,我心裡也很緊張。雙腿微微有些發抖,緊張到挪不開步,呆呆地站在那裡。心裡在想,你不至於打我吧,捱罵是少不了的。雙方就這樣僵持著,時光彷彿在這刻停止了。終於,那位老人開口說話了,他說:“我知道你們學生沒吃飽,很餓。現在紅薯還沒長起,挖了可惜了,等紅薯長大了,我挑幾擔給你們吃″。聽他說完,我只覺得全身的血液直衝腦門,臉上火辣辣地發燙。想不到這位老人竟說出這樣一番話來,他不僅沒有罵我,反而這樣寬容大度,這樣厚道善良,剎那間我對這位老人充滿著感激和敬意。我有一種想哭的衝動,真的無地自容。我不敢再看那位老人,低著頭,一句話也沒說,提起桶子慢慢往學校走去。
回到宿舍,他們有的問我:打你了嗎?有的問我:罵你了嗎?我沒有回答他們,仰面倒在床上,心裡還在想著那位老人的話。過了好一陣,我猛然坐起來,大聲說了一句:“以後就是餓死我也不去了″。我不知是說給自己聽的,還是說給他們聽的,這一夜,我失眠了。
四十年,彈指一揮間。
二零零四年為紀念下鄉四十週年,茶鋪農校的同學自行組織了六十多人,租了兩臺車故地重遊。到學校舊址後,同學們自由活動,於是大家都到自己曾經勞動過的地方去看看。那時班組都有分管的地方,我們管理的那個山叫礦子山,說是“山″,不如說是“坡"更準確。我們當年種的那一排排、一行行的茶樹不見了,轉遍整個山坡,只見到處挖得稀爛,田不象田,土不象土,滿目瘡痍。我能想象得出,這是那些年學大寨的“傑作″。偶有未被完全除根的茶樹,又頑強地從土壤中鑽出來,這裡一束,那裡一蓬,依稀可以看出這裡曾是一片茶園。
時令早已過了秋茶的釆摘期,有的茶樹上稀稀落落的有些茶籽。女同學們在尋採茶籽,說是要帶回去煎茶喝,嚐嚐自己親手種的茶。我卻是哭笑不得,沒有半點興趣。我對她們說:“你們在這裡摘,我隨便走走。
憑著記憶,我找到了當年那塊紅薯地。我站在地中間,腦子裡清晰地浮現出當年的情景。天上那一輪皎潔的明月,那個留著山羊鬍子的老人;那個閃著一雙大眼睛躲在爺爺身後的小孩,似乎就站在我面前。耳邊又響起老人的話:等紅薯長大了,我挑幾擔給你們吃……
我在想,那位老人可能不在了,那個小孩現在應該是四十多歲的漢子了。他如今在哪裡?農民工?白領?我不知道。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他再也不用像他爺爺那樣守紅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