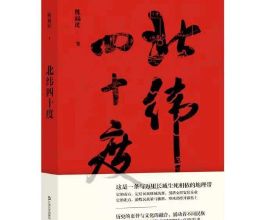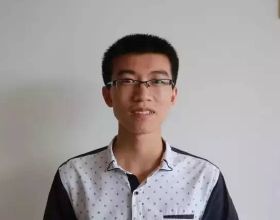當某些型別的恆星演化至生命末期,發生劇烈的高能爆炸,這種現象被稱作超新星。爆炸的光芒通常可以照亮整個星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王曉鋒將其形容為“一場宇宙的‘煙花’”。王曉鋒想象過,如果人類能夠站在宇宙的邊緣,將會看到宇宙空間中此起彼伏的“煙花”綻放,而他就是追逐“煙花”的人。
在過去的一年,利用清華大學—馬化騰巡天望遠鏡(TMTS),王曉鋒團隊在觀測到的188個LAMOST天區中發現了超過3700個週期短於7.5小時的週期性變源候選體,該發現對理解恆星(雙星)演化物理以及空間引力波源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10月2日,詳細介紹TMTS第一年巡天結果的文章線上發表於《皇家天文學會月報》。
喜事接二連三。不久前,第三屆“科學探索獎”獲獎名單公佈,王曉鋒憑藉其在超新星領域的多項開創性成果名列其中。
抓住機會闖入超新星世界
回憶起與天文學結緣,王曉鋒想起了童年的一個夏夜。“天氣炎熱時,我們家會把門板拆下來架在長條凳上,放在院子裡,我和哥哥、姐姐就睡在上面,數著頭頂的繁星,我很快就能睡著。”那時的王曉鋒雖然還不知天文學為何物,但已對宇宙有了無限想象。
高考後填報志願,他選擇了北京師範大學天文學專業。上世紀90年代,天文學仍屬小眾、冷門的基礎學科,“班上人不多,最開始有15個人,後來轉走了2個”。
剛上大學的新鮮勁兒還沒過,王曉鋒便開始擔心起畢業後能幹什麼,於是他給自己定下了讀研的目標。“那時,同學們週末會出去玩,但我很焦慮,不敢去,就只能學習。”本科畢業時,班上有兩人被保研,王曉鋒是其中之一。
但讀了研,困難才剛剛開始。那時,北京師範大學尚無天文觀測裝置,“天文學研究依靠觀測驅動,需要一手資料”。在此之前,王曉鋒的師兄師姐會被導師推薦至擁有觀測裝置的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當時為北京天文臺)進行聯合培養。但王曉鋒卻被導師留在了身邊,焦慮再次籠罩了他。“當時真有點著急,就想老師為什麼不送我去?”他說。
接觸不到一手資料,王曉鋒只能自己摸索,“當時導師給了我幾篇預印本的文章,我就自己邊看邊琢磨”。王曉鋒試著將文獻中的資料摘取出來,進行二次分析。“我只能用別人的資料做一些復現的工作,但連著幾次投稿國際頂級期刊均被拒絕,反饋意見都是缺少一手資料,沒有創新發現。”王曉鋒對未來的學術道路感到迷茫。
就在博士即將畢業時,一個偶然的機會,王曉鋒得知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施密特望遠鏡團組招收博士後。“當時,我就想著一定要去。去了之後,我發現他們有一些近十年的超新星爆發前資料,這讓我特別驚喜。”他說。
終於有機會獲取一手觀測資料,王曉鋒的潛力被徹底激發出來。憑著學術積累和數次嘗試,他提出了Ⅰa超新星光度校準的溫度方法,引起國際同行的極大關注。而後,接連兩篇重磅文章發表於《天體物理學雜誌快報》。“這在天文學領域差不多是僅次於《自然》《科學》的期刊。我感覺自己的人生一下子‘開掛’了。”他回憶道。
王曉鋒覺得,自己終於真正邁進了科研領域,他也明白了讀博時導師對自己說過的話: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導師負責把你領進門,修行好壞主要在個人。
用研究成果“裁斷”學界爭論
2004年底,王曉鋒博士後出站,來到剛剛成立的清華大學天體物理中心。他利用一臺80釐米天文望遠鏡開展超新星搜尋和後續觀測研究,並在2005年末成功發現了3顆新爆發的超新星,開創了國內高校天文發現的先河。但他並未就此止步,他想去更大的平臺磨鍊自己。
2006年夏,王曉鋒進入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博士後工作,那裡是國際超新星觀測研究的中心。在那裡,王曉鋒做出了他在超新星領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此前,根據不同的觀測結果,國際天文界認為Ⅰa型超新星的形成存在兩種理論模型。他們認為一顆普通的白矮星無法引發超新星爆發,需要吸積周邊的伴星物質或與另一顆白矮星併合,才能達到爆炸極限。相對應,這兩種不同的模型分別被稱為單簡併模型和雙簡併模型。此外,還有觀點認為,不同的Ⅰa超新星可能源於同一個爆發模型,觀測差異是由於觀測角度的不一致造成的。此爭論在學界相持不下,誰也無法說服誰,而王曉鋒則用研究結果回答了這個問題。
2008年,王曉鋒團隊在研究爆發於近鄰M100星系中的一顆Ⅰa型超新星SN2006X時,發現其爆炸拋射物向外擴充套件的速度約為16000千米/秒(光極大時),而普通的Ⅰa型超新星則僅為10000千米/秒。王曉鋒針對這一差異,立即對大量Ⅰa型超新星的光譜資料進行了系統研究分析。他將Ⅰa型超新星進一步分類為高速與低速兩種型別,並以此分類為基礎,結合超新星爆發時其所處寄主星系的位置以及爆炸前所在星族位置等資訊,進行統計研究。王曉鋒最終發現,高速Ⅰa型超新星與低速Ⅰa型超新星具有不同的本徵亮度,它們也存在著完全不同的誕生環境。而後他進一步研究發現高速Ⅰa型超新星的前身星具有較高的金屬含量、較豐富的星周物質以及較明顯的爆炸非對稱結構;而低速Ⅰa型超新星則沒有這些特性。
這一結果從觀測上完美呼應了兩種理論模型,高速Ⅰa型超新星可能來源於單簡併演化,而低速Ⅰa型超新星則主要來源於雙簡併演化。這一成果使得尋找性質更均勻的Ⅰa型超新星亞類成為可能,對於超新星宇宙學應用有重要意義。
相關成果發表後,在國際天文界引發熱烈反響。美國天文學會前主席克雷格·惠勒(Craig Wheeler)在文章發表兩天後發來郵件說:這是個了不起的成果!
期待目睹完整的超新星爆發過程
王曉鋒至今記得,當他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看到其數十年積累的巡天資料時的那種震撼。“差距確實很大,我們的光學天文基礎相比要弱很多。”王曉鋒希望儘自己所能推動國內該領域的研究,“我覺得自己有一些責任在裡面”。以清華大學為中心,他組織起了跨單位、跨地域的國內時域天文學組會,希望帶動更多的年輕人投入到超新星和時域天文學研究當中。
王曉鋒培養的學生範圍很寬,從高中生一直到博士生,針對不同的學生他有不同的教育方法。“高中生不要求有什麼重要的科研成果,我主要是引導他們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培養基本的科研思維。”而對於研究生,王曉鋒則因材施教,“有想法的學生就給他們空間讓他們自己去做,暫時沒什麼好想法的就多帶一下。”雖然年輕時對當老師不感興趣,但如今的王曉鋒顯然在人才培養上頗有心得。
展望未來,王曉鋒認為,要做出世界級的科研成果,我國還需要發展通用大口徑光學紅外望遠鏡,“至少要媲美歐美十米級的光學紅外精測望遠鏡”。而接下來他最期待的,莫過於預計將在2024年發射的中國空間站工程巡天望遠鏡(CSST)。以此為基礎,王曉鋒將目標瞄準了哈勃常數的精確測量。
“美國能測量哈勃常數,是因為他們有哈勃空間望遠鏡,以此能分辨出河外星系的單個天體。”他說,有了CSST,我國也將具備此種能力。“CSST的視場比哈勃空間望遠鏡要大300倍,這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精確哈勃常數,以澄清當前的宇宙學危機問題。”
王曉鋒認為,任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離不開綜合國力和社會力量的提升。而他作為一線科研人員,受惠於此,感受頗深。“我們這代人趕上了好時候,國家層面和社會企業都給予我們很多幫助,這激勵我們做出更多出色的成果。”他說。
王曉鋒要感謝的,還有浩瀚宇宙。“每當因為一些瑣事煩惱時,我就會抬頭看看星空,和這億萬年的宇宙相比,我們人類的那些事又算什麼呢?”他說。
王曉鋒還有個願望,他希望能用肉眼目睹一次完整的超新星爆發。“上一次記載人類觀看到超新星還是在1604年,下一次是什麼時候,誰也不知道。”王曉鋒有足夠的耐心等待,他知道,在宇宙深處,總有“煙花”在悄悄綻放。
文/科技日報實習記者 都芃
編輯/範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