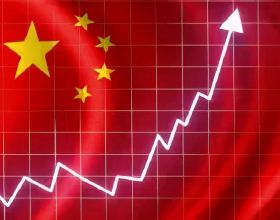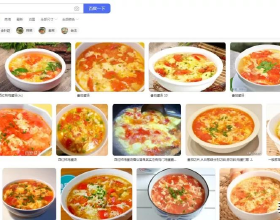金克木先生 (由黃德海供圖)
對於黃德海“長篇非虛構”新作《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以下簡稱《編年錄》)的閱讀期盼,首先當然是因為作品主人公金克木老先生那傳奇般的學術生涯;其次則是德海在這作品後面還附了一則題為“嘗試成為非虛構成長小說”的“後記”式文字,又是“非虛構”、又是“小說”,還竟然要將這兩個基本要素相逆的文體糅在一起,這不得不令我充滿了好奇,急於要看看德海究竟是如何“嘗試”的。
《編年錄》上篇“學習時代”,嚴格逐年完整地記錄了金老35歲前的“求學”生涯。我之所以要為“求學”二字打上引號,是因為這段時光中不僅穿插著金老間或的一些工作經歷,且整個“求學”生涯也完全不同於我們習見中的那種連續性、規範性與系統性,而是呈現出時間上的碎片化和內容上的雖非系統性但又極為廣博兩大鮮明特徵。概括1930年金老到北平求學前那19年所受的教育狀況,無論是啟蒙階段還是中小學時期,拼接起老人家那些零碎的自述,便不難看出這一點。所謂正規的學校教育既斷斷續續也不完整,但個人的閱讀卻從未中斷,且面也是越來越寬、越來越雜,從文言到白話、從國學到西學、從人文學科到自然科學,包括一些左翼進步書報刊以及英語、世界語……都是在這個時期走進了金老的視野與腦海。1930年剛滿19歲的金先生到北平求學,儘管三哥相送時囑其“一定要想法子上大學”,但又囿於經濟窘迫,“大學的門進不去,卻不妨礙上另一類大學”:讀報、入頭髮衚衕的市立公共圖書館、入“私人教授英文”處、入“私人教授世界語”處、入中山圖書堂、松坡圖書館、中國政治協會圖書館、逛舊書店和書攤;至民國大學,聽教育學、國文、公共英文和專業英文,復聽生理心理學、德文、法文課;至中國大學,聽俄文、英國文學史、英文課;至北京師範大學,聽外國人教英文課,窗外聽錢玄同、黎錦熙課;旁聽熊佛西戲劇理論課;再讀屠格涅夫;寫小說;泡北大圖書館;搞翻譯;組讀書會讀馬列原著;聽章太炎、胡適、魯迅演講……1933年帶著在山東德縣師範掙到手的一點微薄薪水再回北平,在北大做起課堂上的無票乘客,聽德文、日文、法文課,迷上天文學;結識徐遲、沙鷗、吳宓、朱錫候等;1935年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員,業餘從事創作與翻譯;結識鄧廣銘,成為學術指路人……包括1941年金老經緬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報紙編輯同時學習印地語和梵語,後又到印度佛教聖地鹿野苑鑽研佛學直至1946年到武大任教前大抵都是這種狀態。
從上述不厭其煩地按時序排列,我們的確不難看出:其一,說金老屬“自學成才”大抵不謬;其二,自學者眾,成才者寡,但金老的閱讀力、記憶力、領悟力、耐受力以及實踐力確非一般人所能抵達;其三,雖無緣接受正規系統的教育,但金老的學習卻因此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與選擇度,於是我們看到他學習的領域格外寬,閱讀的學科特別多,這亦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在《編年錄》中,德海的用語極簡約,但偶爾也會出現或摘錄一點帶有某種畫面感的場景,這很有趣,不妨信手舉例一二。
場景一:金老還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時,“有一天,一個借書人忽然隔著櫃檯對我輕輕說‘你是金克木吧?你會寫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歡你寫的文’”。這個輕輕說話者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有20世紀中國宋史研究主要開創者和奠基者之譽的鄧廣銘先生,當時他正在胡適先生指導下完成自己的畢業論文《陳亮傳》。即使他當時只是北大歷史系四年級的學生,也未必要主動向這位並無學歷的圖書館管理員示好,而且還將自己的畢業論文給他看;後來,更是主動約請當時還基本是默默無名的金克木為《益世報·讀書週刊》撰寫並發表了與當時早已是名聲顯赫的周作人辯論的萬字長文《為載道辯》,而正是此文成了金老“發表大文章的‘開筆’”。
場景二:在1947年前後武漢大學校園中的珞珈山下,時常有四位中年人一邊散著步,一邊“談得不著邊際,縱橫躍跳,忽而舊學,忽而新詩,又是古文,又是外文……雅俗合參,古今並重,中外通行”。這便是當年在武大被稱為“珞珈四友”的周煦良、唐長孺、金克木和程千帆共同呈現出的一景兒。
其實還有,比如發表自己的作品並不需要啥名流的引薦,比如一封信件就可能結識某位名流並與之交流,比如可以免費看到或旁聽到許多書刊及名家的講學……看著金老年輕時的這些經歷,我也明白了自己當年何以一封普通的信函約稿就很快得到了先生的回覆及大作,同樣還是一封普通的信函就能得以拜見金老。
這樣的人際關係與這樣的場景的確令人感到溫馨與神往。如果金老沒有遇到這樣的人與這樣的環境,即使他有過人的天賦與才能,自學雖無妨,成才則未必。胡適當年在為金老證婚時就說過:當時“北大有一特別制度,就是允許青年偷聽。金先生當時不僅聽一門,而且聽很多門。他已成為今天很好的語文學者了。”
最後要說一說這部作品的寫作。作品的主題叫“讀書·讀人·讀物”,這應該概括的是作品的主體內容,即將金老畢生的主要經歷概括為這“三讀”;副題叫“金克木編年錄”,這應該是指作品具體的寫作方法,即如德海自己說明的那樣,全書“以金克木回憶文字為主,間以他人涉及之文,時雜考證”。這樣的作品稱其為“長篇非虛構”自然無妨,換句話也可以稱其為是一部金老生平年表的文字版。可以想象,為完成這部作品,德海下了多少硬功夫、死功夫,耗去了多少心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後所附的那則近乎“創作談”的文字中所提到的“金克木的自學幾乎成了傳奇,可他自學的方法是什麼?金克木曾有近三十年中斷了學術工作,晚年奇思妙想層出不窮的原因何在?”類似這樣的問題在德海的這部作品中都是可以悟到一些答案的。我這裡說的是“悟到”而非“找到”,即答案是需要讀者的參與思考而形成,而並非現成地出現在作品中,而這也恰是德海本作品的重要價值之所在。
還是在這則近乎“創作談”的文字中,德海留下了一句令讀者要費點思量的話:“希望這個編年錄有機會成為並非虛構的成長小說”。“希望有機會成為”指的似乎是未來而非現在這部《編年錄》,“並非虛構的成長小說”則是將“非虛構”作為未來那部“小說”的特徵與限定,這很令人好奇。倘如此,那可真就顛覆了小說這一文體最基本的特性——虛構。這當然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但德海這部《編年錄》在寫作上的確是比較嚴格的編年錄筆法,惜字如金,無一字無來處。而我在閱讀這部作品時的狀態則的確比較“分裂”:一方面是嚴格按照時序跟隨著作品前行,另一方面作品的某一句或數個句子又的確會立即在腦海裡出現一幅畫面、一個場景甚至一段情節。前一種狀態是在讀史,後一種狀態則是在讀小說。我相信,後一種狀態在其他讀者那也會存在,只不過是他們想象中出現的畫面、場景與情節與我的未必完全一樣。那麼是否可以說,讀史是被德海牽著在走,讀小說則是讀者和德海一起的“共謀”或“同構”?倘的確如此,德海期待的那種“並非虛構的成長小說”就已然是一種無形的存在了。
(作者為知名文藝評論家)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