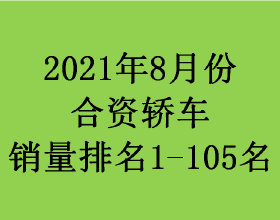地震以後,先是在臨街的地方和鄰居們暫住一個臨建,說是臨建,其實就是一個簡易的帳篷——有棚頂、而四面用竹竿撐著沒有遮擋,從這個帳篷可以望見那個帳篷,白天,大人們偶爾回去拿點必需品,夜晚大家齊刷刷的都睡在大街上。
孩子們最容易忘記恐懼,很快前衚衕後衚衕,前院後院,前街后街的小夥伴變熟絡起來,大家玩在一起好不熱鬧。
再後來,又從附近公園住的臨建,搬進了母親單位統一給大家分配的臨建。
在那裡度過了一段、從童年即將跨入少年的難忘時光。
那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大衚衕套著小衚衕、似乎從東西南北都能走出去、走到大街上,比我們原來所住的衚衕要長很多,寬很多,大很多,猶如電影地道戰迷宮般的衚衕。
單位裡的孩子們很快熱絡起來,夜晚在大孩子的帶領下一起玩捉迷藏、演電影和打仗的遊戲,無憂無慮的童年快樂,沖淡了眼前的艱苦生活:一下雨,臨建就會進水,家人一起往外掏水,夏天太陽一曬,臨建棚頂所散發的熱量,炙烤得人們輾轉難耐,持續的潮溼悶熱,使得人們夜晚不到12點以後,是不願意進屋睡覺的,大家聚在一起講類似於聊齋的鬼故事,倒也不覺得艱苦……嚴重的支氣管炎也就是那時候患上的,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精神上的歡樂足以沖淡物質生活上的窘迫。
彷彿這條長長鬍同的十字路口,單位臨建左側衚衕馬路對面,是一個大雜院,院門不寬,然而裡面人家卻不少,其中就住著我們的主人公“傻二”和她的媽媽,還有一個獨居的被打成右派分子、掃大街的“老頭”。
“傻二”大概得的是唐氏綜合徵,長著一張“國際臉”,看身體發育大概也有十七八的樣子,她的媽媽,面板較黑,瘦高畫質秀,像是三十幾歲、四十歲的模樣,如果按現在的標準,稍加打扮,就是一個俊俏的媳婦。然而在動盪的時代,傻二媽卻有著一張與年齡不相稱的、飽經滄桑的面容。
那時,經常會有群眾參加的批鬥大會,不知傻二媽媽犯了什麼錯(也有人傳說,她和那個掃大街的老頭“搞破鞋”),經常被無緣無故的牽出來遊街示眾,後面也一定會跟著弓著腰、馱著背、低著頭的那個掃地的老頭兒(平時,“老頭”是不駝背的)。只見傻二媽脖子上掛著一雙鞋,嘴裡還唸唸有詞(人們讓她說什麼她必須說什麼)。
於是,有樣學樣,當半大孩子們玩膩了,就會跑到院子裡,把傻二媽牽出來當街示眾,那個女人本就比較黑,這樣一折騰,汗順著臉頰流下來,臉上又添了幾縷黑道子,再加上亂糟糟的頭髮,顯得髒兮兮的。她眼神空洞,任由跟在周圍的孩子們起鬨取樂。
直到不久之後粉碎了四人幫,在沒看見傻二媽脖子上掛著一雙鞋,被人們牽出來遊街的情景。
粉碎四人幫人們在扭秧歌
很快,“抗震樓”建好,臨建裡的孩子們紛紛跟隨家人搬進新的居所,更沒了傻二和她母親的訊息。
想來,這個世界上大概有幾種人是不會自殺的:一種,是玩轉“厚黑學”的潑皮無賴。一種,就像和傻二媽住在同一個院子裡,被打成右派而被迫掃大街的“老頭”——他的學問和信仰是支撐他活下去的勇氣。還有一種,就像被侮辱被損害的傻二媽,在這個世界上有割捨不了的牽掛……
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和現實世界中,都有對使用私刑的描繪和反映(因為愚昧無知或人性之中惡的因子被激發放大,採用非法手段懲治“罪人”的行為),在彼時彼地,也鮮有人質疑這樣做的合法性,或根本無力反抗。
傻二的“破鞋”媽媽和被打成右派、掃大街的老頭,不就是經歷了這樣的遭遇嗎?
時代在前進,人們的思想意識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今天的人們,不可逃避的需要面對網路虛擬世界,那樣的歷史故事,不應該也不允許在網路及現實世界再次上演。
一直以為,盲目的“善良”不可取,擁有更多資訊渠道,逐漸學會獨立思考……好比一個人產生善因的種子,會促使越來越多的世人,喜歡花好月圓的故事不斷上演。人心向善,越來越好。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