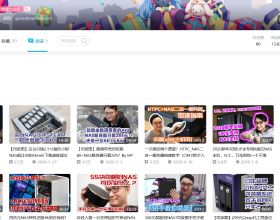1
立秋剛過,眼見圈裡的母豬癱臥在水泥地上,呼呼直喘粗氣,光著小麥色臂膀的春祥,抹了一把汗,捏住明黃色膠皮管子,開始往圈裡滋涼水。水花在空中飛舞,碰上刺目陽光,撞出五彩的虹;水柱砸在地面上,混著刺鼻臭氣,送來了些許清涼。灰白色地塊,被衝成了乾淨的青灰色。
春祥一個圈一個圈地滋,把十幾個豬圈滋完時,已是下午兩點多。不過,春祥並不覺得累,被水汽浸潤許久,他反倒有些神清氣爽了。
春祥曾在廣州打過八年工,終於熬成電子廠備受車間主任器重的熟練工,安裝一個零件僅需兩秒鐘。但是,他受夠了把一年過成兩秒鐘的乏味生活,去年春天,揣著平時吃饅頭就鹹菜省下的十幾萬塊錢,賭氣辭了職,自那座溫暖宜人的南方大城市,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北方小村莊。他試著先在自家院裡養了幾頭豬,一年下來,竟賺了一萬多。今年一開春,春祥就擴大規模,在場院上蓋起了養豬場。他算了一下,待這些豬出欄,他能淨賺七八萬,比打工可強太多了。
春祥記得,小時候,場院還是平坦開闊的空地,一戶一塊,連成一片,一眼能望老遠。那時,為了趕在落雨前把糧食歸倉,村裡人搶收麥子像打仗,場院則是主戰場。他們用架子車,把麥子從地裡拉到場院中均勻鋪開,牽著老黃牛,在毒日頭底下,拉著石磙在上面一圈圈地碾,使麥粒分離出來。麥粒被攤在場院上晾曬的同時,他們會拿出木叉,把麥秸稈叉到場院邊,堆成一座座金黃色的小山。待傍晚來臨,南風起,大人們再拿著木鍁,一鍁一鍁地把麥粒往天上揚,分量輕的麥糠隨風飄向遠處,而分量較重的麥粒則直直地砸在地上。
而今,農村機械化水平越來越高,聯合收割機可以前頭收割,後頭直接出幾無雜質的麥粒,大家只需把麥粒就勢在田裡晾曬乾燥,即可歸倉,或者直接拉到收購站去賣掉,場院便逐漸失去了它本來的作用。
面對閒置下來的場院,村裡人有的在上面開荒種菜,有的在上面種糧食,有的在上面種果樹,春祥則直接在上面蓋起了養豬場。春祥家的場院在最西邊,場院西邊長著一大片白楊林,風一吹,嘩啦嘩啦響。他家在白楊林邊上,距離場院不到一百米,這使得他在養豬場和家之間穿梭起來,很是方便。
春祥套上汗衫,扇著蒲扇,搬出馬紮,坐到樹下乘涼。日頭已然西斜,但它還在不依不饒地釋放著光和熱。楊樹的葉子卷卷的,頭頂的蟬聲懶懶的,地上的雜草蔫蔫的,一切都像是沒睡醒的樣子。
春祥發現地上有個小眼兒,用手輕輕一挑,小眼兒就變成了大洞。春祥把食指伸進洞中,果然觸碰到了滑滑的知了猴脊背。春祥小時候喜歡和小桃一起,白天到處踅摸這種小眼兒摳,晚上他們則打著手燈,跑到林子裡照,把捉來的知了猴過油炸一下,那滋味,春祥而今再想起,也還是會忍不住流口水。莫名地,他就想起了小桃,想起了那個悶頭苦讀十幾年,後來考上大學,他再也沒見過的小桃。
春祥正盯著洞裡的知了猴出神,突然聽到身後有腳步聲。回頭一瞧,一條叼著紅色水瓢的純黑狼狗映入眼簾,黑狗前方走著的,是肩頭墊著一塊毛巾,毛巾上壓著一根扁擔,扁擔兩頭各吊著半桶水的五嬸。
春祥跟五嬸打招呼,問她幹啥去。
“去澆菜!”五嬸回頭看了春祥一眼,腳步卻沒停。
若非看到五嬸,春祥還注意不到她的菜園,可是看了一眼,目光就再也挪不開了。紅的辣椒、黃的南瓜、紫的茄子、綠的黃瓜……五顏六色、琳琅滿目,一切都被五嬸打理得井井有條。
五嬸放下水桶,從黑狗嘴裡接過水瓢,把黑狗趕到一旁的樹蔭下臥著,彎下腰,一瓢一瓢地舀水澆菜。黃瓜在涼水的澆灌下,葉子支稜了起來;五嬸呢,已是溼透了汗衫。
看著五嬸忙碌的背影,春祥心裡有些泛酸。五嬸是多好的一個人啊,可是,而今,她都年過六十了,還在沒日沒夜地操勞!春祥到現在還記得,以前日子過得艱難,夏天想吃水果,只能拿糧食換。多數人家吃水果,都會先把閒雜人等支走,而後鎖上大門,圍在桌前,做賊似的分食。可五嬸不同,他們家吃水果從不避著春祥,每每春祥去找小桃玩,五嬸總會變戲法般地或抱上來一個西瓜,或拿出來兩枚蘋果分給他和小桃吃。
這樣子澆地,得澆到啥時候去?春祥看不下去,快步跑到五嬸的菜地,奪過了五嬸的瓢。
春祥告訴五嬸,這樣澆地太慢了,他可以把膠皮管子扯到菜地裡幫她澆。五嬸抬眼看了眼春祥,釋放了一個苦澀的笑,嘟囔了句:“也好!”聲音弱得像蚊子叫。春祥知道五嬸是覺得麻煩了他,有些難為情,所以故意大聲說道:“您這菜園子不大,我用皮管子澆,十幾分鐘的事兒,權當玩兒了!”
春祥麻利地扯過皮管子,開啟抽水電機,一邊滋水一邊同五嬸講:“天氣熱,這菜園子得常澆水,以後我每隔一兩天就給您澆上一水,這樣子就不怕旱了。”
正幫著捋管子的五嬸說:“這樣確實快,就是別耽誤了你幹正事才好。”
“這不費啥工夫!”
“那我這園子裡的菜,以後你隨便吃!”
春祥嘿嘿一笑,嘴裡連說著中。
春祥聽母親講,小桃大學畢業不久,五叔就得了急病,撇下她娘倆去了。小桃在寫字樓裡上班,看著光鮮,工資並不高,而且還要租房子吃飯,哪裡還餘得下多少錢?五嬸不要小桃的錢,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日常吃菜,都從這菜園子裡出,吃不完的,她還會挑到集市上去賣,掙點買鹽買油的錢。春祥幫五嬸澆菜,本就出於自願,再加上這片菜園對五嬸而言如此重要,他怎麼捨得隨便吃?他之前的假意答應,也不過是為寬五嬸的心罷了。
誰知,許是五嬸看穿了春祥的心思,當天晚上,春祥家就多出了許多的黃瓜、南瓜、豆角、西紅柿……
春祥覺得自己只是捎帶手幫忙澆了點水,卻拿了人家這麼多菜,像是佔了便宜。
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到了半夜,他覺得水還是得幫著澆,但是明天他要去五嬸家一趟,把這事說明白。
2
翌日,春祥喂完豬,就往五嬸家去。
而今,村裡的許多人家都蓋起了二層小樓,差一些的也蓋了平房,唯有五嬸家還和春祥小時候見過的一樣,是灰撲撲的磚瓦房。
春祥剛推了一下門,院內的黑狗就開始汪汪汪地叫個不停。五嬸聞聲出屋,一眼看到從門縫中露出半個腦袋的春祥,喝道:“東來,快別叫!”東來就立時住了聲。原來,這黑狗名叫東來。
春祥進院,滿眼看到的又是一片綠色,中間只留了一條小道直通堂屋。原來,五嬸在院裡也種了菜。只是,因被楊樹和大泡桐擋住了光,這些菜長得並不如場院上的健壯。
東來繞著春祥跳來跳去,很是熱情。春祥問五嬸,這狗為啥叫東來?五嬸告訴他,東來是打村東邊流浪過來的,所以給它取了這個名。那時候,它髒兮兮臭烘烘的,身子還弱,所有人都嫌棄它,沒想到,養了幾年,竟越發壯實了。五嬸還說,東來聽話,對熟人也熱情,是看家護院的好手。
春祥隨五嬸進堂屋,坐在小凳上,東來便也跟過來,在春祥身旁東轉轉、西晃晃,吸溜著鼻子在他腳邊聞來聞去。
電視機里正播放縣電視臺插播的農藥廣告,很是聒噪。五嬸過去啪嗒一聲關了電視,屋裡登時安靜了。春祥記得,以前他最喜歡的事兒就是下午放學,和小桃一起坐在這電視機前,看縣電視臺轉播的《大風車》。那時候,五叔外出打工,能掙錢,小桃家條件好,這電視機是村裡的稀罕物。可是,這麼多年過去,家家戶戶都換上了大彩電,這臺黑白電視機竟然還沒壞。
春祥問五嬸怎麼不換臺彩電。
“小桃之前也嚷著要換,我沒讓。我不大看電視,屋裡有個聲就行,不換了!”五嬸一邊回答,一邊把一杯放了茶葉末的開水端到了春祥面前的桌上。
自外出打工後,春祥已有多年沒來過五嬸家了。他環視一圈,發現五嬸家,除了四方桌的漆掉得更多了一些,明黃色的摺疊沙發變成了暗黃之外,和他記憶中的樣子並無太大分別。他看到這些,又忍不住想起小桃來。
春祥上小學的時候,頭腦靈光,回回考第一,所有老師都覺得他會成為村裡第一個大學生。但到了初中,他的成績就不行了。不是他的腦子不再靈光,而是聰明沒用到正地方。他和班裡的“混子”攪和到了一起,整日變著花樣地出風頭、與老師作對。小桃呢,則開始刻意疏遠所有人,整日悶著頭讀書,當了同學們眼中的“書呆子”。春祥不想當“書呆子”,甚至還一度有些瞧不起當了“書呆子”的小桃。在春祥看來,若想掙大錢,必得會混會闖,成績好有什麼用?
春祥初中沒上完,就毅然退學,像一隻迫不及待展翅的雛鷹,懷著滿腔憧憬,跟著老鄉去城市打工混社會。小桃則考上了縣裡的重點高中,從此與春祥分道揚鑣。
只是,春祥這隻鷹剛進大城市,還沒來得及飛山越海,就不得不被生活剪掉翅膀……春祥猛然發覺,對於農村孩子來說,像小桃那樣好好讀書,考上大學,似乎才是唯一正確,真正有前途的出路。他開始羨慕小桃,痛恨自己以前的所作所為,甚至幻想,如果當時他也努力學習,和小桃一樣考上大學,現在是不是已經和小桃走到一起了?可時光難再回,一切似乎都已來不及,他現在能做的,也只是亡羊補牢,盡最大努力把豬養好,多掙些錢,說上一門親,娶個像小桃那樣美麗的農村姑娘。
春祥問五嬸小桃的近況,五嬸卻嘆了口氣,去裡屋拿出了一張婚紗照。
婚紗照中的小桃綻出空姐般標緻的笑容,嘴角微微上揚。而摟著她肩膀的男人,齙牙也就罷了,更重要的是,頭髮已經不剩幾根,雖然化了妝,但也能明顯看出,他比小桃老上十幾歲。
春祥捧著照片仔仔細細地看了好大一會兒,在心裡默默得出一個結論:小桃一定是不樂意的。對,一定是的,不然,以小桃的眼光,怎麼可能看上這樣一個人?
五嬸告訴春祥,小桃本來不打算這麼早結婚,想著等過個三五年,工作穩定了再結,但幾個月前,突然查出來懷了孕,捨不得打掉,不結也不行了。這婚結得急,就只領個證,在北京簡單擺了幾桌酒。
春祥問五嬸這男的多大歲數、做什麼工作,五嬸說別看他模樣顯老,但是隻比小桃大三歲,碩士,好像是畫圖紙的,挺忙,不過,收入還可以。
春祥心裡酸溜溜的,“哦”了一聲,就打算邁步出去,此行的目的早已被他拋諸腦後。直到快出院門了才猛然想起,道:“五嬸,以後您不用再送菜了,我家離您的菜園子近,隨吃隨摘,這樣吃的新鮮,也省得浪費。”
五嬸送出門來,說道:“知道了,可你得想著去摘呀!”
春祥悶聲“嗯”了一聲,便快步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3
秋日將盡的時候,圈裡多了十五隻小豬仔,這可把春祥樂壞了。這十五隻小豬仔若是都能活,春祥能大賺一筆。可是,不到三天,十五隻小豬仔就被母豬壓死了三隻,而且,母豬奶水不足,春祥不得不拿著奶瓶,蹲到豬圈裡抱著小豬仔喂。
五嬸在養豬場外喊“祥兒,祥兒!”的時候,春祥正抱著一隻黑白花小豬仔餵奶。小豬仔吮吸得急,白色奶水不時從它嘴角溢位,滴到春祥軍綠色的褲子上,洇出一朵朵雪白的花。
春祥聽出是五嬸,忙把奶嘴從小豬仔口中拔出,起身扒著豬圈門往外跳。
“五嬸,咋不進來?”春祥來到養豬場外,看五嬸一手護著懷裡抱著的一兜雞蛋,一手牽著無精打采的東來。
“人身上細菌多,還是不進去了。”五嬸道。
春祥問五嬸是不是有什麼事,五嬸道:“小桃快生了,說要讓我去北京,一來去享享清福,二來也幫幫她的忙。可是,我這家裡一大攤子,怎麼撂得開手?其他的還好說,就是東來,我交給誰都不放心。”
春祥聽懂了五嬸的意思,便直接說:“五嬸,要是您信得過,就把東來暫時交給我養!”
“那會不會太麻煩你?”
“怎麼會?這裡正缺個東來這樣看家護院的好狗,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這是自家雞下的蛋,我也吃不上了,你留著吃!”五嬸把那兜雞蛋往春祥懷裡塞。春祥一個勁地往外推。
“接著!”五嬸話音不高,但其中似乎包裹了不容拒絕的重量。春祥嚇了一跳,只得不情不願地接下。
而後,五嬸把繩頭交到春祥手中,並扭頭正色對東來講:“你以後跟著祥兒,好好看家,得聽話!”
東來仰著脖子,舔了舔五嬸枯樹皮般的手,也不知有沒有聽懂。
一陣狂風吹來,那片白楊林排山倒海般,嘩啦啦搖了起來,枯樹枝噼裡啪啦地砸下,黃樹葉打著旋兒地飄落。
二人直愣愣地對著白楊林看了一會兒,直到風住,春祥才開口對五嬸講:“北京比老家冷,您多帶點衣服吧!”
五嬸“嗯”了一聲,又順著東來的毛呼嚕了幾下,轉身離去。東來對著五嬸的背影汪汪汪地叫,腳下也沒閒著,在黃土路上使勁地蹬,想要掙開春祥手中的繩索,去追五嬸。
聽到東來的瘋狂號叫,五嬸強忍著沒有回頭。東來還是五叔在時養的,五叔離世後,它已經成了五嬸的孩子,陪五嬸熬過了無數個荒蕪的夜,說沒感情是假的。
為防東來再鬧,春祥把它拴了起來,想著等它真正接受了他這個新主人,再放了它。
東來剛來那幾天,沒日沒夜地嚎。春祥也不惱,只是好吃好喝地供著。狗嘛,認舊主,換了新主人,總得給它幾天的時間適應不是。
可是,幾天過去,東來不再嚎,卻整日無精打采地趴著,連飯也吃得少了。
看著東來一天天瘦下去,春祥覺得這也不是辦法,便在一個清晨,給東來解開了繩索。擺脫了束縛的東來,立時像脫韁的野馬般,直衝出門,朝五嬸家飛奔而去。
東來扒著早已掛上鐵將軍的大門朝裡看,追上來的春祥,也扒著門縫往裡瞅。黃瓜架還沒拆,但失去了黃瓜秧纏繞的黃瓜架,就是一堆糠了心的爛木頭,了無生機。
東來不再往裡看,身子一歪,臥在了門口。春祥用腳輕輕踢了踢東來的屁股,示意它趕快起來,跟著他回去。可東來倔得很,任春祥怎樣踢、怎樣呵斥,都一動不動。養豬場裡還有一堆活兒,春祥沒工夫和它耗,只得由它去。
不過,東來不傻。它平時趴在五嬸家門口等,可一到飯點,或者天黑下來了,聽到春祥一喊,它就立馬起身,顛顛地朝養豬場跑。
今年冬天,是個暖冬。都立冬了,天氣還不大冷,雪更是一場沒下。村裡有經驗的老人都說,暖冬不好,地裡的小麥乾旱,人也易生病。
老人們說得有理,不過,於春祥而言,暖冬帶來的是更嚴重的滅頂之災。剛入冬,豬就開始接二連三地生病,春祥把獸醫請來,可一針管子一針管子的藥打下去,總不見好。獸醫提醒春祥萬一是豬瘟,就麻煩了,勸他趁著豬還沒死,趕快拉到集市上賣掉。但春祥不願意,一來得了病的豬隻能便宜處理,血虧;二來,把病豬賣給人吃,他心裡過意不去。
春祥抱有一絲僥倖心理,覺得自己不會那麼倒黴,便又買了好幾箱藥劑,挨個給那幾頭病豬打。
兩天後的一個早晨,春祥起床照例去豬圈巡查,卻發現一頭即將出欄的公豬,正直挺挺地躺在春祥為它鋪的麥秸稈上,一動不動。春祥過去一摸,公豬早斷了氣,連身子都涼了。
春祥飯也沒顧上吃,就把死豬拉到了白楊林裡挖了個深坑埋了,並暗暗祈禱。
可誰知,不到一個星期,春祥的豬圈就空了。
把最後一頭豬拉到樹林裡埋下之後,春祥撂了鐵鍁,四仰八叉地躺在冷風中,號啕大哭。這一下,他不僅十幾萬元血汗錢打了水漂,而且還欠下了幾萬元的外債。
4
春祥高燒不退,連著打了一個星期吊針。打吊針的時候,母親坐在他身邊抹眼淚,安慰他:“錢沒了,咱再掙嘛!”
春祥病好了,卻整日整日地躺在床上,矇頭呼呼大睡,誰跟他講話,他都沒好氣。東來眼見等不回五嬸,便不再去五嬸家門口守著,而是開始日日趴在春祥床頭的地板上,與春祥一起比著睡。
剛開始,母親還好言好語地同他講,一兩個月過去,母親失去耐性,就開始揪著春祥的耳朵,罵他沒出息了。
春祥覺得母親說得對,他的確沒什麼出息。小時候,不好好讀書,學人家去闖社會;好不容易下決心辭了職,回家養豬,錢沒賺到,卻負債累累。他覺得自己活得糟糕透了,也沒勁透了。
“窮折騰,窮折騰,越窮越折騰,越折騰越窮”,春祥自言自語。
東來聽到春祥講話,起身走到他床邊,哈著熱氣,舔他的手指。
“滾!”春祥感覺到了癢,不知怎的,一股怒火攻心,隨手抓起枕頭旁的手機,朝著東來砸去。
東來一個閃身躲開,地面上被砸出一個小坑,螢幕也被摔碎了。母親聽到動靜,急忙跑過來瞧,撿起地上的手機,氣呼呼地說道:“你生氣,拿狗跟手機出啥氣?你要是真閒得發慌,就跟著你爸去種地。”
“種地?呵……”春祥悽然一笑,把頭偏開,衝向汙跡斑斑的牆壁,不再理會母親。春祥打小就討厭種地,在他看來,一年到頭累得什麼似的,卻掙不了仨瓜倆棗,要是趕上天旱或者發水,還得倒賠錢。
正在母親長吁短嘆之際,院內突然傳來了腳步聲和小孩子的哭鬧聲。
春祥欠了欠身子,扭著頭往外瞅,卻見五嬸正手提糕點,抱著孩子往堂屋裡進。春祥胡亂披了件軍大衣,趿拉著棉鞋,坐到了床幫上。東來則早已衝出堂屋,圍著五嬸,興奮地搖頭擺尾,跳來跳去。
母親問五嬸怎麼回來了。五嬸把糕點放到桌上,一邊晃著身子讓孩子別鬧,一邊說道:“我在那裡住不慣,而且北京啥啥都貴,也是實在過不起!尤其是租房子,我們四口人,租小了吧,住不開,租大了吧,不划算。索性我就把外孫女帶回來了,讓小桃他們再好好工作攢幾年錢,等孩子該上幼兒園了,再帶過去上學。”
五嬸把糕點塞到春祥母親手中,母親放下手機,推脫了幾下,最後還是收下了。五嬸問母親手機怎麼摔了,母親看了一眼手機,心頭一酸,眼淚就要往外冒。
母親說:“他五嬸,你幫我勸勸祥兒,我是一點兒招也沒了!”
五嬸看了看頭髮蓬亂,一臉頹廢樣兒的春祥,板著臉,說道:“你的事兒,我聽說了。你難,誰不難?人活一世,誰還不遇上幾個坎兒?我那姑爺,為了多掙倆錢,逢星期天還去送外賣呢,碰上雨天,回到家,手指頭都凍得伸不開。我看著都心疼。”
春祥別過頭去,不看,也不理,五嬸繼續說道:“誰過得都不容易,你還年輕,可不敢這樣,讓你媽心疼。”
春祥還是木著臉不說話,五嬸知道春祥好面子,想著讓他靜一靜,便拉住春祥母親的手,到外面拉家常去了。
又躺了三天,春祥開始起身梳洗。母親看到兒子如此,皺褶的眉頭終於稍稍散開了。母親幫著兒子打水,像小時候那樣,幫他抹洗頭膏搓揉……
春祥覺得自己還是得回廣州去幹流水線。不想回也不行,畢竟,日子總還要過下去。自己的錢賠就賠了,問別人借的錢,不還怎麼行?他前兩天已經給廠里人事經理打過電話,經理也同意他回去。
年關剛過,春祥就用手機訂了南下的火車票。
正月初八,憋了一冬天的老天爺,撕棉扯絮般地撒起了雪。母親見雪下得大,勸春祥等雪停了再走。可是,春運期間,火車票難買,這幾天正值返工潮,票都被搶光了,再退換也不趕趟,他只能這天走。好在,村子離車站不遠,春祥只需步行走上一里多地,就能坐上去火車站的汽車。春祥輕車簡從,只背了個灰色雙肩包,包裡塞了幾件衣服,就把嚷嚷著要送他去車站的父母推回屋,一個人出了門。
雪花紛紛揚揚,蓋住了春祥的養豬場,蓋住了黑瘦樹枝,也蓋住了五嬸家那爬滿了絲瓜枯藤的破門樓。
遠遠地,春祥看到門樓下一低一高兩個黑影。是東來和五嬸。
春祥踩著雪,朝五嬸家的方向走去,打算同五嬸告別。可五嬸看到春祥過來,竟直接扭身回了屋。
春祥以為五嬸是看不起他,不想再見他了,心下立時黯然,於是,不再朝五嬸家走,而是斜著走向了五嬸家一側的小巷子。東來跑到春祥的前頭,像往常那樣,用兩隻前腳扒著他的肩,對著他的臉哈熱氣。春祥摸了摸東來的頭,繼續向前趕路。
“祥兒,祥兒!”沒走幾步,五嬸就追了上來,手裡還提溜著一袋熱騰騰的雞蛋。
五嬸笑了笑,把雞蛋塞進了春祥的揹包裡:“我一早煮好,一直泡在熱水裡的。路上記得吃!”
“謝謝五嬸!”春祥笑了一下。
“到那邊好好幹!”五嬸幫春祥撣了撣羽絨服和揹包上的雪,繼續說道。
春祥點了點頭,轉身繼續前行。剛走了幾步,春祥便聽五嬸在背後大聲說:“春祥,小桃讓我轉告你,別灰心!”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春祥“嗯”了一聲,沒有回頭,繼續往前走。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春祥再也忍不住,豆大的淚珠,噼裡啪啦,與雪花一起,一個勁地往下掉。淚珠落在雪地上,砸出一個個細碎的坑,又瞬間被大雪掩埋,彷彿那淚珠,從未滾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