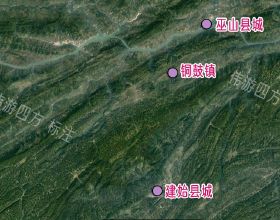“五四運動”對個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提倡並沒有給女性帶來真正的光明。封建的男權社會只當這是玩弄年輕女性的契機,接二連三的悲劇重新給女性蒙上了恐慌的陰影。在租界這個特殊的地域,新的世界不斷滲進來,可是女性的自我意識仍舊無法覺醒。此時,張愛玲以批判者的姿態出現。她深入數千年來女性生命體驗的底層,透過對歷史的思考,冷靜挖掘女性意識的礦藏。張愛玲透過作品探究女性悲劇命運的原因,她的寫作以女性為中心,改變了男性為中心的傳統,表現出對女性命運的同情和關注以及對女性生存道路的探索。
中國戲劇中悲劇的特點——中國的悲劇是女性的。張愛玲筆下這些女性都是傳統意義上生長於父權家庭的女性,她們柔弱可憐,又有著虛榮、嫉妒以及殘忍的一面。她們天生就是社會群體中的弱者,都是純粹的女人,註定一生受著男權社會的控制,受著封建禮法的摧殘。在這樣的生活境遇下,保住自身的家庭地位以及金錢,往往超過擁有愛情。她們在這樣的環境中等待、忍耐、變得虛榮貪婪,並且從他人身上報復命運的不公平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她們人性的自私、冷酷、庸俗和陰毒更加深了她們自身命運的悲劇。張愛玲的眾多作品都在提出一個關於女性價值的根本問題“女人究竟在透過什麼確立自我人格?”這個問題是女性為何長久地陷入悲劇人生的泥淖無法解脫的關鍵。而問題的答案是:女人一直在以男性的價值觀來確立自我人格。
《色戒》中王佳芝在暗殺行動的關鍵時刻放走易先生,最終導致自己殞命槍口。而一切的源頭是陪歡場女子買東西的老手易先生自我陶醉時的那抹帶點悲哀的微笑。王佳芝天真地把那笑意理解為“溫柔憐惜”,她想“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就這一剎那心動的錯念,實實在在於王佳芝的心中確立了一個錯誤的“自我人格”,為著這個男人愛她,她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她是接受過先進思想的學生,卻又和那些麻將桌上的太太們沒有兩樣,明知是賭局就會輸,卻仍不假思索地陷入這注定悲哀的命運的輪迴之中。在這個現實人生裡她們難以找到自己實實在在的位置,只能從別處尋求自己的價值。於是奮力去抓住絲毫男人的愛,至少自己是為著這個人活的,可是一切終歸徒勞。
《霸王別姬》裡堅韌聰慧的虞姬何嘗不是以項羽的壯志為她的壯志,以項羽的勝利為她的勝利,以項羽的痛苦為她的痛苦。以至於她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她這樣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她只是項羽的一個微弱的回聲,待她容顏老去項羽遲早會厭倦她。於她而言,失去項羽的愛她便不再是活生生的她,往後的歲月裡不過是別人口中的一個諡號,一口棺槨罷了,殘酷而真實。自刎前,她知道這個人活著她不能一生擁有他。他死了,她的一生也就結束了。於是死亡也變得簡單了,沒有這個男人她的“自我人格”亦不復存在。這些讓人心疼的女人從未真正把握住自我,她們以男人的座標為參照系奮力追尋,徘徊黃泉仍未明白自己為何而生,又為何而死。
反觀易先生與項羽。對於王佳芝的死易先生想“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佔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他以為王佳芝是忠心耿耿的愛著他,為他而死是她選擇的人生。但這個女子於他而言也不過是人到中年得遇的粉紅知己,僅此而已。另一邊,四面楚歌中的項羽在垓下之戰前並未想過給那個愛他的女人一線生機。他讓虞姬跟隨他直到最後一分鐘,懷疑戰敗後他的女人會繼續服侍劉邦。這樣的絕對佔有又有多少真情包含其中?
其實女人自己的命運,未嘗不是靠她們自己去把握,未嘗不是與她們自己有關。可是偏偏那樣一個時代,女性的選擇與把握不得不背離自己,繼續將努力伸出的雙手探向婚姻,男性與金錢。《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能在受到丈夫家暴後果斷離婚無疑受到過新思想的影響。這樣一個走向現代的女性在“舊人物”盤踞的白公館眼睜睜看著這種大家庭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反目成仇,她恩斷義絕的逃離也只能依憑婚姻。正如文中白流蘇與徐太太的對話所言:“我又沒念過兩句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麼事?”中國“娜拉”的悲劇就在於無法擁有職業改變自己在經濟地位上的被動。沒有經濟地位,女性的人生依舊得拴在男子的身上,婚姻即是女人的依靠與保障。
大家閨秀白流蘇無法在物慾橫流的新世界實現自我的獨立,她需要一個金錢有保障的男人依附,是否愛他並不重要。她與範柳原兩個精刮的人,為著截然相反的目標算盤打得仔細。卻從香港戰爭開始的那天,倆人拋卻了所有自私與算計,開始攜手面對真槍實彈的生與死的戰爭。死亡讓他們重新獲得了生命的契合,兩個個人主義者彼此交付了真心。現代文明的繁華虛榮在戰火下暴露出了它的蒼白無力,當浮華世界化為廢墟,剩下的彷彿只剩下飲食男女兩項主題。這種平實的人間生活促成了白流蘇與範柳原的婚姻,也使我們看到了那個異化的時代中女性身後的風雨飄搖。
女性對自己的淡漠以及骨子裡深深的奴性讓自己甘願依附於男性與這個扭曲不公的社會,對原本美好的愛情的期待,也漸漸變成了對物質的、金錢的慾望。長久環境壓抑下的病態的心理匯成了女性生存陰暗心理的眾生相,她們沉湎於悲劇的汙淖仍不忘伸手把岸邊的乾淨女孩扯進這深淵來。《心經》裡那個說自己某種程度上“人盡可夫”的女孩綾卿對許小寒談及自己的家人道“都是好人,但是她們是寡婦。沒有人,沒有錢,又沒受過教育。我呢,至少我有個前途。她們恨我吶,雖然她們並不知道。”這並不是誇張的說法。那些上一輩接受了悲劇命運的女性無不日復一日的吸著大煙,摸著骨牌,算計著家財,在無愛的歲月裡壓抑變態。待年華逝去,這些女人內心早已變得自私與冷酷無情。於是女性的悲劇就正如《金鎖記》的結束語“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黑暗中幽幽窺探的月帶著瘮人的陰寒夠侵蝕幾代人的骨血。
張愛玲筆下那個瘋魔了的女人——曹七巧“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她自己不幸也硬是要拉上幾個人的幸福與生命同她陪葬,於是女兒長安、兒媳壽芝、絹姑娘、三嫂蘭仙和小妹姜雲澤,這些女性無一例外都因七巧造成了人生或多或少的缺憾。七巧悲劇的根源是身不由己地接受了兄長安排的畸形婚姻,所以對於姜雲澤的婚事她極熱心的在老太太面前挑唆,蘭仙與季澤的婚事亦是她從中推助。可是姜雲澤並不想覥著臉似的低人一等出閣,蘭仙生平最大的憾事便是出閣是趕著非常時期潦草成的家。七巧看似體貼熱心的舉動背後是隱隱的怨念與報復,她也要從婚姻的開始就為那些初碰人事的女孩埋下悲劇的種子。
七巧畸形的人格使她對自己身邊人甚至子女衍生出一種變態的報復心理。家境貧寒是她悲劇的源頭,她便瘋狂的佔有金錢。自己婚姻悲慘,情慾得不到滿足, 那麼其他人也休想得到幸福。她瘋狂使用陰毒手段讓身邊所有有望看到光明的人最終成為了她悲劇人生的殉葬品。這些走上悲劇絕境的女性背後沒有光的所在,黑暗的淵裡透出一線炯炯的光亮是這群瘋魔女性面具下陰陰的一瞥。
女性悲劇的另一面是那個虛偽病態的男性世界造成的。《封鎖》中的呂宗楨象徵著屈服於社會,麻木生活的一大部分人。他穿著體面,抗拒思考,看不慣清寒子弟,不論外表還是思想都被社會的秩序束縛得整整齊齊。在封鎖中的電車裡,這個“切斷了時間與空間”的場所給了所有人人性自由的空間。於是他卸下了面具,對身邊的女人吳翠遠傾訴自己累積的壓抑,表達自己真實的慾望,袒露對愛情真切的嚮往。“他們戀愛著了”那時他變得溫柔自然,可愛而勇敢。直到封鎖開放“切斷時間與空間”他立刻逃離真實的自己,“遙遙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恢復虛假規矩的模樣,不真誠也不瘋狂,自私怯懦的“裝死”。他給了吳翠遠一個關於愛的“不近情理的夢”,繼續為自己的現世安穩一頭扎進自私麻木中當一個“好人”。可是這個女人,卻被這個滿是“好人”的虛假世界支配擠壓得失去了希望。
張愛玲作品中的另一位“好人”必然是《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面對初戀玫瑰他閹割自己的情慾,面對真心愛他的王嬌蕊他自私捨棄,面對妻子煙鸝只當她是豎在家的“貞節牌坊”。這樣一個“好人”不斷逃避自己人性真實的一面,為著世俗評判的眼光,道德規範的約束以及自己的前途名譽,忍痛拋棄真誠和愛,戴上虛偽的假面,就這樣有始有終,有條有理的成為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他創造了一個能夠隨心掌控女性與自我的荒謬虛偽的人性世界,隻身高高在上立於其中,可是光鮮外表正對著的鏡子中無不展現著他的不自信,後悔與悲哀。作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煙鸝的人生全然蒼涼的模樣,她從未得到過真心的愛,並且日復一日忍耐著丈夫的冷漠與傷害。一個蒼白的知識女性硬生生被擰巴成一張塵埃上皺黃的紙,枯槁空洞一無所有。
張愛玲筆下的“舊女性”一直在社會生活中尋找一種擁有權力的捷徑,於是她們結婚、生育、想透過家庭確立自己的地位,但是怡怡相反,婚姻使她們落入了陷阱。在張愛玲看來女性若找不到獨立的價值,那麼對她們來說,婚姻不過是她們實現最終的價值罷了。這些女性永遠擺脫不了世俗的束縛,跟不上時代的步伐。
張愛玲作品中這些女性不論是因為自身的卑弱與虛榮投身婚姻,還是在金錢與情慾異化中變態,或是掙扎沉淪於男性世界的支配控制。最終她們都自覺自願自甘的屈居於男性的影子裡,崩潰瘋狂,萎謝凋落。張愛玲透過對作品中女性冷靜、徹底的指責,不動聲色地展示出中國舊式婦女肉體和精神的痛苦,展現了這些女人可悲的生活方式與畸形的生命形態,剖析出女性自身是造成人生悲劇的內在原因。女性經濟獨立與自我價值的構築是結束自身悲劇的首要因素,正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丁阿小,她自己賺錢養育兒子,永遠沒有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對於男人亦沒有依賴的心理。張愛玲給予丁阿小慈悲的母愛,堅強,獨立與勇敢,在她的身上完成了女性的自我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