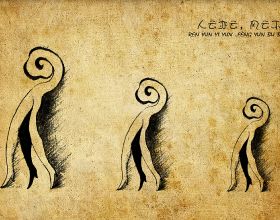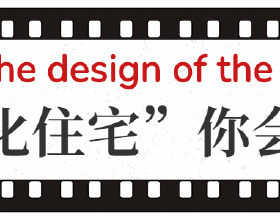雖然兼具詩人和作家雙重身份,但詩歌在黃梵心中有著更重的分量。他認為,“詩歌是一切寫作的起點和終點”,而寫作,“不只關乎尊嚴、聲名、利益,也關乎人的生活需要”。
於是,在出版了一系列詩歌、小說作品之後,黃梵用《意象的帝國:詩的寫作課》,首次分享自己的詩歌創作心得,教授寫詩的方法。
寫詩真的可教嗎?圍繞這個問題,向來有紛爭。但是,黃梵的詩的寫作課,聊的遠不止詩的寫作,更多是普通人如何接近和抵達詩意,如何在生活中用詩歌安頓人心。
詩與生活,遠比你我想象的要密切得多。
黃梵詩人、小說家、副教授。已出版《第十一誡》《浮色》《南京哀歌》《月亮已失眠》《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中國走徒》《一寸師》等。曾獲“2015—2016年度十大好詩”提名獎、紫金山文學獎、《芳草》漢語雙年詩歌十佳獎、《作家》“金短篇”小說獎、金陵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後天》雙年度文化藝術獎、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漢語詩歌獎、博鰲國際詩歌獎等。
那些通常意義上的成功者,為何要轉向文學尋求意義?
上書房:作為一位成熟的、優秀的詩人,出版一本教人寫詩的書,是很冒險的,必然會遭遇這樣的質疑:詩是可教的嗎?您為什麼會出版這本《意象的帝國:詩的寫作課》?
黃梵:教人寫詩這件事,在我出版這本書之前,我已經有了10年的實踐經驗,且讓很多學員學有所成,所以才有底氣寫這樣一本書。
我寫了20多年的詩,但直到2011年,才因為外部的推力,促發我去澄清一些有關詩意的問題。除了外界的各種講座邀請,最大的推力來自學校,學校鼓勵我開設“文學創作”的通識課。通識課就意味著,你得對水平參差不齊的人,甚至零基礎的人講寫作之道,不只是讓他們改變寫作觀念,還要將他們帶入當代寫作的實踐前沿。
給普通人講寫新詩,迫使我去追蹤一句詩的詩意究竟是由什麼決定的。透過回溯詩意的源頭,體察詩人的創作經驗,我找到了理解詩意、寫出詩意的便捷之路。我意識到,普通人容易理解的人性,才是支撐詩意的根基。說得更確切一些,構成詩意的內部機制與構成自我的內部機制,不過是人性的一體兩面。這個認識讓我的教學取得了奇特的效果。透過不到三個月的課堂訓練,我的學生中,有不少從未寫過新詩的人,開始在專業文學期刊上發表詩作,甚至有好幾位學生在結業兩年後,獲得了詩獎,出版了詩集,被認為是詩壇後起之秀。
這堂學校裡的通識課,因為常有校外的人來蹭課,逐漸被外界所知。2017年的暑假,嚶鳴讀書會的策劃人說服我面向社會開寫作課。他是學哲學的,比我更早看清這門課對社會人士的意義。
課程大受歡迎,尤其讓我意外的是,參加課程的人中有很多是企業家、高校教授、領導幹部這類通常意義上的成功者。他們為何要來參加詩歌寫作課?我發現,除了有一類人是想成為寫作者之外,更多的人是在生活中找不到北了,覺得這樣過下去不是個事兒,轉而向詩歌尋求人生的意義。透過學習,這類人發生的變化很大。有個學生是某銀行支行行長,行里人際關係複雜,讓她頭疼。透過學習,她發現詩歌是可以極大地影響人心的,於是就在行裡推廣詩歌文化,鼓勵大家讀詩、寫詩,她的團隊後來成為系統裡最團結的。五期班上還有一個製造汽車部件的企業家,學詩過程中他跟我說:“難道工廠只是一個枯燥的生產空間?工廠就不能有詩意的生活?我過去製造部件,我現在要製造生活。”他用汽車部件搭出雕塑,用詩意改造職工食堂,工人變得很願意待在廠裡。
寫詩讓這些焦慮的心靈安靜了下來。他們原先把成功理解為世俗層面的成功,學詩之後,他們的心境平和了,不再焦慮和衝撞,這才是真正的成功。安頓人心是最要緊的。能用金錢、地位來安頓人心嗎?安頓不了的。但詩歌可以讓你找到現實世界中志同道合的夥伴,可以讓你把古往今來的詩人作為精神同伴,有置身同一個精神共同體的感覺。你以前是孤單一人面對世界,沒有底氣,現在,你有了詩歌撐腰。
人性的審美根基到底在哪裡,與生活的根基是否重疊?
上書房:為什麼一堂詩歌寫作課可以帶來這樣的變化?
黃梵:我不僅教大家寫詩,更是帶著大家思考生活問題、文化問題:人生的根基到底在哪裡?人生的根基和你的生活的根基、工作的根基是否有重疊的地方?
寫作不只關乎尊嚴、聲名、利益,也關乎人的生活需要。你若能從人性角度去理解寫作,就容易把寫作之門開得更大。誰都知道,人是審美動物。比如,衣服本是用來遮體保暖的,但人們還是會在乎衣服的款式;房子本是用來居住的,但沒人願意住毛坯房。這些就是人的審美本能,人有把身邊的一切用品、環境等審美化的衝動。人對身外之物有審美需要,對身內之物,比如情感、情緒、感覺等,也有審美需要。無論是遇到高興的事,還是悲傷的事,一般人都有與他人分享喜悅,或向他人傾訴悲傷的願望。高興、悲傷、憂鬱、孤獨、痛苦、愛、恨、虛無等情感、情緒、感覺,如果只是堆積在心裡,它們是無序的、混沌的、無形的、模糊的,如百爪撓心,難以觸控,人不會滿意這樣的內心狀況,會本能地想改變它。普通人能找到的改變方式,就是訴說。訴說時,人需要用語言把內心堆積的東西,一句句說出來。這樣,原本無序的感覺,就有了語言秩序;原本混沌的感覺,就有了時間、邏輯的順序;原本無形的、模糊的感覺,因為語言而有了明確含義,就會得到明確描述,變得有形、可感。訴說就是一個審美化的過程。
人訴說的時候,常會激動,甚至語無倫次,就算訴說時十分平靜,口頭表達也難免拖泥帶水,散漫或重複,固然比不訴說、把感覺堆積在心裡要好不少,但還是滿足不了一些人更高的審美需要,畢竟訴說產生的秩序感,只比把感覺堆在心裡要高一些。這些不滿足訴說的人,就會用寫來代替說。寫不可避免地要斟詞酌句,要避免囉唆重複,要避免結構失調,書寫產生的秩序感,自然就高於訴說。
再琢磨一下寫又會發現:便條、信件的秩序感不如散文;散文的秩序感不如小說;小說的秩序感不如詩歌。秩序感的高低,對應著審美要求的高低,詩歌的審美要求是最高的。這就很容易理解網路時代的種種寫作現象了。為何很多人會天天寫網文,甚至有人天天寫詩?寫作於他們,與晨起梳妝打扮來滿足對儀表的審美需要一樣,不過是迎合內心審美化的需要。
從審美需要出發,就可以回答人們常問的一個問題:文學會消失嗎?我的回答是:除非人的審美需要消失了,否則文學是不會消失的。
上書房:您在書中提出,“詩歌是一切寫作的起點和終點”,為何這麼說?
黃梵:因為詩歌不只是對詩歌負責,它還對語言負責,它是民族語言的守護神。所有文學體裁中,詩歌是離語言最近的。就算可以逃避詩歌,也逃避不了一直被詩歌影響的語言。我們用的很多成語,就來自詩歌。
詩歌一直供應著語言的標準,最高標準。如果沒有詩歌,你如何判斷語言的好壞?你也許會說,只要有小說或散文,語言就有好壞的參照。但其實,小說或散文為了醫治語言的庸常,借用的處方還是詩歌,不是借用過去的詩歌,就是借用當代的詩歌。沒有詩歌,人們很難知道漢語的美,可以達至多深、多廣、多高。文學界有一個現象很普遍,凡小說語言很棒的作家,通常早年都寫過詩。甚至於廣告語、實用文,如果帶有詩化的意味,也會傳播得更廣。
詩歌會影響我們的思維。因為詩歌會把語言運用到接近表達的極限,甚至試圖超越語法的規則,超越字典對字義的約定,抵達言外之意,試圖抓住語言形成之中、之前的那些意識,讓人面對語言之外的超驗領地,仍能怡然自若。小說和散文一般不會冒著晦澀難懂的風險去探索語言,除非是那些改變觀念的小說革命,比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可是對詩歌寫作來說,探索語言是常態。所以,現代詩會塑造人的現代意識,古典詩會塑造人的古典意識。
詩歌教化語言,語言教化思維,思維教化人,古人很早就意識到了詩教的重要性,而把寫詩視為讀書人的基本功。事實上,一個人一旦有了寫詩的經驗,就完成了對其他寫作的啟蒙。大家千萬不要有體裁偏見,不是寫小說就只學小說,寫散文就只學散文,寫詩歌就只學詩歌。不管你將來是否成為詩人,不管詩寫得好不好,透過寫詩訓練,你可以釋放出語言潛能,培育出敏銳語感,重新認識詞與詞的微妙搭配,擺脫日常語言的束縛,極大解放你的想象力。你的筆,需要長出更多更纖敏的語言觸鬚,來供小說、散文、應用文寫作之用。
將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是詩意的本質
上書房:對於詩歌,人們最難把握的是詩意。如何理解您剛才說的“構成詩意的內部機制與構成自我的內部機制,不過是人性的一體兩面”?
黃梵:一般人覺得浪漫的事、遠方的事、夠不著的事,是有詩意的;而眼前的生活總是苟且的,身處的現實環境總是缺乏詩意的。他們還認為詩歌只屬於詩人,而詩人的一生總是動盪的,其實,古今中外,安靜的詩人也有很多,他們過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
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用的是非常日常的眼光。一旦採用日常的眼光,大家就會覺得藍天白雲有詩意,悽風苦雨沒有詩意,就會用自己身體的愉悅與否,來判定有無詩意。但這不是詩意的本質,詩意的本質是“熟悉的陌生”,是在現實中找到旁逸斜出的路,是把通常認為“苟且”的事物陌生化,賦予它們以詩意。
這背後是有人性根據的。人既有追求安全的需要,又有追求冒險的需要,這是數百萬年的人類生活在人們心中積累下來的一種本能,這種本能根植於我們所有的生活中,且不可改變。一件衣服穿久了,你想去買新衣服;在一個環境裡待久了,你想去旅行,想去認識陌生人;反過來,如果你一直人在旅途,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中,你又十分想要安定下來。人們就在熟悉與陌生中不斷切換。
詩歌把兩者調劑得非常好,既可以給你安全感,又可以帶著你冒險,“熟悉的陌生”就是詩歌的平衡策略。這本書除了總結古往今來關於詩的他人認識,書裡也有我的原創,比如寫詩的四種模式,就是我對這種平衡策略的具體化。對舊體詩來說,你必須按照格律的要求來寫,詩的音樂性是你在寫之前就知道的,這是安全性的表現;但優秀的詩人總會從格律中掙脫而出,會出現拗字,不符合平仄的規律,這恰恰是冒險的體現。現代詩遵循同樣的法則。現代詩提倡寫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熟悉”的。但熟悉的日常生活怎麼可以有新鮮感?那就要創造意象。很多人把意象的創造想得特別複雜,其實很簡單,意象創造就是把舊的事物放在一起,產生新的事物。就像“月亮代表我的心”這句歌詞,雖然它現在已毫無新鮮感了,但它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帶給了人們詩的意象。月亮和心都是我們熟悉的事物,但合在一起,就產生了新的眼光,就把你的情感和月亮這個意象投射、融合在一起,月亮所具有的神秘感,月夜帶給你的清冷、幽靜、明亮,都成為你的情感的表達。再比如,蝴蝶是舊的事物,落葉也是舊的事物,但如果我說“蝴蝶是不肯落地的落葉”,就有新的事物產生了。
總之,詩意不僅僅在得到之中,也在付出之中;不僅僅存在於所有帶給你舒適幸福的事物,也存在於所有帶給你痛苦悲傷的事物。詩意不來自世界,而來自詩人的注視。我甚至專門寫過蒼蠅、蚊子和蟑螂,就是為了證明給大家看,只要我們用生命平等的眼光去看蒼蠅、蚊子,蒼蠅、蚊子也可以有詩意。
上書房:哪怕是生活的褶皺處,都可以有詩意棲息。
黃梵:是的。人們總是擔心自己寫的事物不夠重要,不夠崇高,好像詩意的世界與日常的世界存在著一條界河。我認為,寫詩首先應該忘掉宏大的歷史,而用顯微鏡打量自己的生活。
那些歷史的大題材裡,已經有太多的公共話語,有大量別人留下的詩化陷阱,你如果也去寫那些東西,很可能不過是在套用別人的詩意。而你的“卑微”生活,與人類的宏大生活其實是暗渠相通的,它們都有相同的生存和道義邏輯,你書寫自己就等於在書寫人類。所以常人需要“去蔽”,因為常人有太多的視而不見,太多的習以為常,它們遮住了我們的眼睛,這是一種由觀念造成的“白內障”。
詩意不侷限於具體的詩歌,也瀰漫於我們的生活
上書房:如何理解我們常說的“詩意生活”?
黃梵:詩意不僅僅侷限於具體的詩歌,也瀰漫於我們的生活。人為什麼需要詩意的生活?到底什麼是詩意的生活?人們對詩歌、詩人存有誤解,認為詩人是天才,認為只有詩人可以寫詩,我們老百姓就不要和詩沾邊了。我的這本書是祛魅的,是要告訴大家,不僅人人可以寫詩,而且人人需要詩;印成文字的是詩,沒有印成文字的也是詩,那是你用生活寫成的詩。不管一個人寫不寫詩,詩都與他的生命相關聯,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正在採用詩意的方法更新自己的生活。
你雖然不寫詩,但你在生活中也在創造詩意。我剛才已經舉過例子了,無論穿新衣、換髮型,還是過一段時間想去旅行,都是把熟悉變得陌生的做法,普通人都需要詩意的生活。我們之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已經在生活中本能地運用了詩意;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現代人與詩意生活久違了。古代詩人與生活是靠得很近的,我們可以透過作品看到古代詩人之間很日常的唱和,以及那些即興的生活場景。我們現代人為什麼會與詩歌有割裂之感?我認為有一個原因可能是為大家所忽略的,那就是,胡適等人當年提倡白話詩,引進的是當時西方的現代派詩歌。現代派詩歌是脫離生活、俯視生活的,拒絕和生活交流,拒絕和讀者交流。這有當時的時代原因。那麼多年過去了,我們很有必要恢復中國古代的詩歌傳統,我無論是自己寫詩,還是教別人寫詩,都希望把生活詩學作為整個漢語詩學的基礎。當然,對傳統不是全盤恢復,而是要有新的做法。我們必須要思考現代詩和現代生活的關聯,我們對詩意的理解必須有所變化,核心是要用新的眼光去看舊的世界。
上書房:讓我們與詩意生活漸離漸遠的,也許還有現代人那份揮之不去的焦慮。
黃梵:這是一個尋求人生意義的問題。
很多人為什麼焦慮?因為他們從小所受的教育,讓他們對成功的定義非常狹隘。當他們發現自己不“成功”時,就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生活本身是不提供意義的。你一天干了很多事,但意義在哪裡?你做的事情不會開口告訴你意義,可是,人類總是需要面對總結的:一個月的總結,一年的總結,一輩子的總結。普通人不善於總結,無法從亂七八糟的事情中去總結人生的意義。怎麼辦?這時,文學的意義就顯現出來了。文學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為我們的人生提供意義。文學不僅僅是講故事,而是透過對生活的描述,賦予故事一種意義。小說也好,詩歌也好,都是生活的宗卷,給予生活很多種意義的提示。人們讀小說、讀詩,會獲得很多啟發,從中找到和自己類似的經歷和情感,看看別人是如何思考和體驗的。很多喜歡文學的普通人,通常內心都很平靜,因為他們透過作品,找尋到了人生的諸多意義。
上書房:您曾是理科高才生,在彈道研究領域遊刃有餘,但您中途捨棄一切,轉投文學的懷抱。很多人神化您的這段經歷,將之視為您在文學上的“天生麗質難自棄”,果真如此嗎?詩歌對您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黃梵:看似華麗的轉身,其實都是挫折和無奈。直到高考以前,我的理想都是學天文,想去一個天文臺,孤獨地看星星。但在高一那年,我和其他22位尖子生一起,其中包括已故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鍾揚,提前參加高考。我的考分,除清華、北大之外,其他學校都是可以上的。但因為我在志願表的最後一欄,填了南京理工大學,南理工的彈道專業就繞過所有其他學校,直接提前錄取了我。當時國家急需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我就這樣進入了一個不喜歡的專業,從此無緣天文。
雖然我只在專業上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其他三分之二時間和精力都用來閱讀文學作品,但我還是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畢業了,並留校在彈道專業任教。這個專業很受國家和學校的重視,我也完全勝任這份工作,但我的心是不安的,精神是不愉悅的。我幾次要走,主任都不放。最終,我把自己調到了學校的出版中心,總算是與文學近了一點。那是1988年的事。2003年,我那時已經出道,成了所謂的作家,學校就招我回去教授文學課。
但我寫詩是始於1983年。那一年,我在畢業分配的問題上遭遇挫折,初戀也失敗了,身體也不好,在家休學一年。我整夜整夜地失眠,每天會心顫兩小時以上。我一開始想研究數學、物理來分心,研究了幾個月,還是不行。有一天,我寫了一首古體詩,情緒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出口。我就每天寫詩,先是古體詩,後是新詩。寫了一屋子的詩,父母很擔心我,他們讓我去武漢的叔叔家散心。我前腳剛走,他們後腳就從千里之外的四川請來一位20多年從事寫作的老同學。此人在我家住了一星期後,留下一份鑑定書走了。鑑定書上寫著:黃帆(我的本名)毫無寫作才能,建議從事除文學以外的任何職業。
我父母信了,我也信了,從此不再寫詩。直到1986年,學校成立了一個青年教師文學社,邀我加入。一加入,我對詩歌的火就復燃了。當時我就想,不管能不能成為詩人,我都要寫詩,寫詩能救我。同時我決定,再也不和父母討論寫作這件事。
後來,我認識了現在的愛人,我給她寫了一首情詩。她要求我,永遠不要發表這首詩,讓這首詩只屬於她。她還對我說了一句話,讓我從此死心塌地地搞文學。她說:“你應該寫詩,不寫太可惜了。這個世上有無數的處長、無數的老闆,可是隻有一個詩人黃梵。”
上書房:當下很多家長逼著孩子學不喜歡的專業,做不喜歡的工作,您對他們有什麼要說的?
黃梵:我的教育理念在我女兒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實踐,我們鼓勵她做她喜歡的事。
熱愛是最好的老師,當下社會正因為許多家長的想當然而致很多人都在從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哪怕他們是科班出身,但因為不喜歡,他們不會去鑽研,不會去想達到專業的巔峰,這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一種業餘性。這樣的社會,是呼喚不出工匠精神的。
《意象的帝國:詩的寫作課》黃梵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來源:作者:顧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