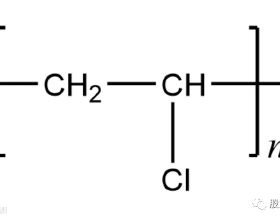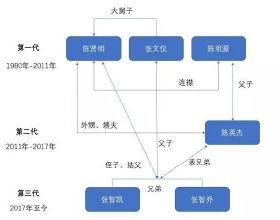2020年度傑出作家 馮驥才
作品《藝術家們》
祖籍浙江寧波,1942年生於天津,中國當代作家、畫家和文化學者。現任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民協名譽主席、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等職。他是“傷痕文學”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說”在當今文壇影響深遠。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二百餘種。代表作《啊!》《雕花菸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一百個人的十年》《俗世奇人》《單筒望遠鏡》《藝術家們》等。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韓、越等十餘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五十餘種。多次在國內外獲獎。他倡導與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傳統村落保護等文化行為對當代人文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授獎辭
馮驥才是一個名字,也是一種文化情懷。他向藝術要美,向俗世要傳奇,向行將消逝的文化遺產和古村落要文明的證據,向過去要未來。他對文化現狀傾全力而赴之的痛惜、救護,把知識分子的良知落實成了一種有感召力的行動、有反思精神的寫作。他出版於二〇二〇年度的長篇小說《藝術家們》,是對一種文化人格的追念和加冕。時代熾熱,才華閃光,那些藝術家的世界裡,慾望與理想同行,絕望與希望並存,但在浮華背後,記憶最重要的遺存仍然是對美和真理的求索,對善好人世的眷戀。這本寫給自己的莊重之書,也充盈著對精神同道的真誠禮讚。
這本書在我心裡壓了太久了
南都:請談談動念寫《藝術家們》這部小說的原因。
馮驥才:原因挺複雜的,不是一個原因導致了一個結果,而是有多重原因。實際上,年輕的時候我就有一個夢想。我是畫畫出身,我也看過一些寫藝術家的小說。這類小說中國不多,歐洲多一點,而且有寫得非常好的。比如我特別喜歡羅曼·羅蘭寫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羅曼·羅蘭寫過一系列音樂家的評傳,比如《貝多芬傳》《亨德爾傳》,也寫過雕塑家米開朗琪羅的傳記。
出生於上世紀40至50年代的那一代人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奉為翻譯文學裡的經典。因為是傅雷先生翻譯的,譯筆特別好。最重要的是,這是以貝多芬為原型寫的一部小說,他寫出了音樂家的一種主觀的感覺,這種感覺充滿了音樂的氣質——音樂裡的韻律,音樂裡的節奏,音樂裡的獨特的意境。《藝術家們》發表以後,《收穫》雜誌在上海給我舉辦了一場研討會。我在研討會上就提到過《約翰·克里斯多夫》。
20世紀80年代,我們那一批作家在傷痕文學之後進入文壇,寫的更多的是對社會貼得很緊的,反映社會矛盾和時代氣息的,反映人的渴望的小說,幫助讀者認識生活。那時我很想寫一箇中篇,叫《藝術家生活圓舞曲》。我腦子裡有很多藝術家的形象,因為我認識很多同時代的藝術家,有很多特別值得寫的東西。
我想我多虧沒寫。如果我寫,我一定會把他們寫淺薄了。幸虧我又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我經歷了不同的時代,經過了社會的轉折,也體驗了不同的時代與人之間的關係。比如市場的時代,消費社會,比如改革開放以來東西文化的激烈碰撞等。這樣一些大的背景下,藝術家們各奔前程,走不同的道路,他們的命運如何?我經過了這些時代,我當然要思考藝術家的命運,他們的心靈和歷史,他們在不同時代下、在各種新的問題面前的遭遇與選擇,以及選擇帶來的不同境遇。這些都是我寫《藝術家們》這部小說的原因。
南都:小說的20多萬字是一氣呵成的嗎?
馮驥才:我寫《藝術家們》這部小說時特別快。第一遍下來可能也就是兩個月多一點。寫完以後修改了一段時間。如果不是新冠疫情蝸居在家,這個小說根本寫不了。因為我的時間特別緊張。
但疫情突然就中斷了我很多聯絡,跟誰也不能見了。這段時間給我一個巨大的財富,就是連貫的、完整的幾個月的時間。平常我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時間,而是時間不連貫。寫小說的人要跟他虛構的人物在一起生活。你就是跟你家人在一起,面對面,你腦子裡想的也是你虛構的人。你家裡人當然已經習慣你了,一般人不習慣你,覺得你怎麼忽然就走神了,也不聽人說話了?實際上你在跟你虛構的人物交流。虛構的人物在經歷各種各樣的變化、遭遇。
對於我來講,寫短篇得要一個禮拜,寫中篇我起碼要二十天到一個月,寫長篇就得幾個月的時間。我在寫《俗世奇人》的時候基本是放假和過年的時候寫。寫《俗世奇人》最快的時候我一天可以寫兩個短篇。
為什麼呢?不是我本事大,而是這個東西在我心裡憋的時間太長了。有時間它就會蹦出來。
但是長篇不行。寫長篇必須有一段比較長的充裕的時間,而且要“與世隔絕”。整個那段時間,天賜的,全給我了,很美妙。所以我一口氣就寫下來了。你看這本書你一定覺得很順暢。為什麼呢?因為壓得太久了,就像火山一樣,岩漿壓的時間越久,噴發出來的力量就越大。
有現實原型,你才好去感知他
南都:讀完小說後我有一個感覺,小說前半部分楚雲天的經歷跟您自己人生的某些階段十分接近,所以,這個小說裡到底有哪些是取材於您的真實生活?
馮驥才:小說的人物實際都是虛構的,但一般小說的人物都有原型,特別是主要人物。如果沒有原型,沒有一個生命的實體,你就不好感覺他。
就是城市也有原型。比如賈平凹寫商州,或者莫言寫高密;就像天津是生我養我之地。王安憶寫上海得心應手,因為那是生她養她的地方,她從小跟那個地方水乳交融,她的情感、她的生命的氣息,跟那個地方都是溝通的。所以人物擱在那兒,自然就活了。
人物就像城市一樣。城市你把它擱在一個熟悉的地方,你就好感覺它,所有地理位置、風物、環境,周圍人的性格,就都是活的。如果完全虛構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你可以把你知道的地方換一個名字,但這個地方的感覺必須是你熟悉的。
人也是這樣。這個人物必須有可感覺的現實依據。比如我在生活中發現那個人物和我寫的人物特別接近,我就把這個人物無形中而不是有意識地寫進來了,使他成為一個原型。原型的意思不是說一模一樣照著他來寫。作家從自己最熟悉的那些人身上去找生命最可感的東西作為原型。一些其他人物的特徵,如果能跟這個角色生命融合,變成同一個個體,那自然而然也被寫進來。也可能再加上作者自己的虛構。
所以你剛才那句話說得特別對,《藝術家們》上半部我的東西很多,到了下半部我的東西就很少了。上半部我主要寫六七十年代的藝術青年。那個時候沒有藝術事業,他們沒有社會責任,但是他們有對藝術一往情深的摯愛,有藝術的夢想,美的夢想。這麼一群人他們在一起抱團取暖,共同感受藝術的氣息。小說裡的“三劍客”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們的友誼也特別珍貴,那就是我的年輕時代。
我寫的時候,我周圍的那些人自然而然就進來了。因為過去的生活裡的記憶,總是把最讓你感動的東西留存下來。那些人很容易就進入了我的小說。可能是他們的相貌,也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相貌,加上他們的個性,還有另外一個什麼人的細節,或者是我想象出來的東西……自然而然就把它們放在一起了。
因為楚雲天是《藝術家們》裡最主要的人物,而且我想用他來表現我的角度,我要揭示我的角度,我個人就很容易帶入。我把自己寫進來的時候,一定帶著我的經歷,帶著我的故事,帶著我的情節,最重要的是帶著我的心理和對藝術的感覺。這樣,等人物都進來以後,我已經知道藝術家在新的一個時代裡會如何行動。每個人會怎麼做,我心裡都明白。他們就“自由發展了”。
南都:所以您就像“架構師”一樣,完成了前期定調的工作以後,小說就開始自由發展了。
馮驥才:說實話我根本不知道它會怎麼發展。當然我有一些大概的想法。我知道我的朋友們有的沉淪了,在市場社會里,被消費社會的準則所左右了,被庸俗社會觀侵蝕了,非常有才氣的作家,最後崩潰了。
比如我寫洛夫這個人物,我自己認識的好多藝術家,有更悲慘的自戕。什麼樣的都有。也有的藝術家沒有那麼大的才氣的,時代讓他開闊了眼界,激發了他的創造力,但後來也沉淪了,在生活中慢慢煙消雲散了。也有堅持自己的藝術理想,堅守藝術的,這樣的藝術家特別少。比如我在小說裡寫了兩個人,一個是高宇奇,一個是易瞭然。
我也寫了唐三間、屈放歌,這些人都有生活原型,在市場裡呼風喚雨。他們在市場上太成功了,有那種大老闆式的財大氣粗。在市場社會里,我們對畫的標準影響了兩部分人。一部分人是普通觀眾,他們衡量藝術的標準已經變成了畫市上的價錢了,但市場的價錢充滿了虛假。這是一個極端。另外一個極端就是真正影響或者腐蝕了我們的畫家,使畫家沒有為精神工作的純粹性了,他失去了藝術家的本質和氣質。就像我寫的洛夫這樣的人,非常有才華的藝術家,但是他們被市場收買,最終又被市場拋棄。
儘管近二十年我一直在田野奔跑,在做古村落的搶救,非遺的搶救,但是我相當一部分的目光注視著藝術界,我也注視著作家們,我有時候有憂患。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確實沒有出現80年代羅中立畫的《父親》那樣的作品。因為我們的時代缺了80年代藝術家的純粹性,以及對時代的激情。
南都:《藝術家們》裡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當代中國藝術家群像。您覺得哪個人物是寫起來最艱難,最耗心力的?哪個人物是您個人最喜愛的?
馮驥才:實際上,如果我像寫楚雲天這麼寫高宇奇這個人物,肯定是很難寫好的。因為我是從楚雲天的角度去寫的,小說裡最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或者我最崇尚的人物,或者楚雲天最崇尚的人物,實際是兩個人,一個是高宇奇,一個是易瞭然。我都沒有把他們放在楚雲天的身邊,不像羅潛和洛夫。這兩個人沒有和楚雲天生活在一起。我把他們放在遠處,一個在安徽,一個在河南。
因為我覺得,只有放得遠了,有距離了,這個人物才能更理想化。
好多人知道高宇奇的生活原型是李伯安。實際上,我在寫小說的時候,跟我現在對李伯安的感覺是一樣的。在我心裡,李伯安就是一個神。
我跟李伯安的故事可能你也知道,關於李伯安的第一篇文章《永恆的震撼》是我寫的。我認為,如果說20世紀前半個世紀最偉大的畫是蔣兆和的《流民圖》,後半個世紀最偉大的畫應該是李伯安的《走出巴顏喀拉》。它是永遠留在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幅畫。這個畫家最了不起的是,他一生從來沒有賣過一張畫。價格不是衡量他的畫的標準,衡量他的標準是一個時代的藝術,是我們心裡崇高的審美。
我的文化遺產搶救不是學者立場,是作家立場
南都:對於當代的藝術界來說,凝聚了您一生感悟的《藝術家們》可以說是一部批判和警示之書。小說出版以後,在藝術界是否引起反響?您是否希望它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功能?
馮驥才:當然我也聽到藝術家們有很多的議論。我擔心人們會以為我的某一個人物是在影射某一個畫家,但目前還沒有這種情況。
但是大家也在思考,一個是高宇奇這個人物,另一個是藝術家們對價格的追求,導致當前的藝術明星都是價格最高的。過去我們一說好的畫家應該是吳作人、徐悲鴻、李苦禪,他們的畫藝很高,我們不談他們的價錢。現在一談畫都談價格,都為一張畫過了億感到驚訝。
人還在世,一張紙才六尺長,你畫完一張畫比一個工廠的價格還高,怎麼可能呢?這其中就有很多商業炒作。我覺得這個小說引起的這方面的反思比較多。
這個小說實際上我還沒寫完。我剛寫完了一箇中短篇的小說集。明年找時間,我還要寫一個藝術家的小說。我覺得它有兩重意義,一個意義是藝術家的主題,另一個意義是我所在的這座城市的主題。
天津這座城市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樣的。它有兩半兒,一半兒是老城,我寫的《俗世奇人》《神鞭》《三寸金蓮》這些小說發生在老城。它有獨特的地域個性,水陸碼頭,市井風氣很濃,而且這些地方全說天津話。這是一個天津。還有一個天津是租界裡的天津。租界裡的天津華洋雜處,做洋務的人比較多,全國各地來的富豪比較多,這個地方跟上海的英法租界有接近之處。
寫完了《俗世奇人》,我覺得我把老城不同的人的性格、地域的特點、地方人的逞強好勝基本上都已經寫得差不多了。我是在租界里長大的,這塊土地給我的生命影響很深。如果今後我還能寫,我想好好地寫一兩部書,體現租界這個地方獨有的文化氣質。
南都:您在《藝術家們》的前言裡說“要用另一套筆墨寫另一群人物和另一種生活”,是否也和藝術家們的故事發生在租界而非老城有關?這部小說使用的筆墨和《俗世奇人》相比有什麼不同?
馮驥才:有的作家就是有好幾套筆墨,有兩套筆墨的作家很多。比如說魯迅,魯迅寫《阿Q正傳》《狂人日記》,還有他的雜文是一套筆墨,是魯迅的筆墨。魯迅寫《傷逝》,寫《祥林嫂》是另外一套筆墨,味道是不一樣的。羅曼·羅蘭寫《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套筆墨,他寫《哥拉·布勒尼翁》用的是另一套筆墨。有的作家用一套筆墨寫所有的東西,有的作家就是兩套筆墨。
我一直是兩套筆墨,可能跟我獨特的生長經歷有關係。租界人的氣質跟老城的氣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在租界,在一個洋場環境裡生存的文化,跟地道的、鄉土的、碼頭的生存文化是不一樣的,人的集體性格也不一樣。所以我想,寫兩個地方,用兩套筆墨,更契合這片土地的獨特氣質和韻味。
另外,在文字的運用上有不同的審美,寫作也是一種快樂。《藝術家們》的文筆和《俗世奇人》完全不一樣。比如說,《藝術家們》裡有大量的散文化的東西,比如我寫到美,寫到環境,寫到抒情,就有大量的散文。《俗世奇人》裡絕對沒有散文。《俗世奇人》裡更多的還是中國傳統筆墨,比如《三言二拍》,比如中國的口頭文學,筆記小說,更多這樣的東西。
南都:自上世紀90年代起,您將大量時間投入到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上。二十年後,您再度“迴歸”文學,推出了《單筒望遠鏡》《俗世奇人全本》《藝術家們》等引發廣泛關注的作品。您覺得現在的您在觀念上、技巧上、心境上和80年代蜚聲文壇的您有何不同之處?您對未來的創作還有什麼期待?
馮驥才:我很有意思,我的文化遺產搶救不是學者立場,是作家立場。我是在最好的時候,90年代初,筆最熱的時候,轉向文化遺產搶救工作。因為作家嘛,你受恩於生你養你這塊土地,你一定要把這塊土地的靈魂,你對這塊土地的情感,還有對生活本身的認識寫出來。
可是你太熱愛這塊土地的時候,當這塊土地上的一些文化、一些歷史的遺產、一些歷史的精神與文化財富在時代變化中逐漸瀕危,受到損失,有的快要消亡的時候,你不可能不出來保護它。就像你自己的母親受到了傷害,你就要保護它。
我是出於作家的立場來做的文化遺產保護。做了二十多年,一直做到本世紀20年代,這時候我自己體力不行了,往田野跑得少了,在書房裡的時間多了,我25年左右做文化遺產積累對大地的理解,對地域性和個性的理解,對土地上人們的文化和人們獨特性格的理解要比以前深刻得多。二十多年的積累對人的命運、對社會的認識,包括要愛和要批評的東西,也要多得多,這個東西后來反過來又促使我寫作。
現在寫作,文字方法我就不細說了,我覺得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現在心裡面還有東西要寫。我不是為寫作而寫作,我曾經有一次對記者說過這麼一句話,不是我找的文學,是文學找我來了。我過去知道的同時代的藝術家,我要是不寫,誰也不知道他們。他們找我,就要讓我寫。
我不敢給我自己派的活兒太多。因為我現在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還有些事情要做。國家幾個遺產保護中心都在我的大學裡邊,像古村落保護中心、口述史中心、木版年畫中心……我直接要負責這些工作。還有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另外,從今年開始,我們建立了非遺學的學科碩士點。還有大量的教學培養規劃、教材的編寫等。所以我現在把畫畫停了。現在我寫作肯定要寫。而且正在寫。文學創作對於我是不可遏制的。
答謝辭
感謝兩個字是首先要說的。它並非虛言,而是我個人由衷的表達。
一個有影響的重要的文學獎對於作家來說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使你得到一種肯定,來自專家和學者的肯定;我把評委們撰寫的頒獎詞,看做是給我最好的思想禮物,它有利於我的自省與自我的思辨。有助於我下邊的寫作。
另一個是給我帶來更多讀者的閱讀。作家的作品是在讀者的閱讀中活著的。我一直以為,作品的生命由再版開始,如果一本書不再出版,沒有下一代讀者,作品的生命就會完結。當然,任何文學獎都不可能提高作品的質量,但它可以喚起讀者對我們的作品產生閱讀的興趣。愈有影響的文學獎,這種效應愈大。
所以,我今天是幸運的。
我個人的寫作史分做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始於上世紀八十代的新時期。我做過十幾年的職業作家。此後,由於我認為“搶救瀕危的文化遺產與傳統村落”比我個人寫作更重要,我自願放下寫小說的筆,投身到田野大地中。在長達二十五年裡,我更多的寫作是和消費時代功利主義的反文化的思潮作戰,為建立遺產學的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傾盡全力,還有大量的田野檔案的編制。
近幾年,由於年歲大了,難於再去田野奔波,在書房裡的時間多了,為什麼小說迎頭找上了我?
我的體驗是,一個人一旦與文學擾在一起,就會被糾纏終生,永世難分。你的文學立場就是你生活的立場,你對生活的感受方式常常是文學的感受方式,你的生活思維也融合了文學的思維。
生活,大多是在不經意中積澱下來的。在我二十多年的不寫小說的時間裡,我心中的文學卻在成長。同時,在文化搶救中,我對大地上的人、生活、時代、歷史、文明的理解大大地加深。既是意韻的加深,也是思想的加深。當我再度拿起筆來,便有了“不一樣的人物、不一樣的思考、不一樣的小說”的感覺。當我把這些“心中的文學”寫出來後,我不知道讀者的看法。我曾經的一代讀者離我遙遠,當今的讀者會不會與我彼此陌生?
故此,我把今日南方文學盛典頒發的獎,看做是對我的支援和鼓勵,使我在面對當今這個茫茫的讀者世界時,有了一些信心。作家的天職是為讀者工作。透過文字與讀者一同認知生活與時代、尋找溫暖與光,以及不屈不撓的力量。
為此,再次感謝評委、南方都市報,感謝大家用寶貴的時光傾聽我的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