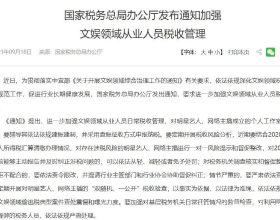雖然蘇軾與辛棄疾的部分隱逸詞均有超脫之氣,但是細細領會,二者的超脫是有差別的,此間的差別以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熟爛之語概括再確切不過:“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具體地說,在蘇軾的隱逸詞裡,他是以一個失意文人廣博的胸襟體味著人生,咀嚼著苦難,在體味與咀嚼之中得到的往往是哲理式的感悟,而他那原本應該洶湧澎湃、飽含痛苦的感情也在這個過程中變得如秋水般平靜,這種平靜的感悟,使他的詞作帶有超曠的氣質。
而辛棄疾的隱逸詞則不然。在辛詞中,失路英雄的悲憤令他每每以一種沉痛乃至絕望的心態發洩心中的感情,這種宣洩如火山熔岩般熾烈,就算詞中偶有曠達之語,也絕不似蘇詞那般波瀾不驚,激盪的感情使他的詞作具有雄豪的風格。再以下列例項分析此問題:
蘇軾的《浣溪紗》一首:
遊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此詞元豐五年(1082)作於黃州。詞前有“遊薪水清泉寺,溪水西流”的小序,可知這是詞人遊薪水城外清泉寺,因見西流之蘭溪,有感而作。上片三句寫遊歷見聞。蘭溪中的幼芽剛剛鑽出泥土不久,尚且短短地浸在溪水之中;松林間的沙道在頻繁的雨水沖刷下,潤澤而潔淨:透過瀟瀟暮雨,不時傳來杜鵑鳥的聲聲啼叫。下片三句為即景抒情。俗話說,“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時”,漢樂府《長歌行》中又有:“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以花開花落及流水東去之不可逆轉,表達人生易老、韶華難留的無可奈何。白居易的《醉歌》:“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緩系未穩,鏡裡朱顏看已失”,也是感嘆時光之飛逝,生命之短暫。而此首《浣溪紗》一反以往的悲觀論調,既然悠悠東去、永不復返的江水,都有向西而流的可能,人生怎麼就不會再度擁有青春呢?雖然生理上會一點點衰老,可是精神上要始終保持年輕的狀態,絕對不可以作《醉歌》之嘆!
蘇軾這位可以經天緯地的才子,處於也許永遠不見天日的貶滴生涯之中,竟能以明麗秀美的蘭溪風光為契機,將自己的滿腹心事化作樂觀豁達的理性議論,其心態之灑脫爽朗,實屬難能可貴。再看一下辛棄疾的《沁園春·再到期思卜築》與之有何區別:
一水西來,千丈晴虹,十里翠屏。喜草堂經歲,重來杜老,斜川好景,不負淵明。老鶴高飛,一枝投宿,長笑蝸牛戴屋行。平章了,待十分佳處,著個茅亭。
青山意氣崢嶸。似為我歸來嫵媚生。解頻教花鳥,前歌後舞,更催雲水,暮送朝迎。酒聖詩豪,可能無勢,我乃而今駕馭卿。清溪上,被山靈卻笑,白髮歸耕。
此詞作於紹熙五年(1194)秋冬之際,為辛棄疾再次到期思選地造屋時所作。詞的上片首先大筆勾勒了期思的地形與景色:“一水西來,千丈晴虹,十里翠屏。”自西而東的河流,橫跨晴空的彩虹,屏風般的山嶺,足見此地地勢之起伏,風景之優美。而句子之工整,氣勢之磅礴,大有包舉全篇之氣概。接著著重說明了自己來此地的意圖。詞人是要像杜甫重歸草堂、陶潛游覽斜川那樣隱居期思,遊賞美景,並借用《莊子.逍遙遊》中“鶴鶉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之句,將自己比喻為高飛的老鶴,棲息時不過只須一枝而已,嘲笑那些為家業所累之徒,只要尋個十分中意的地方,修建一座茅舍,他便得其所在了。從此可見詞人心胸之廣闊。詞的下片首先敘述了寄情山水的無窮樂趣。
詞人望著那高峻的青山,似乎覺得因為自己的歸來,他們憑添了幾分嫵媚似的;還有山花野鳥,行雲流水,也為他前歌後舞,朝飛暮送,好不熱鬧。作為酒中的聖人,詩中的豪傑,詞人自忖從今而後若是能駕馭這青山秀水,也算是人生一大樂事,愈顯其性情之豪邁。可是,詞章結句則陡然一轉,借山靈譏笑自己白髮歸耕一事,抒發自己不願就此退守田園的心情。此首作於詞人第二次被迫隱退之際的《沁園春》,不僅僅表現為爽朗與豁達的情調,豪放之中更蘊涵著詞人政治失意的巨大悲哀。可能是性格的不同,也許是學時的差異,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或者還有更加複雜的原因。
總之,蘇軾與辛棄疾那些具有超脫品質的隱逸詞是不一樣的。從以上對具體作品的理解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遭遇不平的蘇軾內心肯定也是不平衡的,但是他能夠將自己的心情調整至平衡狀態,從而使《洗溪沙》之類的詞作仍可以寧靜平和地出之,顯示著其人其詞的曠達。而辛棄疾的內心更是不平衡,他只能任由感情暢快淋漓地噴湧,卻不能對內心激烈的動盪加以左右,他的隱逸詞也只能至似《沁園春》那種豪放為止,無法達到超曠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