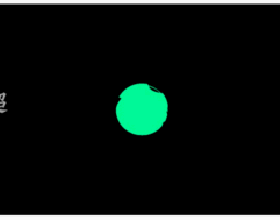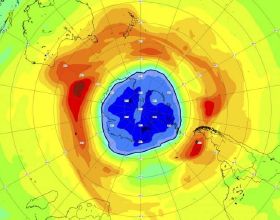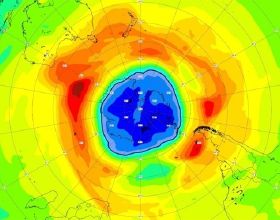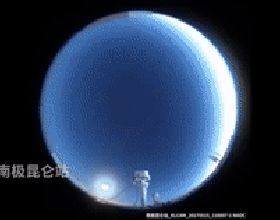今天讀了餘華早期的一個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心靈受到很大的震撼。
這部小說最早發表於《北京文學》1987年第1期,是餘華的成名作。
一 、小說簡介
小說選取的故事是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初次出門遠行所經歷的生活片段,寫了成長中的挫折與失敗。它表達了人生是複雜而曲折的,在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遭遇到種種的艱難和挫折。
餘華出生於 1960年,是浙江海鹽縣人,祖籍山東高唐縣。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先鋒文學代表作家。早期著名作品有中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鮮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煙》《難逃劫數》《河邊的錯誤》《古典愛情》《戰慄》《在細雨中呼喊》等;90年代以來有著名長篇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
在餘華早期創作過程中,作為一個先鋒文學作家,他幾次撰文說明自己的創作主要受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影響。
餘華說:“在我看來,川端康成是文學裡無限柔軟的象徵,卡夫卡是文學裡極端鋒利的象徵。川端康成敘述中的凝視縮短了心靈抵達事物的距離,卡夫卡敘述中的切割擴大了這樣的距離; 川端康成是肉體的迷宮,卡夫卡是內心的地獄;川端康成如同盛開的罌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進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奮和痴呆。”
“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這理解成命運的一次恩賜。”“我要感謝卡夫卡,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
餘華在談論卡夫卡對他的“解放”時無一例外的提到了一部作品,就是《鄉村醫生》。他發現原來文章還可以這樣寫:“他想讓那匹馬存在,馬就存在;他想讓馬消失,馬就沒有了。他根本不作任何鋪墊。我突然發現寫小說可以這麼自由。”
餘華的早期小說注重與對人的存在的探索,在這種探索中,其小說筆調以冷酷著名。他以一種冷靜的筆調描寫死亡、血腥與暴力,並在此基礎上揭示人性的殘酷與存在的荒謬。代表作品有《四月三日事件》、 《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難逃劫數》等。
在這些小說中,在表現人世的冷漠與殘酷時,餘華刻意追求超然物外無動於衷的冷峻風格,貌似超然而冷靜的敘述風格來源於作家與現實之間的一種緊張關係,他要與他筆下的人物及其代表的人性的殘暴與殘酷的一面保持距離。不論善惡,他都要保持一種理解之後的超然,並由之產生一種悲憫之心。象高居天穹的上帝,洞悉塵寰的眾生靈,心懷悲憫,卻不加干預。
後來,進入90年代後,在先鋒文學的大逃亡中,以《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為代表,餘華小說風格來了一個大的轉變:在描寫底層生活的血淚時繼續保持了冷靜的筆觸,但是加入了悲天憫人的因素,這些都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先鋒小說之“先鋒”主要強調在不再重視 “寫什麼”,而是著力探索“怎麼寫”。其中,餘華是“先鋒小說” 的領軍人物。
莫言曾經當眾這樣評價餘華:“當代文壇上第一個清醒的說夢者。”《十八歲出門遠行》就是描寫了一個流動、虛無縹緲的、真實的、殘酷的夢。下面就讓我們進入這部著名的說夢小說吧。
二 、人物大舞臺
小說涉及到人物從主到次,有“我”,司機、山民、父親等。
1.對世界充滿愛的“我”
作為小說的主人公, “我”天真單純:對世界充滿愛,“所有的山所有的雲,都讓我聯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著它們呼喚他們的綽號”。
“我”叛逆輕狂,做事沒有分寸,在招手搭車而汽車並不停留時,想拿石頭砸汽車,甚至想躺到路中央去攔車。
後來終於攔到了車,“我”學著像成人一樣給司機遞煙,司機接受了煙,我就認為這就代表他接受了“我”,這個細節顯示了“我”只是一個在年齡上邁入成年而在心理上卻是一個充滿童真的模仿成人的孩子。
我坐著司機的車出發了,後來汽車故障,拋錨了。一群山民來搶蘋果。“我”奮不顧身出來阻止;當事者司機卻看笑話似的袖手旁觀;當“我”被山民揍得遍體鱗傷倒地不起時,司機卻偷了“我”的揹包與搶劫者一起離開。這些荒誕的事情就像一顆炸彈,將“我”原本的價值觀摧毀殆盡。“我”在十八歲時懷著熱情和夢想第一次出門遠行,現實世界卻給“我”當頭一棒。
2.作為看客的司機
司機作為一個成年人,面對氣勢洶洶的搶劫者,他選擇了明哲保身。沒有絲毫抗爭的行為和動作,因為這樣的事他以前遇見過很多次。最開始他也反抗過,但是最後受傷的都是自己。今天的他很明白,在這樣一個暴力群體下,他弱小的抗爭是徒勞無力的,搭車客“我”奮不顧身的幫助,在他看來也只是以卵擊石、極為可笑。
結果是司機雖然損失了蘋果和汽車,但是卻保全了自己;當“我”被打得遍體鱗傷,司機已搖身變成了看戲的人,一個能在“我”身上獲得補償性滿足感的看客。
最後司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拿了“我”的包與搶掠者一起離開。他發現在“我”面前他是一個勝利者;在“我”身上,他獲得強者和保全者的滿足感。
所以說,司機這種人是一類擁有看客心理、世俗化、愚昧麻木、欺善怕惡、圓滑世故的病態群體。這也是當年魯迅針砭痛罵的人。
3.暴虐的山民
山民是暴力的代表。山民看見拋錨的汽車,然後就像參加日常生產勞動一樣,有條不紊地搬運起蘋果來。“我”上去阻擋,結果被狠狠打了一頓,就連原本天真可愛的小孩也充滿暴力,“幾個孩子朝我擊來蘋果”“拿腳狠狠地踢在我腰部”。這些人就像野蠻人一樣暴力無情。在一批搶掠者之後,又來了更大一批搶掠者,搶完了蘋果然後開始拆卸汽車,把汽車大卸八塊,最後汽車“遍體鱗傷地趴在那裡。而我也被揍得遍體鱗傷,“每動一下全身就劇烈地疼痛”。
4.溫情的父親
十八歲生日那天父親給了我一個紅色書包。然後在我後腦勺上拍了一下,於是我就像一匹小馬駒歡快地衝出家門。開始了一場旅行。
父親讓“我” 出門遠行,但是他好像不瞭解世界與“我”。 雖然父親沒有與惡為伍,是一個用心良苦,充滿溫情的人,他就像陰天裡的一縷陽光,給人溫暖,照亮黑暗。同時還承載著現實世界裡所有父親對兒子深厚的愛。
在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領路人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充當青少年成長中的指導和教誨的角色。而這部小說中,“父親”完全沒有發揮一個“領路人”的作用。他只是給我準備了紅書包,裡面裝著衣服和錢,還有食品和書,但是他卻沒履行一個領路人的角色。在我十八歲生日這天,在“我”後腦勺拍了一下,把“我”拍出了家門,任由對世界一無所知的我開始了一個一場危險無比的旅行。
從這一刻起,“我”一下子被拋入現實社會,開始孤獨地面對陌生世界,“我”在路上漫無目的,沒有方向。因為“我”出發前就沒有預設的目標和來自成人的引導。
當“我”終於搭到車坐上去,雖然汽車是向自己來時的方向行駛,但“我”仍然覺得舒服。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預設方向。
因此說“父親”的形象代表著一個不可靠的許諾,一個不得不被戳穿的美麗的謊言。揭示某種特定經驗正規化的虛假和不可靠,並且鏡照著一種新的自我意識的浮現過程。
小說中的“紅揹包”象徵著革命傳統,象徵“父親”的意識形態包袱,也構成了“我”曾經擁有的身份。最終“紅揹包”被神秘而無信的司機搶走,象徵青年所接受的成長教育的悖論和父輩的理想主義在“我”對於背叛與暴力的直接體驗中完全失去了可信度。因此說,在社會及個人前途不可知的情況下,機械般的形式教育和片面性的思想教育,是導致“我”過渡到成年階段必須付出巨大痛苦的原因之一。
三 、荒誕、漂泊的主題;隨時可能暴發的暴力
小說透過剛剛年滿十八歲的“我”第一次出門遠行的經歷,走路、搭車、被搶、在車裡過夜等等故事情節,表達了“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感覺——冷漠、暴力和荒誕。 在這場旅程中,到處充滿不可知的危險和隨時可能暴發的暴力。
在這個六千字組成的有限空間裡,出門是一種象徵,“我”就像一艘毫無方向的船,沒有方向。小說裡寫到當我終於搭上車出發時,汽車的方向是我來時的路,但我根本不在乎。我在路上漂泊,旅館只在遠處半睜著眼望著這一切。到結尾處,汽車恰恰成了旅館。最終,我只能蜷縮在“汽車”受傷的心臟裡抵擋外界的風寒。這裡遍體鱗傷的汽車和遍體鱗傷的我互為映象,其象徵含義是,沒有人可以依靠,唯有自己可以給自己溫暖。
因此說,這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關於啟蒙與認知的寓言性故事,即成長小說:透過一場本該是無憂無慮的旅行,“前面是什麼” “你走過去看吧”——然後變成了一個考驗過程——最終呈現一個遍體鱗傷的結局。
“我”的出門遠行,完成了一個發現自我的現代主義旅程:殘忍與暴力。經歷這樣一個變故的“我”是極有可能摒棄父輩留給我的神話遺產的。
人就是這樣在受騙的經歷中完成他十八歲的成人禮的。“我”對世界充滿愛的幻想破滅了,“我”迎來了成熟的成年:一場血的教訓最終助“我”完成最終的蛻變;“我”由一個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少年,在成年人的惡和和生活的教訓面前,終將變得見怪不怪,對人性之惡視若無睹。
這樣一部現代性成長小說,和傳統中對於成年的定義是不一樣的。傳統的成年都是經由漫長的“學徒生涯”來完成。“學徒生涯”是一個緩慢而明確的通向父輩家業的必經之路,通常是小徒弟在一個技術高明、處事精明練達的師傅的指導和帶領下,不停學習為人處世的交際能力,鍛造高超的業務技能,最終學成一身武藝,最終擁有幸福的婚姻、成熟的個性、適當的社會化、穩妥的步入成年------最終收穫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而現代性成長小說則是對社會空間進行充滿變數的探索:遊歷與冒險、迷失與幻滅。就如這篇《十八歲出門遠行》所描寫的。這部小說的獨特性表現為,在著力表現世界的冷漠與非人力量的同時,透過個人所受到的創傷而拼湊起一個無情冷漠的世界。
四、 風格特色:獨特的敘述方式和語言表達
這篇小說敘述的口吻彷彿是成年後的“我”回憶過去的親身經歷,含有超然與反省的語調。關於小說採用的形式,作者餘華是這樣說的:
——“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後,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誠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真實。”
下面摘抄幾個金句和大家一起欣賞。
——“我走在這條山區公路上,我像一條船”;
——“我就這樣從早晨裡穿過,現在走進了下午的尾聲,而且還看到了黃昏的頭髮”;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處總在誘惑我,誘惑我沒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個高處,中間是一個叫人沮喪的弧度。儘管這樣我還是一次一次地往高處奔,次次都是沒命地奔”;
——“雖然汽車將要朝我走來的方向開去,但我已經不在乎方向。我現在需要旅店,旅店沒有就需要汽車,汽車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