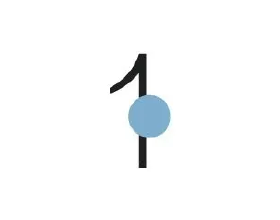清晨起來,天有些冷,季節又一次似乎相同似乎略異地輪迴已到了“北風捲地白草折”的季節。不過現在的時令再覺得冷,也沒有小時候冷了,那時候凍得手腳皸裂、一臉的鼻涕眼淚穿的十分臃腫仍覺得冷,那時的冬天真是天寒地凍,現在再怎麼冷也覺得不那麼冷。
前幾日下的鋪天蓋地的靡靡大雪隨著溫度的上升,已漸次融化,或許偶爾在路邊、在草叢、在溝坎還能找到一些隱隱雪兒的蹤跡,大自然的妙筆神畫之於繁華喧囂嘈雜的城市裡瞬間少了些自然嫻靜的情趣,有些無奈。穿行於螞蟻大軍覓食的行列裡,清冽的陽光下駐足於腳下川流不息的天橋上,孤寂地望著遠方鱗次櫛比的混凝土灌注的叢林,顧影自憐不禁慨然道:“浮生如夢,為歡幾何?”
侄女給了我本清末民初吳克岐的紅學研究著作《懺玉樓叢書提要》,書籍是手書影印豎版無句讀的、我邊讀邊標點邊查字典,十分晦澀的一字一句啃著。書籍內容詳實豐富耐人久讀,別說考證了,僅書籍抄本的楷書筆致秀勁以及輯者的學識涵養就使人折腰。其中有一段描寫“浮生如夢”的,我咀嚼了幾遍,頗有感觸:“夫人生一大夢也,夢中有榮悴、有悲歡、有離合,及至鐘鳴漏盡,遽然以覺,則惘惘然同歸一夢而已。上之遊華胥、熙九齡,帝王之夢也;燕鈞天摶,楚子侯王之夢也;下而化蝴蝶、爭蕉鹿、宦南柯、熟黃粱、紛紛擾擾、離離奇奇,當其境者,自忘其為夢,而亦不知其為夢也。蘭皋居士,曠達人也,猶憶為孩提夢、作遊戲夢、肄業夢、遊庠夢、授室夢、色夢、養夢、居憂夢、續娶夢、作宰官臨民斷獄夢、集義勇殺賊既而夢,休官夢、復職夢、居林下迢迢長夢、歷一花甲於茲猶復夢,夢然夢中說夢,而不知其為夢也。”是呀,走過這個世界的生靈都知道人生如夢,是海市蜃樓般不實的,可一代一代的芸芸眾人們還依舊執迷不悟地在這春秋大夢裡夢中說夢,一味裝睡就不肯醒來。
“生於繁華,終於淪落”的曹雪芹在歷盡人生顯貴與凋敗、雍容與卑賤、順達與阻險之後“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寫成的鉅著《紅樓夢》,雖千人千面百事百態紛繁複雜又命運前定,不可逆轉。曹公一生的血淚經歷用如椽大筆蘸著亦濃亦淡翰墨寫了一部比之於“黃粱一夢”的紅樓大夢,以期叫醒呼呼酣睡的世人,可沒幾個人讀得懂,可惜了曹公一片心血。
大凡讀過《紅樓夢》的國人,大概誰也不會忘記《紅樓夢》也就是《石頭記》裡那一僧一道中的瘋癲跛足道士,更不會忘記他那堪稱蓋世警言的、度化執迷不悟的世人《好了歌》。原著如是寫道:
甄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柺杖掙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癲落拓,麻鞋鶉衣,口內念著幾句言詞道: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槓,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這跛足道人本是曹雪芹虛構的一個道破天機的人物,藉助於他的“大觀”眼睛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慾望無窮、沽名釣譽、巧取豪奪的泥濁不堪的世界,甄士隱更是為《好了歌》作了直接精彩的註解,一句“陋室空堂”揭謎這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群舞臺,演的不過是一幕幕荒誕鑼鼓鐃鈸的鬧劇:“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奔波一生繁忙一世到頭來不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可惜了這一世人身。
世人也就是如此奇怪,還考證跛足道人這在人世間確有其人,有就有吧,本就“神仙本是凡人做”,沒什麼奇怪的。《荊州府志》如是記載:好了道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姓氏。貌體古怪,椎結芒服,性嗜酒,飲數石不醉。善為巧法,言禍福奇中,能使鬼。正德間(明武宗年號,公元1506-1521年),常來宜都(今湖北省西北部)山中。叩其姓氏,笑而不答,但點首曰:“好了。”人以故呼為“好了道士”。居無幾,大疫,道士遍詣諸疫者,呼曰:“爾曹急去,毋困此一方人也!”疫遂止,道士亦去,莫知所之。兩位道士一前一後,均與“好了”有關。在賈瑞“邪思妄動”、“非藥可醫”之際,跋足道士曾手持“鳳月寶鑑”前來給賈瑞治病,在寶玉、鳳姐“魔法叔嫂逢五鬼”之時,這頭陀和尚與跛足道人又一齊出現,自然“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兇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如此看來,跋足道士也是“能使鬼”之輩。至於“貌體古怪”、“言禍福奇中”,二人也有相近之處。考證的有鼻子有眼十分詳實,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如此也挺好。
記得有一次和女兒聊天,敘述家庭的興衰以及我這一生的成敗利鈍境遇,豈料女兒一臉疑惑地問我:“老爸,你是來渡劫的嗎?”
“……”頓時,我一臉蒙圈。
我只是一個愛讀閒書的寂寞孤獨者,無意於研究考證什麼,但凡著作者的一字半句“於我心有慼慼焉”,便覺得十分受用。自己的一絲幽魂不知從哪個星球降誕到這個世界,由此便昏昏沉沉由夢入夢了,一直到了過了知天命之年,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活成自己想要塑造的樣子了,便稍稍迷迷糊糊有些想醒來的意識,但睡眼朦朧睜不開彷彿依舊在混沌般夢寐之中,不知何時真能覺醒。想來,中國的老祖先真是智慧,在造字的時候把覺悟的覺(jué)與睡覺的覺(jiào)做一個字,真是玄機無窮,只能自己紅塵裡歷盡千難萬險千辛萬苦淬鍊參悟了。
“嗨,走路看著點,天寒路滑。”一邊沉思一邊下天橋,只聽得有人招呼一聲,略微有些驚醒。是啊,天寒路滑走路得小心著點兒,小心點兒…… “春日才看楊柳綠,秋風又見菊花黃。榮華終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 我本出身寒門並非生於繁華,但一樣無法更改地終於淪落,如此便如此!走,向前走,向著有光的地方走以至於融化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