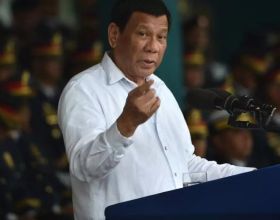思想主張
沈鈞儒清末主張立憲救國,認為立憲即改變清朝封建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政治,讓人民有參政的民主自由權利。
辛亥革命後,他本著民國主義在民的精神,反對封建軍閥統治,要求貫徹民主精神,厲行立憲政治,參與了“天壇憲草”和浙江自治省憲的擬定工作。在領導救國運動中,他參與制定的救國會政治綱領中,明確提出民主制度的確立,是各黨各派徹底合作的基本條件;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是聯合戰線絲毫不能讓步的要求。
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始終認為抗日與民主不可分,要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必須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參戰,充分發揚民主,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他針對抗戰後國民黨繼續實行專制、壓制民主、破壞法治,先後在國民參政會上兩次提出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獲得許多參政員的聯署支援。
他和各抗日黨派參政員一道,發起民主憲政運動,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保障人權和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為了爭取實現民主憲政,他和一些中間黨派負責人共同發起,成立了旨在促成實施民主憲政的統一建國同志會,隨後進一步發展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沈鈞儒和救國會是共產黨在爭取政治民主化鬥爭中的忠實盟友。
抗戰勝利後,在沈鈞儒的領導下,救國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其政治綱領提出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他參與創辦的《民主生活》週刊,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認為當前一切問題的癥結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筆來反映人民的公意,發揚民主精神,實踐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國民黨宣佈為“非法團體”遭取締後,他潛離上海赴香港主持召開了民盟三中全會,領導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義方面”。
反對人治,主張法治,是沈鈞儒法學思想的核心。沈鈞儒認為,法制健全與否,是否實行法治,是國家強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韓非的話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北洋軍閥統治下,他長期參加政學會活動,是因其政綱對政治取穩和改進主義,強調發揚民主與厲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專制之積威,唯法治可以納庶政於軌物。”與自己的理念相吻合,他說:“歐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國式政治之精神在人治。”“吾國政府素重人治,與歐美之一切歸納於法治者迥異,政治之所以不進步,此實一大原因。”
認為當今中國是無法無天,武人干政,軍閥禍國,只有建立法系,實行法治,結束人治,才是弭亂致治之道。上世紀30年代,他針對國民黨當局罔顧法治,踐踏民主,非法拘禁愛國人士的白色恐怖統治,倡導冤獄賠償運動。發表宣言說:“‘堂上一筆朱,階下千滴淚。’此種至可慘痛之現象,竟存留於二十世紀之中國,則斯民之不幸,果為何如?”並制定冤獄賠償法草案送呈國民黨中央採用,要求建立冤獄賠償制度,以保障人權,獲得廣泛輿論的支援。
冤獄賠償運動是當時整個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法制史上一頁有意義的篇章。40年代,他撰文批駁國民黨政府頒佈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等法令。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建立和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殫精竭慮,使法制建設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此外,沈鈞儒從小接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濟世救民的優良傳統,有著良好的道德修養。他一生“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潔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樂於助人,重視家庭,愛護子女,對後輩循循善誘,是青年的良師益友,為世人所稱道,這更是值得我們繼承的一份精神遺產。
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1931年, “九·一八”事變牽動了沈鈞儒那顆憂國憂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國運動的洪流之中。並於同年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多次上書南京國民黨中央。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助長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愛國群眾。沈鈞儒等人又發起組織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在“九·一八”五週年當日,他不顧當局禁令,帶頭率幾千人上街遊行示威,不畏軍警的鐵棒刀槍,不理會蔣介石的點名警告。
10月,又主持了魯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參加的送葬禮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及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上發表講話、以救國會名義致電張學良等國民黨將領、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罷工等等活動都觸怒了國民黨反動派,結果沈老先生和李公樸、鄒韜奮、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一同被捕,成為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在獄中,沈鈞儒先生被公推為家長。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援、互相鼓勵,堅決不寫悔過書,堅持愛國無罪。在法庭上,“七君子”義正詞嚴,駁得檢察官啞口無言,狼狽不堪。
沈鈞儒雖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卻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審訊退庭後,他感慨萬千,以詩抒懷:我不要這種勝利!眼看地圖變了顏色;六千萬同胞淪亡在深淵之底,我們如果還有一些人氣,那裡有心思來與自家人鬥鼠牙,爭蟲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禱著這一天:能把我的血,飛灑到關外數千裡與天無際的白雲上,把我們的骨,深埋在那一邊的土裡,這才是我們的勝利!也是我們民族的勝利!國家的勝利!我再也不想要其他的勝利!他的詩表現出一個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堅定信念。
“七君子”的愛國行動得到了舉國上下的支援,宋慶齡等知名人士也紛紛發表宣告。在全國各方面的壓力下, 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不得不釋放了他們。當他們走出獄門之時,各界群眾聞訊趕來迎接,口號聲、爆竹聲高入雲霄。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 “可以告慰於大家的是,我們出獄與入獄時一樣,主張沒有變更,我們決不改變我們的宗旨,決定和過去一樣,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線。
宣傳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春,梁啟超和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正值清廷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訊息傳出,群情憤慨。梁啟超受康有為之命,“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四月初八日,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邀集10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從而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
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重要助手,不僅協助組織會議,聯絡人士,而且還撰文謄錄,起草奏書,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不久改為《中外紀聞》),梁啟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在鼓動輿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那些士大夫“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梁啟超在辦報過程中也得到了鍛鍊,顯示了才華。他那高度的熱情和出眾的能力,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梁啟超就從一個人微言輕的普通士子,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啟超應邀前往主持筆政。在主編《時務報》時期,他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啟超在這些文章中,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
他還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議會制度,竭力宣揚民權論,痛駁“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的封建說教,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把歷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呼籲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並且強調,這是維新變法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苟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於文明耳。”
梁啟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連嚴復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直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由於梁啟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啟超的名聲也隨之日重。
維新時期
梁啟超全家變法理論的宣傳,有力地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開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對維新運動人物的不滿和嫉恨。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授意汪康年進行干預,力圖控制《時務報》,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啟超難以與其爭,遂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離滬赴湘,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
由辦報改而教學,條件和環境都不同了,但梁啟超並沒有放棄宣傳工作。在講學過程中,他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特別是在批答學生札記時,梁啟超往往借題發揮,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他甚至大膽宣佈,“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是民賊也”。這些激昂的言辭,對於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錮的青年學子來說,猶如是出征的戰鼓,激勵他們投身到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歷史洪流中去。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非常險惡的局勢。清廷的腐敗和無能,透過這次戰爭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各國趁火打劫,力圖擴大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出兵侵佔膠州灣,康有為趕到北京,積極組織救亡活動。梁啟超由於在湖南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也於光緒二十四年二月返回上海,隨即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於三月初來到北京,跟隨康有為奔走呼號,決心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儘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撰文演說,呼籲要使全國民眾“鹹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梁啟超反覆強調,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梁啟超的作用和名聲也越來越大。在“百日維新”期間,有關新政的奏摺、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五月十五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賞六品銜,並讓梁啟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逃出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時,他一度與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往來密切,並試圖聯合立會,後因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但是,梁啟超與革命派畢竟不是同路人,他繼續追隨康有為,堅持改良立場。
為了控制、利用輿論,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啟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為改良活動搖旗吶喊。他竭力宣揚“光緒聖德”,說什麼“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
密謀反袁
民國三年一月,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後僅三個月,就下令取消國會。二月,熊希齡在內閣倒臺。儘管袁世凱改任梁啟超為幣制局總裁,但這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位,實在難以引起梁啟超的興趣。十二月,他辭去幣制局總裁之職,攜家遷往天津。
以後,袁世凱又任命梁啟超為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啟超都推辭未就。在此期間,梁啟超與袁世凱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既不滿於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又對他寄予希望。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和企圖抵制自為的行徑,梁啟超是反對的。
由“二十一條”引起的政治風潮剛剛開始消歇,袁世凱就加快了恢復帝制的步伐,公開打出了復辟帝制的旗幟。只是到這時候,梁啟超才對袁世凱完全失望。面對全國已經蓬勃開展起來的反袁鬥爭,梁啟超恐為“牛後”,終於發出了討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啟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
與此同時,梁啟超又與蔡鍔密謀,積極策劃武力討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在雲南組成討袁“護國軍”,梁啟超於民國四年底從天津來到上海。他與蔡鍔等人函電往來,幫助護國軍擬定計劃,起草文告;又與廣西都督陸榮廷秘密聯絡,促其獨立。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梁啟超應陸榮廷的邀請,繞經香港、越南趕到廣西,直接參加護國運動。五月六日,軍務院在廣東肇慶成立,梁啟超任副軍兼政務委員長。在職期間,軍務院的佈告、文電大都由梁啟超親自執筆。
護國運動以後,梁啟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之中了。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之後,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主持國務院事務,成為新的實力人物。梁啟超很快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
他在給南方各都督司令的電文中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否則“大局將不可問”,要他們協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佈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復會,並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之後,梁啟超便主動撤銷軍務院,以避免與北方對峙而發生衝突。在梁啟超的一再催促下,軍務院於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政治主張
改良思想
梁啟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隨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
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但是這種居於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
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乾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佈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後,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徵,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於技窮。
復歸傳統
民國七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經過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啟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來,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
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昂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啟超從一箇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箇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迴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復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賦稅思想
梁啟超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徵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