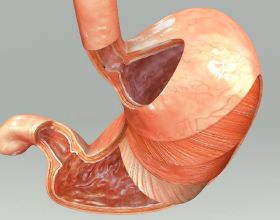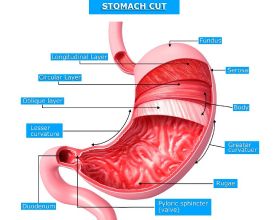我們知道,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造成人口銳減,同時也引發了人們精神上的突破,歐洲的百姓,主要是上層統治者,開始突破宗教、神性的束縛,發現人性,解放人性,開始了文藝復興,也逐漸結束了黑暗的中世紀。
相似的,中國漢末三國之間,災害頻繁,爆發了時間持續長,影響範圍大的幾場瘟疫,現實的災難也刺激了人文創作,激發了人文精神的興起。
漢末瘟疫產生的背景
《續漢書·五行志》記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後漢書·桓帝紀》記載,“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續漢書·五行志》有,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有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正月,大疫。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桓靈之際”的黑暗,絕不僅是因為親小人,遠賢臣而已。在天威之前,人力是如此渺小。自公元二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原一帶瘟疫頻繁,此後天災人禍頻發,人民除了顛沛鋒鏑之間,流離海內之外,還要遭受疫病的侵襲,以至“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更令人絕望的是,建安時期,瘟疫的爆發更加猛烈。據學者統計,從靈帝時期至曹魏初期,瘟疫的發生頻度從近三年一次上升到近一年一次。而瘟疫之後,人口也隨之銳減,中原戶口,十不存一。當然,不能排除動盪之際隱瞞戶口,或者良轉為賤的現象,但瘟疫絕對是人口銳減的一大原因。
瘟疫的產生,首先是天災。據竺可楨先生研究,東漢到三國時期,是中國氣候逐漸轉寒冷的階段,氣候寒冷,則“比歲不登”,極端天氣多發,森林、河流(黃河)等生態環境惡化,人民因而飢寒交迫,社會矛盾激化,此為內憂,引起北方少數民族的內遷、寇邊,此為外患。
極端天氣的出現、持續的寒冷,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瘟疫的傳播,如造成自然災害,而“大災之後有大疫”。
據學者統計,從東漢安帝永初元年至獻帝建安末年,共發生水災34次,旱災35次,蝗災19次。而那恰恰是瘟疫的溫床。
其次是戰爭等人禍。軍營生活條件艱苦,人多聚集而衛生條件堪憂,這有利於瘟疫的傳播;戰爭使人口大量死亡,死人不能及時處理或處理方式不當,更使瘟疫橫行;戰爭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流動,於是一旦防護不當,瘟疫即擴散開來。“自頃已來,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這樣的慘狀,卻隱藏著瘟疫擴散的極大隱患。
另外,還要考慮到戰爭破壞了原有的社會救濟。東漢國家強盛時期,如有瘟疫,尚且可以中央排程賑濟地方,地方豪富或邀名或謀利,也總要擔負起救濟百姓的隱形義務。但中央失權,百姓流離之下,想要聚集足夠的力量維持以往的秩序,代價就太大了。
最後,也要歸咎於當時醫學水平的限制。張仲景正因為看到家族因疫病而凋敝,才沉寂作《傷寒雜病論》,成為一代醫聖。醫學水平的限制使瘟疫瀰漫卻不可遏制,只能等它“盛極而衰”。
瘟疫造成的影響
如題中所說,漢末大疫影響了建安時期人文精神的興起,因此這一節只論瘟疫造成的除精神文化以外的直接影響。
1、瘟疫使當時中原人口銳減。
疫病使人口銳減的現象,屢屢見於當時的文學創作和文字記載中。張仲景提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時居其七。王璨嘆息“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而他本人也稍後因此而死,是文學史上的一大損失。《後漢書》則稱,桓帝時期“比歲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困,司隸、豫死者什四五”。
若將這些泛泛的感嘆化為具體的數字,則更是觸目驚心。《晉書》記載桓帝永壽三年的全國戶口為一千餘萬戶,五千六百餘萬口。三國時期數字較為散亂,計算複雜,暫且不論,但到西晉統一初期,這個數字變為“晉戶有二百七十七萬。”
從漢季到西晉,三國之間疫病瀰漫,戰爭頻繁,人口勢必不會有太多恢復的機會,但這種落差仍然是驚人的,其中固然有戰爭的原因,但瘟疫不可或缺。
2、瘟疫影響到當時戰爭的發展。
以著名的赤壁之戰為例,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戰中失敗,原因很多。其一是北人不習水戰,其二是千里來戰,士兵疲敝,其三是曹兵中有新附之人,未能歸心,其四就是瘟疫。《三國志》記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士卒飢疫,死者大半”。裴注因而嘆惋,“天實為之,豈人事哉?”
因瘟疫影響到戰爭程序,遠不止六朝之間。秦皇興兵南越,士卒多有水土不服,瘴氣橫行軍中,使秦兵蒙受莫大損失,甚至間接加速了秦軍的滅亡。另外,如前所說,戰爭使人們大量死亡,一旦不能及時處理死屍,加重疫情不過在旦夕之間。
建安時期的人文精神
1、建安時期的文藝創作
漢末到建安時期,瘟疫橫行,戰亂頻繁,人們無論貧富貴賤,不分男女老幼,都時刻面臨著生死的威脅。這反映到文藝創作上,就是兩種傾向。一種是人生無常,長吁短嘆,一種是及時行樂,奢靡無度。前者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後者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後來到東晉,王羲之在他著名的《蘭亭集序》中感慨“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東晉之有一死生、齊彭殤之人,蓋人世無常,離亂如故,與建安時期相似罷了。
當然,在如此悲觀的氛圍中,仍不乏奮發之人。既然悲慘世界中有人忙於悲泣、有人用虛度光陰、嗑藥行樂麻痺自己,那麼自然也有人知人生之短暫而要及時建功立業,以求不朽。然則他們並不耽於詩詞歌賦之間,留下的作品相對少。
然而,無論是哀嘆還是樂觀,文藝創作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人文精神的興起。即,這一時期的人們自我意識開始覺醒,人的價值被發現、被重視,作品中更多了對“人”的關懷和對人生的思考。不能說這全賴瘟疫,但瘟疫、戰亂等造成的整體氛圍確實是促使人們反觀自身,進而個性覺醒的一大原因。
2、建安時期的社會宗教
考慮到此時恰逢三教並立時期,而戰亂之際儒家衰落,佛道獲得大發展,建安時期的社會宗教,這裡只論佛道。
佛教在西漢就已經傳到了中國,但到漢末魏晉之間才逐步融入中國社會,獲得更好發展。佛教主張萬物皆空、形滅而神不滅,認為現實的折磨與苦難,既是自己前生所作罪孽的懲罰,同時也是來生平安富貴的保障,因此,它要求教徒用贖罪的態度去認可和承受現實的種種折磨與苦難。
這恰好迎合了建安時期的世情心態。但也要注意到,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在初期,還沒有很好的本土化,因此在建安時期,相比道教,佛教並沒有廣泛地參與到救治人民的瘟疫疾病之中去,還在“端坐釣魚臺”,是在兩晉以後。
面對長期的動盪,佛教徒才吸取教訓,學習道教逐漸發展起來,因此,建安時期受到瘟疫影響進而發展壯大的宗教,幾乎可以特指道教。
如果說文藝創作反映了建安的世情和文人的苦悶,那麼宗教就迎合了更多百姓的需要,為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都提供了心靈慰藉和社會關懷。而道教廣泛參與瘟疫救治,回應瘟疫下的人民社會心理需求,正是一種人文關懷、人文精神的體現。
這一時期道教的發展集中表現為道教科儀、理論的發展完善和宗教活動的活躍。由於人口大量因瘟疫死亡,喪葬活動頻繁。此時道教發展出解註文和買地券。巢元方《注病諸候》提到,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注易旁人也。
解註文是當時鎮墓的文字,所謂解注,參考引文,也就是擺脫疫病之“住”,使死人身上的疫病不要禍害活人。買地券也是向地下世界通知人的死訊,使死者的魂魄不要流連人世。除此之外,道教還因此發展了許多驅除疫鬼的儀式,這些儀式不免有原始的巫術色彩,但這是早期道教發展並在民間普及的關鍵。
如果說瘟疫使道教思想有所發展充實,就是終末論的提出。在當時,道教的許多流派都提出了終末論。簡單來說,黃巾起義的口號“蒼天己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終末論的一種闡發。後世白蓮教起義,稱彌勒佛是未來佛,要改天換地云云,也與此相似,當然,其中是否有佛對道的剽竊內化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已經提及當時的農民起義,必須說,具有煽動性的宗教一旦染上反抗色彩,則十分容易挑動民變。要闡述建安時期道教的蓬勃發展,則黃巾起義和天師教(五斗米教)、太平教的發展是繞不開的。
《後漢書》記載,鉅鹿張角……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之。黃巾起義之前,張角正是透過道教儀式,治病救人來發展教眾,才最終發展到“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醞釀成黃巾起義。
3、建安時期的醫學發展
前文提到,建安時期瘟疫橫行的一個原因是醫學水平不發達,對瘟疫的防治、控制無能為力,這樣,現實的需要就越發促使醫學接受挑戰,儘快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雜病的含義一望可知,傷寒的意思,據南北朝人解釋是,“雲傷寒是雅士之稱,雲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時代較近,當為可信。
《傷寒雜病論》的出現,有利於傷寒之學的形成和獨立,對東漢以來的醫學理論和臨床治療方法也有所創新,它系統地分析了傷寒之症,提出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為瘟疫的救治提供了理論支援,也能獲得大量的實踐機會,從而進一步完善。
生命健康是最基本的人權,瘟疫橫行之下,醫學的進步也就是最突出的人文精神的體現。
小結
由於各種天災人禍,公元二世紀以來中原大地瘟疫橫行,對人們的生命健康造成極大威脅,對社會變革、政治經濟發展造成極大影響。在極度的黑暗絕望之中,瘟疫的壓迫也刺激了建安時期人文精神的興起,主要表現為文學的自由、思想的發展、宗教的普遍、醫學的進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