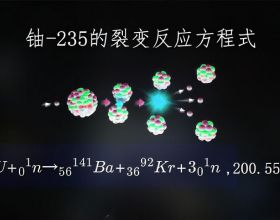獨特的寧夏中衛方言
秦朝並六國後,大將蒙恬率30萬士卒,取黃河南北之地,始將中衛納入中央集權版圖。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置北地郡,中衛屬之。西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攻克北地郡,又復修沿河城障,中衛境內築有城池。西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徙內地70餘萬災民到河套以南地屯耕,中衛始有灌溉農業。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11至109年),境內開始開挖引灌蜘蛛渠(今美利渠)。元朝太祖二十年(1226年)秋,成吉思汗經過沙陀(今沙坡頭),至黃河九渡,攻取應理縣(原中衛縣)。元太祖二十二年(1228年)秋,成吉思汗病死於今海原天都山行宮。
在寧夏,中衛方言是寧夏人語言中最特殊的一支。幾個人坐在一起,中衛人開口說話,就會被識別出來。這是因為“中衛話”別具一格,它以特有的語音、詞彙和語調,將中衛人和其他地區的人區別開來。
“中衛話”不僅與周邊省份陝、甘、內蒙古等地區語言有著非常大的區別,就是和同一省份的吳忠、銀川也迥然不同。
“中衛話”是中衛人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的文化現象。在寧夏,乃至在全國獨樹一幟。
中衛語音因區域地段不同,語音差異也很大。中衛版影象一片東西向平放的樹葉,黃河從中間流過,將縣境自然分割為南北兩塊。
北有騰格里大沙漠,南有香山山地及丘陵臺地,中衛人所操口語明顯地區劃為河南口音和河北口音兩種:黃河以南的永康、宣和等地人說話受中寧、吳忠以及銀川的影響,跟銀北人大體一致;而黃河以北及鄰近地區(包括今中衛黃河大橋以西常樂地區、中寧石空等地)的話語,既不同於自治區首府銀川為中心的寧夏川區話,又和西、海、固山區話有著根本的差別。
這種話語可用中衛市沙坡頭區話作為代表。平常我們所說的“中衛話”,就是指這種話語。
那麼,中衛話到底有什麼特點呢?
中衛方言和普通話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和詞彙上,語法方面的差別一般不大。
語音系統涉及聲母、韻母、聲調等都有多少不同的差異,多種因素形成了中衛話特殊的音色,所以,中衛人只要一開口,就顯得與眾不同了。
中衛話詞彙特點也是非常顯著的:由於歷史上中衛人口遷徙、地形封閉等原因,使中衛詞彙系統中較多的保留了元、明、清古白話詞語;兼收幷蓄了各地方言詞彙,融合性比較明顯;“子”綴重疊構詞靈活多樣,非常富有特色。
諸如:子麼、兀那、支應、比對、牙行、出跳、包彈、談羨、打攪、犯嘴、合該、使乖、行短、和哄、怪道、活泛、淡話、過犯、端相、點卯、營幹、營生、囊膪(chuǎi)、一世界、二和藥、不上串、不受用、冷合合、內官子、大模廝樣、五黃六月、秧秧蹌蹌、不當豁豁、波勒蓋子、立馬短時等。
這些詞語有的在宋代平話中就已出現,大量運用則見之於元雜劇和元、明、清古白話小說。現在普通話和寧夏其他地區話語中大都已很少使用或不再使用了,但中衛話內不僅保留,而且還以較高的頻率使用著。
中衛境內漢族人口五方雜處,來源不一。這種情況反映在語言上,便形成了中衛話詞彙與各地方言土語相混雜的融合性特點。
如:頷水、心疼(好看)、賴髒、惡梭(垃圾)、鍋盔、姜窩子、烏肚子水等是陝西話詞彙;娘娘(姑姑)、尕娃、幫肩(差不多)、著氣(生氣)、卜浪子(手搖小鼓)、汗蹋子(布衫)等是甘肅話詞彙;燒包、客氣、吵嘴、膀子(翅膀)、墳堰(塋)、撂(扔)、胳老赤、軲轆子等是安徽話詞彙;大爹、姨爹、姑爹、姑媽、街(gāi)道、背時、洗澡(游泳)、乾飯、蒸饃、口乾(渴)、胰子、牢實(結實)、兒娃子、女娃子、背鍋子、街沿子等是四川、雲南話詞彙;嫌含(討厭)、兀老(棉鞋)等是東北話詞語;大媽、丫頭、立巴(外行)、跑肚等是河北、山東話詞彙;爹爹、外母、事幹(事情)、戳(捅)、擔(挑)、扯(拉)、綁(系)等是南方話詞彙。
這些詞彙經過一定的歷史過程,逐漸融合形成了中衛話常用詞彙。
中衛話詞彙的又一特點是用“子”作字尾或者用“子”作字尾重疊構詞。這種構詞不僅應用得極為廣泛,而且在結構方式上也表現得更為靈活多樣。
平時在中衛人的口語中(尤其是老年人),經常能夠聽到像:缸子、凳子、胖(音茫)哥子、豆角(音各)子、娘母子、黑子子、石子子、盆盆子、罐罐子、車車子、馬馬子、油油子、鹽鹽子、辣辣子、醋醋子、站站子、等等子等一系列詞語,它可以使聽話者感受到一種特別的親切感,也能微妙地表達出中衛人對一些事物的好惡感情和褒貶態度。
另外中衛話裡還有一些特殊詞語,如老老(叔父)、傢什、香匙、葫蘆(南瓜)、芋頭(土豆)、印花、哈德(衣兜)、馬下、額顱蓋、胳肘子、幹腿子、火取子(火柴)、跑橋子、把故子、推故子、跌故子、去秋子、二不子、西番麥、水饃饃、流沙虎子、脊樑乾子、肚冒齊子、精屁股劉四等,這些生動活潑、有濃厚鄉土氣味、富有極強表現力的詞彙,進一步加重了中衛話的地方特色。
那麼,特色鮮明的中衛話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但主要和漢族人口的遷入、地理環境的影響及人們的心理習慣有直接的關係。從漢族人口的遷入情況看,自秦漢至元末、就已經在寧夏移入了漢族人口,而且各個朝代寧夏也一直有漢族人口居住,但由於中衛地處祖國邊疆,漢族政權對邊疆的統治很不穩固,居地人口移入遷出更迭頻繁,同時又缺乏歷史資料,他們的來源很難確定。元末農民起義推翻了元朝政府,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發生過兩次大的人口遷移。據舊寧夏地方誌稱,移民來自齊、晉、燕、趙、周、楚,而吳越人口居多,故居民“彬彬然有江左之風”。這是寧夏各地、包括中衛在內的有籍可考的人口來源。
據一些中衛老戶說,自己的祖先是山西大槐樹人。經調查,山西省洪洞縣城北廣濟寺旁的大槐樹,確為洪武至永樂年間各地移民的集散地。各處移民到此集中,由官府編排隊伍,發給“憑照川資”,然後遷往各移民區。
“大槐樹”只是一個移民集散地,從大槐樹下移到寧夏、移到中衛的不僅有山西人,也有其他省籍人,其中包括不少江淮吳越人。從中衛人的“尚詩書、攻詞翰”“重耕牧、嫻禮儀”的良好文化道德傳統,以及飲食起居習慣,尤其以農業的精耕細作、種植綠肥等方面,都可看出大有江淮吳越人的痕跡。
明代移民奠定了寧夏人口的基礎,中衛人口亦然。各地遷移過來的屯田軍士、移民、罪囚以及官臣、屬吏、從眷等雜居共處,多種方言互相影響,共同融合,便逐漸形成了獨特的“中衛話”。整個寧夏方言大致以“秦晉語”為基礎,並雜以“齊魯趙燕語”“江淮語”甚至“吳越語”。而中衛話除了上述語言融合外,還和“隴語”關係密切,還有西南“川、滇”話的影響。明清之際,寧夏川區語言大體相近,這也可以從《朔方道志》所載的方言資料中得到證實。
但發展到今天,為什麼銀川、銀北和銀南的大部分地區的話語比較相近,而與中衛話的差別卻非常之大呢?
這主要是語言的可變性造成的。中衛話的差別與特色正跟中衛黃河以北的地理環境有關。中衛的地理形勢,正像縣誌裡稱道的那樣:“北背邊牆,南面大河,據銀川上游。其東則青銅牛首,鎖鑰河門,其南則香巖雄峙,列若屏障,左倚勝金之固,右憑沙嶺之險。”這段描寫清楚地描畫了一個四塞之地的典型形象。尤其勾勒出了中衛黃河以北地區的封閉狀態。這在交通極不發達的古代,很難與外面發生經常接觸和聯絡。
同時,這一塊封閉起來的土地又是肥美的膏腴之地,加上黃河水自流灌溉,既無旱災之苦,也無水澇之憂,山清水秀,魚豐米足,這種優越自然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了中衛不需要和外面發生過多的聯絡。因而定型以後的中衛話很少有能夠發展變化的機會。這就形成了中衛話保留古白話詞語多的保守性特點。而銀川平原的其他各縣則不然,它們處在一個開放性的地理環境中,交通比較方便,和外省區的接觸、聯絡也比較頻繁,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比較大,這就形成了銀川話的變異性特點。
這樣,中衛話和銀川話相比,就有了越來越大的差別和特色。
另外,人們的心理習慣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中衛優越的自然環境,早期發達的經濟狀態和文化教育,造成了中衛人心理意識上的優越感和自豪感。
“中衛有天下人,天下沒有中衛人。”
山南海北的外地人一到出產豐足,飲食上好的中衛就定居了,就不想走了。
中衛人都比較懷戀鄉土,不願出門。即使有也要千方百計回來,或者稍有年紀就落葉歸根。中衛人心理上的家鄉優越感和自豪感對“中衛話”發生著巨大的影響,以致形成了中衛話對內的穩固性和對外的同化力;這種優越感和自豪感在人際關係上會產生一定排外性。
新中國成立前,中衛人常把外來的陝西人叫“吵子”,把河南人叫“侉子”,把四川人叫“蠻子”,把甘肅鎮番(民勤)人叫“沙老鼠”,把蒙古人叫“臊韃子”。
外來人要想在中衛定居,免受中衛人的歧視,就必須儘快改變自己的言語,由外地口音改變為中衛口音。反之,中衛話在別的語言環境中卻非常穩固,具有一種不可滲透的性質。
不管中衛人是在銀川工作,還是在固原或者鹽池工作,不管是在區內還是在全國其他任何地方,中衛口音都很難改變。在異地他鄉,往往憑著一口富有特色的中衛話,到處都可以很容易地識別中衛老鄉。
中衛話是漢語許多方言中的一支。它深刻、動聽、富於表現力,易於引起對方聽話的興味。但中衛話中的不少字音和方言土語也往往給人們帶來誤會,影響更大範圍內的交際。因此,在新時期語言文字政策的指導下,中衛話需要積極向普通話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