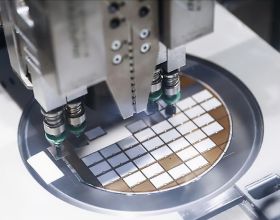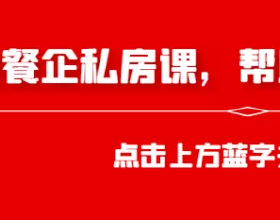孫伯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古代漢語、文獻語言學、少數民族古文字文獻、西夏學。著有《西夏文獻叢考》《西夏新譯佛經陀羅尼的對音研究》《黑水城出土等韻抄本〈解釋歌義〉研究》《金代女真語》。
中國民族文字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曾經使用和正在使用的文字。中國是世界上文字種類最豐富的國家,傅懋勣曾統計古今少數民族文字共57種。聶鴻音認為民族古文字有近40種,而加上20世紀以後傳教士創制的民族文字,以及20世紀40年代以後國內創制完成試行的文字,中國古往今來的民族文字當近百種。
中國民族文字一般以辛亥革命為限,分為古和今兩種型別,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境內創制或借用的各種記錄漢語之外的民族語的文字均可稱作民族古文字。民族古文字的使用年代最早可追溯到2—3世紀,如佉盧文,大約於2世紀在於闐(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使用。它們的產生和來源多樣,除了仿漢字的方塊壯字、方塊白文,利用漢字結構創制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之外,有些是源自域外古老的阿拉米字母,如佉盧文、粟特文、突厥文,粟特文進而衍生出回鶻文、蒙古文、滿文、錫伯文等;有些源自印度的婆羅米字母,如焉耆—龜茲文、于闐文、傣文、藏文等,而作為元朝“國字”的八思巴文則依藏文變化而成。這些民族古文字和漢字一起,組成了中國文字的百花園。
2019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致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週年的賀信指出:“新形勢下,要確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傳承。希望廣大研究人員堅定文化自信,發揚老一輩學人的家國情懷和優良學風,深入研究甲骨文的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促進文明交流互鑑,為推動中華文明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賀信不僅為甲骨文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務,也為我們從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學者提出了新命題和新使命,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具體而言,民族古文字研究在“十四五”期間肩負的新使命有如下方面。
第一,傳承“絕學”,培養精通民族古文字的稀缺人才。學界一般把于闐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滿文等民族古文字稱作“死文字”,是基於曾經使用這些文字的民族已經融入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現在已經沒有一個民族主體使用它來記錄自己的語言。如果研究這些民族的古代歷史、語言和文化,只有透過遺存文獻的釋讀才能實現。早在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即開始設立“特殊學科”的傳承保護專案,中國民族古文字方面主要由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專家主持。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增設“絕學”專案,而從2020年開始,社科基金又設立冷門“絕學”團隊專案,加大了資金投入力度,規模堪比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一批民族古文字文獻研究專案得以立項,如段晴領銜的“北京大學胡語文書研究團隊”、孫伯君領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古文字文獻研究團隊”、吳元豐領銜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文獻研究團隊”。國家投入大量資金把民族古文字納入“絕學”加以支援,其宗旨即是保護和傳承古文字研究,培養該領域的稀缺人才。
第二,聚焦“民族文獻語言學”研究方向的理論與平臺建設,於民族古文字文獻研究中貫徹漢字研究的考據學方法,建構和發展本學科的基本理論,融通“漢語言文學”與“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兩大學科體系。目前,各大院校中文系設立的“中國語言文學”等課程只包括漢字、漢語的教學與研究,很少涉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而民族院校研究少數民族語言也很少涉及古漢語。今後民族古文字文獻研究應該借鑑漢語言文學領域的考據學方法,著眼漢語與民族語的接觸、影響與互證,廣泛蒐集整理民族古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事實,不侷限於為民族語提供資料,要為分析漢語通語與方言的語音變化提供實證,把中國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的內容納入傳統的“漢語言文學”大系統,打通學科壁壘。民族古文字文獻中有很多對音材料,對這些番漢對音資料加以系統整理,可以彌補漢語韻書《切韻》和《中原音韻》等漢字歸類字書之不足,為擬定漢字音值提供寶貴材料。同時,民族古文字文獻中大量譯自漢語的儒家、佛教經典,也堪為研究漢語的歷時音變、詞彙演化、語法構成,以及宗教文化的傳播歷史提供參考。遼代以來,北京話的前身近古官話的形成,與漢族和阿爾泰民族長期接觸的語言背景不無關係。在契丹語、女真語、蒙古語、滿語等阿爾泰語系語言的影響下,現代北京話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結構最簡單的漢語方言。通語的發展演化和方言底層的橫向傳遞均需要民族古文字的對音資料加以佐證。
第三,深入研究民族古文字中的文字“活化石”,為文字發展史和文字型別學提供理論支撐,把“民族古文字”納入“中國古文字”和“普通文字學”研究的大框架。從遠古到20世紀初,中華大地上曾經出現過近40種民族古文字。爾蘇沙巴文、納西東巴文等“助記符號”啟發我們在普通文字學方面深入思考文字的性質及其與語言的關聯方式。民族古文字的造字法對漢字會意、轉註等造字法的創造性繼承和發展,及其靈活採用“音讀”與“訓讀”的形式借用漢字,極大地豐富了漢字“六書”及其理論。民族古文字異常豐富的來源、形態及其系統型別,為普通文字學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思考空間。比如哇忍波創制於1923—1927年的傈僳音節文字,總數989個文字元號,大多是由弧線、曲線構成的圖形符號,形態較為原始,但卻是典型的音節文字,能夠比較全面地記錄傈僳語音節,堪比1980年8月國務院批准實施的涼山規範彝文方案。傈僳音節文字的創制啟發我們思考如下問題:(1)判斷一種古文字成熟與否的標準是什麼?是這種文字字形的符號化程度,還是這種文字發展歷史的久遠端度,抑或是能否完備地按照語詞次序記錄語言的最小單位“詞”或音節?(2)與傈僳音節文字一樣,中國境內出現的民族文字大多是由某個人一次性創制的,如藏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漢字發展史上也有倉頡造字的傳說,《淮南子·本經訓》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但古往今來,學界都對漢字是某個人創制的持懷疑態度,認為漢字是社會需要的產物,是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傳說中的倉頡未必真有其人,即使有也無非是做了一些整理和統一工作。如《荀子·解蔽篇》所言:“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無疑,民族文字的創制過程為理解“倉頡造字說”提供了思考的空間。
第四,深入挖掘民族古文字文獻中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揭示中華文明交流互鑑的實情,構建中國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歷史文化大系,為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學理支撐。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豐富多樣的民族古文字所記錄的歷史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二十五史”是用漢文書寫的中華民族的歷史,而民族古文字文獻可以與漢文史料互證,從“他者”的視角呈現少數民族融入中華民族的過程。在與中原王朝交往過程中,少數民族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具體表現在推行了仿照漢字設計的全新文字,以及透過翻譯大量中原王朝的書籍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西夏翻譯的典籍涵蓋中原典籍的經、史、子、集各個部類,其豐富程度為中古少數民族地區之最。
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往往認為孔子是“萬世所尊”的“有大功德者”,紛紛效仿中原王朝為其建廟、春秋祀奠。今後的民族古文字研究,應該全面地研究民族古文字文獻,揭示周邊少數民族對中原儒家文化的理解方式和接受方式,揭示中華文明交流互鑑的實情,為中華傳統文化研究和我國各民族文化的和諧發展提供素材,從而構建中國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歷史文化大系,為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學理支撐。
第五,建立民族古文字文獻基礎資源庫,搭建民族古文字數字化平臺,把民族古文字研究帶入數字化時代。隨著國力的提升,國家投入了很多力量保護民族古籍,近年,很多民族古籍得以入選遺產名錄加以保護。同時,國家也花重金把流失海外的民族古籍拍攝回來出版刊佈,這為少數民族古籍保護與數字化提供了重要契機。不過,目前民族古籍的數字化大多仍停留於刊佈圖片、掃描存檔的階段,沒有實現真正意義的數字化,原因之一是民族文字字型檔的研發嚴重滯後。有鑑於此,2011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實施了“中華字型檔”工程,其主要目標是要建立全部漢字及少數民族文字的編碼和主要字型字元庫,重點研發文字的編碼體系、輸入、輸出、儲存、傳輸以及相容等關鍵技術。其中第18包“少數民族古文字的蒐集整理與字型檔製作”主要任務是研製少數民族古文字的字元庫和輸入法方案;第19包“少數民族現行文字的蒐集整理與字型檔製作”計劃研製全部少數民族現行文字的字元庫和輸入法方案。目前這一工程接近尾聲,建立在統一平臺上的全部少數民族文字的字元庫接近完成。
在當前的形勢下,民族古文字的數字化任務應該是建立民族古文字文獻基礎資源庫,搭建民族古文字數字化平臺,解決古文字研究發展的瓶頸。下面幾項任務尤為緊迫:(1)設立服務於語言學、歷史學等研究目標的民族古籍數字化專案,數字化內容包括:古籍的著錄、圖片的掃描和歸檔,對古籍進行電腦錄入,用“四行對譯法”加以解讀,對句子成分進行“語法標註”,具備檢索功能等。(2)設立“民族古籍保護與數字化研究中心”,從國家層面統籌管理,加強研究團隊建設,以老帶新。民族古籍研究普遍存在學科帶頭人年齡結構老化的問題,今後課題的設立應該重點考慮國內各文種的學科建設和佈局,優先支援各文種的代表性專家和有研究基礎的重點基地的團隊建設。(3)重視多文種資料的關聯研究,構建大文獻、大歷史的學科視野,服務於中華文明交流互鑑的研究。
綜上,民族文字記載的文獻不僅能夠構建本民族的歷史文化,而且對周邊民族歷史文化研究、對建構中華民族各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均能提供重要的參考。有些民族古文字曾作為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所建立王朝的“官方文字”,其文獻內容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共同書寫的,呈現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過程。西方國家研究遼、夏、金時,往往把契丹、西夏、女真等民族的歷史放在中亞史範疇。如果我們不培養該領域的人才,放任民族古文字成為真正的“絕學”而無人可識,那勢必把該領域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他人隨意解讀和構建。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孫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