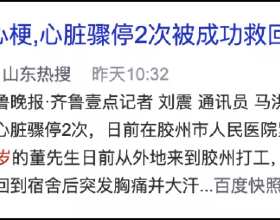感謝陳峰老師賜稿
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1日第17版“學林”,今據作者原稿,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漆門學記
文丨陳峰
有緣投於漆俠先生門下為徒,實乃我人生一大幸事。今天,我能執教於大學講堂,從事史學研究,是離不開先生的引導。而先生一生執著學術的精神和百折不摧的傲骨正氣,更成為我行走世間的路標和楷模。
初 識
初識漆先生是1981年的事。那年秋天,中國農民戰爭史年會在母校陝西師大歷史系召開。孫達人老師作為辦會方負責人,將系裡七七級的許多同學調動起來,協助會務,我也被安排在其中。當年中國農戰史還是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一大批重量級的學者長期都活躍於這一領域。看到參會者的名單,我們學生都很興奮,因為雖讀過大多數人的論著,卻沒有機會謀面。
報到那天,各路名家紛至沓來,真可謂冠蓋雲集。其中漆俠先生十分引人注目,屬來賓中的高個子,戴著眼睛,清癯有神,談吐爽朗,帶有濃重的山東鄉音。以前,聽課時瞭解過一些漆先生關於農民起義的觀點,也知道文革中《光明日報》批判過先生“讓步政策”的觀點。為寫論文曾拜讀過他著的《秦漢農民戰爭史》,但印象最深的還是《王安石變法》,文筆犀利,分析深刻,是書荒時代少有的好書。
會議期間,我接觸漆先生的機會不多,只是在會場上聽過先生充滿個性的發言,也知道先生當選為理事長,照相時位居前排正中,作為一介學生也清楚其中的分量。會後,同學們議論所見各位學者風采,其中談到最多的一位便是漆俠先生,我自然對先生心存敬意。不過老實說,當時只是作為名家聊到了漆先生,尚未聯想到其他方面。但這次見面,卻成為我以後投師的機緣。
入 門
1984年,我工作兩年後獲准考研,尋覓導師時很自然便想到漆先生。於是斗膽報考了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室。當時,已大致瞭解到國內宋史研究的重鎮有三處,一處在北京大學,一處在杭州大學,還有一處便是河北大學。河北大學倒非名氣很大,但卻因漆先生及其研究室而享譽史林和學界。
初試成績通過後,我懷著忐忑的心情赴河北大學參加複試。再度見面時,先生和藹可親地詢問了一些情況,我在回答完問題後,也趕忙提及那次農戰史會議上的事情,先生聽罷爽快的笑了,說:“好啊,願意學習就好,來了後要多讀書。”還聊起抗戰期間在陝西的見聞,並特別打趣地說:當地人吃飯不講究,主食之外,就一盤辣子和一盤醋。交談之下,我既感到溫暖,也放下了心。
說句實話,與當下的大環境相比較,當年確是讀書做學問的好時光,想必大多數人都同意我的看法。那時,國家空前重視教育,社會崇尚知識,上面及學校干擾又少,師生更為心靜。特別是招生嚴格,錄取人數不多,導師遴選的條件也很嚴,大都是有相當成就的專家,這就保證了培養的質量。我入學前,漆先生門下只有三位弟子,三位學長外就是我們四位新生,總共七位研究生。就規模人數而言,比現在許多導師帶的博士生還少。當時,先生身邊還有助手高樹林、郭東旭兩位老師,另外就是辦公室和資料室的兩位工作人員。
宋史研究室坐落在河北大學南院東面一處平房院內,是舊時河北省委的地方,環境相當安靜。研究室有不少圖書資料,先生自己的許多書也拿來供大家使用,像浙江書局刊本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宋會要》等等。不久又重金購置了臺灣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這在八十年代中葉的中國大陸還比較少有,許多大學圖書館也無力添置。先生每天必來,往往還是最早就到,寫作之餘,常找我們談學問聊天,氣氛十分融洽。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熟悉了漆先生率性剛直、愛憎分明的性格,也大概瞭解了先生的學術經歷。先生的傳統史學功底極為雄厚,文獻史料常常信手拈來,但印象更深的還是博大的眼界和深厚的理論素養,談學術話題總能從大處著眼,看問題極其深刻。這些都可從先生的論著,特別是百萬言的煌煌鉅著《宋代經濟史》得到說明。先生早年入西南聯大求學,抗戰結束後進入北京大學隨鄧廣銘先生讀研究生,是當時北大的高材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漆先生到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成為所長也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的助手。以後因政治風波及性格耿直的原因,被整離開該所,調入天津師範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河北大學。
回憶研究生三年學習,真是有苦有樂。記得那時除了主要由先生授課外,高樹林老師也講過元代經濟史的課,再就是先生請來一些名家友人作報告,印象較深的有首都師大的寧可、山東大學的田昌五、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方行和歷史研究所的王曾瑜等多位先生。我與同門大多數時間都在自己看書,有時為了尋找史料,還常泡在北京圖圖書館古籍部多日,住宿在便宜的地下室裡,吃著泡泡麵。那時我有些魯莽膽大,時常為一些問題打擾先生,先生總是循循善誘,使我醍醐灌頂,如沐春風。就此大致掌握了史學研究的方法,算是初入門徑。
說起來慚愧至極。大約在1986年下半時,漆先生詢問我畢業去向,當時我還孑孓一身,就回答隨便去哪裡都行。隔了幾日,高老師便找我談話,說漆先生打算留我在身邊,我很高興地答應了,因為能繼續受到先生指教,做宋史研究必有前景,並多少有些虛榮心,能被先生看中。
事有湊巧,次年寒假回家,家人、同學給介紹了一個本地高校的物件。那時自己年輕不懂事,熱戀中只考慮與女友的關係,返校後便向先生說出反悔的決定。先生剛直傲骨的性格是學界出名的,聽了我的表白非常生氣。以後高老師多次勸我留下來,我也清楚這是先生的意思,雖然深感內疚,但仍未能改變主意。畢業前,先生不計前嫌,因為我聯絡工作的緣故,還為我給時任西北大學校長的張豈之先生寫了推薦信。現在想起來,我確實傷了先生的心,但先生以父輩的寬厚原諒了我。
就這樣,我懷著十分歉疚的心情離開了河北大學,告別了恩師漆先生。
回 爐
到西北大學歷史系工作後,因教學任務繁重,加之宋史非所在單位的研究重點,資料欠缺,我只能自己摸索,其間又到國外兩年。興之所至,做的方向更雜了,故在宋史研究領域進展緩慢,除了就漕運專題從宋代上下延伸,完成了《漕運與古代社會》的書稿,並發表了若干篇論文外,多年對宋代軍政的興趣卻未取得突破。這些都是自己的選擇,也沒有多少怨言。但每每想到當時離開先生的情形,就深感愧疚,除了出國前攜家人專程看望過先生一次外,也一直不好意思去拜訪,只有每年寄上賀卡,寫上表達祝福的話語。
1997年夏天,宋史年會在銀川召開,先生作為宋史研究會會長必然出席。接到通知之後,我躊躇再三,還是打消顧慮參加了會議。其間,我找機會向先生彙報了自己十年的情況,特別提及做研究的一些困難,先生很關心地聽了彙報,鼓勵我繼續在宋史領域深入探索。不過,在會議前後,我有兩年多時間花在了開發研製國內第一部多媒體《中國通史》的工作上,這是一件耗費精力,又無所依憑的艱苦事情,暫時無暇他顧。
到1999年初,當多媒體《中國通史》大致有了結果時,我決心擺脫各種干擾,一面整理完成了有關北宋崇文抑武問題的書稿,同時將自己的研究集中到宋代武將群體的專題上。這時,更感覺到自己學識的不足,另外在資料資訊欠缺的情況下,培養研究生也有些吃力,於是想到重回漆先生身邊學習的念頭。好在我得到了先生的理解,還有同門師兄弟的支援,當年便取得在職攻讀博士生的機會。
說來慚愧,自己當時剛評上教授,在年近四十時又回爐與年輕同學一起當學生。不過,經歷了許多磨礪之後,既珍惜時光和機會,讀書看問題也會深入一些。因此,雖然有一部分時間還要在本單位服務,但效率不算低。在選畢業論文題目時,我提出作“北宋武將群體研究”,認為有些積累,此前《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透析》的書稿已請先生看過,並得到先生的序言,故而先生首肯了我的想法。由此,我對這些問題的思索有所深入,不僅兩年多大致完成了論文初稿,還先後發表了十篇論文。
回想那段日子,除了在蒐集資料和寫作的過程中,不斷請教先生問題外,我還經常有機會與先生聊天。晚年的先生早已貫通古今歷史,思路異常清晰,既保持了一貫深刻犀利的風格,看問題更充滿睿智。在那間多年的辦公室裡,先生總會讓我抽他的好煙,先生也偶爾抽一兩支,談話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先生常常談起往事,涉及許多學界的人和事以及經驗教訓,使我大開眼界,也讓我更深入地瞭解了先生。還值得一提的是,漆先生與我有共同的愛好,就是喜好拳擊,當然先生是欣賞,我則不僅欣賞,從前也練過一點,因此談到拳王泰森與霍利菲爾德之戰時,先生眉飛色舞地發表見解,令人想不到是年近八十高齡的老人,竟那樣洋溢著生機,充滿鬥志。我和同門們都說:漆先生肯定高壽,一定能活到九十以上。但誰又能想到,以後竟發生了意外醫療事故。
傷 逝
記得很清楚,那是2001年11月2日,一個寒冷陰霾的日子。早晨八點一刻左右,我騎車到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看書,一進樓道就被辦公室的老師攔住,告訴我剛得知漆先生可能不行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頓覺腦子一片空白,立刻下樓騎車趕往先生家。
回想起來,我進先生家門後,首先看見一位女醫生正在收拾器械,再看到的就是躺在床上的先生。當時在場的還有先生的公子漆燕生,其餘一兩位已記不清了。望著彷彿睡著了的先生,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兩天前下午我還與先生在辦公室聊過很多事情,時隔兩日竟發生這樣的意外。
隨之,幾位師兄弟和宋史研究中心以及學校有關負責人等都先後趕來,大家先詢問有關情況,後來就商議到如何處理後事。大約上午十點多鐘時,我和師兄姜錫東用酒精為先生仔細搽洗了身體,換上一身新衣,其時內心的傷痛才不斷湧出。至今已八年過去,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送葬那天,來了很多人,既有同門弟子、本校師生和河北省的一些官員,還有遠道專程趕來的許多學界友人。葬禮非常隆重,當哀樂奏響時,很多人難掩悲痛,都流下眼淚,記得王曾瑜、山東大學的喬幼梅、南開大學的葉振華等幾位先生和我們許多弟子更失聲痛哭。我想,這種傷心不僅僅在於一位老人的辭逝,更多還是因醫療事故引發的意外刺激,使人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現實。漆先生雖然經歷了多少苦難和折磨,但身體是那樣硬朗,思想是那樣活躍,意志又是那樣堅強,還有那麼多宏大的寫作計劃要完成,如果真有上蒼的話,肯定不該如此對待。然而,誰也不願相信的意外就擺在眼前,不免使人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無常。
在漆先生故去前,我已大致整理出畢業論文的主要內容,並獲得了先生的指教,只是還沒有拿出完整的稿子請先生過目把關,這無疑是我終生引以為憾之事。我想,自己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認真完成論文,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靈。2002年5月間,我順利透過答辯,結束了在職博士學位的學習,隨後告別了河北大學。
當年11月2日,是先生亡故後一週年,我專程去保定參加了紀念先生的活動。散佈各地的大多數同門弟子再度匯聚,加上在校的學生,人數有六七十位之多,幾居國內宋史學界小半壁江山,其中許多人也已成為本領域的骨幹學者(若算至今日,包括我在內的中國宋史研究會四位副會長都是先生的學生),正是高山水長,惠澤百川。在先生的墓地前,我垂頭撫今追昔,內心盛滿了感恩之情。自己在漆門學習的日子,如畫面般快速閃過,先生的音容笑貌更清晰顯現。離別時,我在心中默默地訴說著無限的思念,祝福先生在天國長樂無極。
斯人長逝,遺風永駐。作為一名受業多年的弟子,我始終視漆先生為道德文章的楷模,尤其敬佩先生身上的錚錚傲骨和坦蕩胸襟,在培養自己學生的過程中時常以此教導他們。人生也有涯,而知無涯,每每想到先生,自己做事做人未嘗不時刻加以鞭策警惕!
2009年12月8日於西北大學
注:本文發表時無主標題與小標題。
▼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編輯:潘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