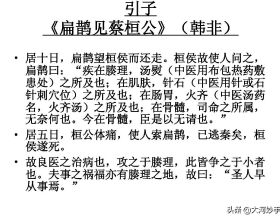成年人的愛,既要在世俗現實中掂量權衡,又要分析取捨計較得失,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原則。年少氣盛時能捨棄一切去愛,是因為那時候擁有的一切不多而已。
世界上哪有那麼無緣無故的愛。每個人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付出最小化。
①
高紅瑛催她最小的閨女談戀愛,催得不明顯,就是問問。問急了,閨女冒出一句:“哎,現在的男人,都不是想來愛我,而是想來睡我,你說咋回事?”
65歲的高紅瑛愣了一下,緩緩說:“那也是好事,到了我這個年齡,想睡我的人都沒有了。”
女兒笑得驚天動地。
高紅瑛是個奔放的老人,90年代就開始一邊上班一邊做生意,手裡有點錢,也不顯老,現在還每個月去美容院保養。美容院有個專案叫“私護”,這也是她每個月都要做一做的。它全名叫私處護理,打著“醫美”的名號,幹著“不可告人”的勾當——幫人達到高潮。私護老師用手、用儀器,60多歲的老人都能叫她爬上巔峰。高紅瑛體驗過一回之後,再也斷不了這事兒了。
做“私護”價格很高,高紅瑛有時候也自責是不是忒不要臉,不把錢存著留給孩子用,自個兒在這兒浪得沒邊兒。但是又一想,丈夫走得早,自己吃了半輩子苦,為啥不能享受點好事兒?
這事兒她誰也沒說過,獨自滋潤著。
她覺得自己是六十多歲的身子,四十多歲的心。碰到有人給介紹物件,長得不賴的,她還春心萌動一把。
萌動不曾熄滅,但也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得人品正,聊得來,還得有真感情,收入上也得搭。隨便拎出一條來好找,綜合起來就沒戲了。
②
老社群的姐們兒打電話來,說老房子要拆遷,叫高紅瑛有空去辦手續。誰先簽字,誰的賠償最高。高紅瑛趕緊回去辦手續,沒想到碰上了張輝民。
“你不是在紐西蘭嗎,回來啦?”高紅瑛心跳得緊鑼密鼓。
“回來辦老房子拆遷手續,你最近咋樣?”
“還不錯。你呢?”她說:“你肯定是好,發達國家,能不好嗎?”
“外國的月亮也不是你想的那麼圓,尤其飯難吃。”
兩人都笑起來,約了晚上一起吃飯。酒不醉人人自醉,倆人聊起從前,都是說不完的話——
60年代末,國家號召學生學工、學農、學軍。當時倆人都才上初中,有一次老師通知大家學軍。張輝民以為要到部隊去,去了才知道,由於部隊彈火炸藥多,怕出事,不能讓學生去,於是部隊派人到學校組織拉練,也就是學軍人走路,一天來回要走50里路。白天要由學生們自己做飯,糧食,蔬菜,鍋,每人帶一樣來就行。
糧食和蔬菜還好說,可是那時候每家每戶只有一口鍋,所以提出帶鍋的寥寥無幾。
張輝民家裡是做修鍋補碗的生意,有多餘的鍋,於是他自告奮勇地提出帶鍋。
高紅瑛當時是他們的排長。部隊化管理嘛,都管班長叫排長。張輝民揹著口鍋還沒叫苦叫累呢,但見高紅瑛揹著她自個兒的口糧,累的氣兒都快斷了。那時候學生放學後都幫家裡人幹活,沒有嬌生慣養的。張輝民覺得稀奇,老看她。
六十年代的學生男女都不太說話,也不知道對方家裡情況。
他們第一次說話是:“你的東西太沉了,我幫你拿。”
“不用,我拿得動。”高紅瑛紅臉拒絕。
在那個年代能說出這話是了不起的突破。
中午吃飯,其它同學拿的都是雜糧紅薯包穀面。只有高紅瑛拿的是細糧白米白麵。高紅瑛能感覺到張輝民總想問她什麼。她躲著,眼神撲閃著,不讓他有機會問出口。
因為她父親是縣長,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不會再和她說話。那個時候男女關係嚴格得令人髮指,只要上面有人聞到點風吹草動,就可以處分他。
兩人升起點情愫,誰也沒點破。
③
6月,夏收。學校又組織大家到離家100裡的農村學農。
他們班50名學生,25名男生,25名女生。一男一女搭配成25對,到25家農戶吃飯,每人每天交給農戶一斤糧票。睡覺是在當地學校的課桌上,男生一個班,女生一個班。學農的時間為10天。
老師開始念男女同學搭配的名單,當唸到張輝民和高紅瑛是一組時,兩人對視一眼,臉都有點紅。
張輝民和高紅瑛分的這家農戶是一對中年婦女,家裡有老人和兩個孩子。屋子都是土地,土牆,土炕。吃了兩天飯,高紅瑛有點兒受不了了,因為幾乎一日三餐都是紅薯和苞谷糝。張輝民問她:“你是不是不舒服?”高紅瑛告訴他,自己在家天天吃白米白麵。
第二天村裡一家人辦喜事,張輝民不見了。高紅瑛正在地裡幹活,張輝民神秘地跑過來,鼻尖上都是汗,他從衣服裡拿出倆饅頭:“給!”高紅瑛大吃一驚:“哪兒來的?”“村裡有人結婚,我去偷的。”高紅瑛餓得拿起來就吃,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到了收麥子的時間,村裡的農民讓學生用架子車把麥子運到麥場。
太陽烈火一樣熾烤著大地,張輝民拉著架子車要經過一個上坡,他用力拉,高紅瑛在後面用力推。革命感情就這樣在汗水中建立起來。終於把架子車拉上去,張輝民讓高紅瑛趕快到麥場佔地方,剩下的路他自己拉。高紅瑛一溜煙跑去佔地兒了。
地方佔好後,高紅瑛卻左等右等等不來張輝民。她只好又回頭去找。只見他在魚池洗澡,露著個頭 。她著急得大叫:“張輝民,你讓我去麥場佔地方,你卻跑這來玩水!”
張輝民窘迫地說:“你先走,我馬上去。”
高紅瑛不走,覺得他太貪玩:“我盯著你,要不然你又跑了。”
張輝民這時候是光屁股。高紅瑛不走要盯著他,怎麼辦?那時候人單純,高紅瑛根本沒想到這一層。而張輝民又不能說,說了有耍流氓的意思。
倆人僵持著。
那家農戶的男主尋了過來,看見他們一個在魚池裡,一個在魚池邊。哈哈大笑:“你不走他怎麼穿衣服呀。”
高紅瑛這才反應過來,掉頭就跑,跌跌撞撞,比蛇竄得還快。
晚上吃飯時高紅瑛質問他為什麼跑去玩水,張輝民吱吱唔唔地說:“我是去洗澡,衣服都汗溼了,人都臭了。”
“臭了又怎麼樣?!出來學農,誰還能香?”
“我怕……你聞著噁心。”
高紅瑛不說話了。月色清涼,星光依稀,兩個年輕人悶著嘴嚼粗糧,你偷看我一眼,我偷看你一眼,眼神兒撞上了,又驚惶地撲騰開。
④
學農還剩兩天時,高紅瑛發現張輝民有點不對勁兒。吃完飯他們坐在院子裡的小石墩上,高紅瑛問他怎麼了,張輝民說:“我糧票丟了”。
“丟了多少?”
“丟了兩斤。剩下兩天的飯錢。”
“哦。”
晚上同學們陸陸續續回學校休息,高紅瑛磨磨蹭蹭的,跟張輝民走在後面:“喂,張輝民,張輝民!”
張輝民小心地回頭。
“晚上你到學校後院來一下。”
他們的包袱被褥都在教室。高紅瑛取了自己的糧票,跑到後院。張輝民果然等在那裡。她把糧票塞進他手裡:“拿著。”
張輝民問:“你呢?”
“我多著呢!”
“高紅瑛,你家到底什麼情況呀?”
“你別問這些。”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你不是也對我好嗎,上一次你還給我偷饅頭呢。”
張輝民尷尬地笑笑。
高紅瑛說:“你膽兒挺肥的,我叫你出來,你就敢出來。這要是被人逮到了,指不定要怎麼處分呢。”
張輝民忽然激動起來:“我不怕!”
“為什麼不怕?”
“我知道你不會害我。”
“那要是害你呢?”
“我認!”
高紅瑛眼圈兒紅了,她說:“握個手吧。”
她把手伸出去,張輝民握著,不丟。她想往回抽,他用力往自己身上拔。高紅瑛又急又羞,莫名還有點幸福。到底沒他力氣大,被他拽到了懷裡。青春的荷爾蒙一點即炸,兩個人氣喘如牛,最後張輝民也沒幹啥,只是緊緊地抱著她說:“高紅瑛,我喜歡你。”
⑤
學農結束之後,兩人不再躲避。如果旁邊有人,他們微微一笑,如果沒人,還會說上幾句話。
快畢業了,突然有一天一輛吉普車開進學校,學生們都看見有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走進教導處。過了一會,幹部模樣的人出來,校長點頭哈腰地迎送。
高紅瑛隱隱有不祥的預感。
果然,放學後張輝民被叫到教導處,等他出來,高紅瑛問他:“教導主任找你幹什麼?”
“你父親是縣長?!”
高紅瑛低下頭。
“他們警告我不要和你走得太近。”
高紅瑛眼圈一下子紅了。
張輝民也心痛之極。
他知道那就是愛情。
可是愛情不會照顧他們註定分歧的命運。
畢業後張輝民分到一家企業當工人,高紅瑛被分到縣委辦公室。
隨後倆人各自結婚生子,90代初期,張輝民下海經商,和人合夥開了一家外貿公司,再後來他出來單幹,公司很快發展壯大,五年內將朋友的那一家也收購了,這段發家史在當地頗為傳奇。
到了2015年,六十歲的張輝民退休搬到紐西蘭,和兒子兒媳生活在一起,沒多久,他的愛人因病過世了。
⑥
這次回國,張輝民感嘆時代變遷太快,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屬於他們的那個時代,徹底消失了。
高紅瑛說:“消失就消失,咱倆都記得就行。”
張輝民說:“紅瑛你知道嗎,我想了你一輩子,夢了你一輩子。現在看到你,我還像當年那麼激動。當年我去給你偷饅頭,忍著人家廚房裡飄出的鹹肉香,我特難為情。那種餓得要命的人聞到肉香的感覺,就像我看到你又得不到你是一樣的。我的比喻很……不合適,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高紅瑛心裡說,傻冒。嘴上說:“兜兜轉轉,還不是繞到了一起。”
“是啊,當年你多麼高不可攀。”趕緊又補:“當然現在也高不可攀。”
高紅瑛“噗哧”一聲笑了。她說丈夫走後,自己過得也並不咋樣。她在給他機會。
張輝民接得很準:“那你沒想著找個老伴嗎?”
“想過。”
“我也是想過,但一直沒碰到合適的。真沒想到能碰上你!這可能是我一直沒碰到合適人的原因。”
高紅瑛笑:“你這次回來幾天?”
“一個月。”
“好,我明天帶你去吃老米鋪豆腐,全是過去的味兒。”
臨別時,兩個人抱了抱。抱得依依不捨蕩氣迴腸。兩次擁抱隔了將近半個世紀,人老了,背厚了,身子也重了,但眼睛裡跳躍的欣喜,與當年無差。
⑦
第二天兩人去吃老米鋪豆腐,張輝民讚不絕口。高紅瑛也挺有成就感,她說她做飯更好吃,在國外,他可吃不到這麼正宗的味兒。
吃完飯高紅瑛又帶他去買東西,逛街時看到路上有坎兒,張輝民本能地伸手去拉高紅瑛,拉上了,就不撒手。兩人看上去像挺普通的一對老夫老妻。高紅瑛有些感動。想想自己的那些擇偶條件,他全部都滿足。最滿足的是感情,這感情完全不需要用時間培養,它已經醞釀了半個世紀,沉澱為任何人都無可取代的信任。他讓她心甘情願把手交給他,把人交給他,把餘生都交給他,完成最終的圓滿。
逛了一天,張輝民也不嫌累。高紅瑛說:“你身體還挺好哦。”
“棒著呢!老當益壯!”
高紅瑛哈哈大笑。
“你笑什麼?”他過了一會兒反應過來,也笑起來:“是真的。”
他說:“我還有套房子在這兒,晚上你上我那兒去?”這時候說這話沒流氓意思,純粹是為了證明。高紅瑛笑得勾下頭去。
“行不行嘛。”他有點企盼又有點壞地瞧著她。
“行吧。”
高紅瑛跟他回家,竟有點害羞。她鬼鬼祟祟的,碰到他跟鄰居打招呼,她往後躲。張輝民一邊開門一邊說:“你躲什麼呀,我家就是你家。”
他的房子挺大挺好。倆人聊了一會天兒,張輝民去洗澡,洗完問她洗不洗。她說她也洗,張輝民屁顛地去找吹風機,找浴巾,找新牙刷,找睡衣。瞅他那激動樣,她也激動起來。張輝民把什麼都準備好,擱在洗手檯上,然後像個小男孩一樣,用畢恭畢敬掩飾著興奮,一臉正經八百地把門帶上了。
高紅瑛在洗手檯上刷牙,發現他手機落洗手檯上了。
來了一條微信,訊息浮在手機上。
兒子:“靠不靠譜啊?”
高紅瑛忽然直覺,他們在討論她。
她劃開訊息,他手機竟然沒上鎖,她輕易看到了前面的聊天記錄。
兒子叮囑他:“這次回去就兩件事要辦,一,拆遷手續,二,保姆必須中國菜做得好。”
後面他說沒問題,兒子問他保姆找到了嗎,是哪個家政公司的,得在大家政公司找。他說不用去家政公司,他找了個熟人。
高紅瑛刷牙的手停下來。
原來他是為了找保姆幫帶孫子。她一個活得逍遙自在的老太太,每個月還去美容院做臉做背做“私護”,這半輩子都活得飛揚跋扈,老了,竟然差點被人利用成保姆!
牙也不刷了,高紅瑛臉上還有泡沫,連鏡子都懶得再照,美給他看?他配嗎。她一把將門拽開,拿著張輝民手機說:“你手機落這兒了!”
“哦!”張輝民有一絲慌亂。這一絲慌亂叫她徹底死了心。如果他穩穩的,她倒還懷疑他是在應付孩子,可他的肢體和表情出賣著他,他就是在找保姆。
高紅瑛進去扯一截衛生紙抹了一把嘴,連他找的毛巾都不用,覺得膈應。
她挺著脖子邁出來:“張輝民,你是不是想把我帶紐西蘭去?”
“嗯……”
“以什麼身份?”
“當然是我老婆的身份。”
“可是這些年你生活在國外,我就是一退休老太太。我們有共同語言嗎?”
“我們怎麼會沒有共同語言呢?我們有那麼多回憶。”
高紅瑛苦笑:“一兩天都回憶完了,以後呢?”
張輝民知道她突然間的變化是因為看了他手機,他有些尷尬:“你不相信我的真心……”
“談不上真心,也談不上假意,只不過這麼多年早就沖淡了咱們的情誼。你在商場上闖蕩,選什麼東西都要先掂量價值。你瞭解我,覺得我可靠,我也能理解。可是我也要照看我的孫子,我也有我的一大家子,我早就融在我自個兒的生活裡,咱以前算是好過一場,一輩子都不忘,但也停那兒吧,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咱們現在都牽扯得太多,走不到一塊兒去了。”
張輝民還想解釋,高紅瑛要走,他跟在後面囉裡吧嗦講了一堆,大意是兩個人還是合適的,他是有真情的,甚至他要想娶她還得過兒子那關,那關不是那麼容易過呢。張輝民越說她越冒火,回頭吼了一句:“不用送了!”
⑧
潮溼的身體突然冷卻下來,就結了冰。高紅瑛搭了個計程車回去,碰到小女兒悶悶不樂地坐在沙發上玩手機。她繼承了她的基因,坐著躺著歪著,都漂亮得突兀。
“你怎麼還不睡?”
小女兒說:“相親去了!”
“咋樣?”
“還能咋樣?吃完飯要看電影,看完電影要唱歌,我不想去,這歌一唱就唱到半夜,倆人再喝點酒,他要不提出去開房,我跟他姓。”她又嘟囔著:“男人都只是想睡覺,一點意思沒有。”
高紅瑛說:“想睡覺就把你氣成這樣,等你再拖拖你就知道更難受的不是想睡覺。”
“還能想幹啥?”
高紅瑛笑笑,沒有揭穿。但她聽得見自己內心深處關於愛的引擎停下來了,它的轟鳴和顫抖一點點變靜,最後兩下抖得尤其心傷,是拼盡了全力的告別,然後熄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