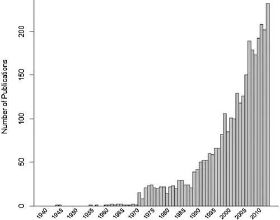2016年11月,吳偉歸安大高玄殿寶匣。作者供圖
2013年在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讀完本碩,我陰差陽錯地進入故宮博物院。其實這並不是我首選的單位,那時候“宮裡”還沒有考古的部門和崗位,雖然在碩士階段專攻建築考古方向,參與了一些古建築調查測繪工作,但我還是一心撲在考古上,想做古建築材料方面的研究。
“入宮”之後,我被分到了工程管理處,一個我完全不瞭解的部門。錄取之後在官網上檢索才知道,這是做古建築修繕工程管理工作。我有點傷感,看來就此要遠離考古了。沒想到,這是一次新的出發。
入職不久,我跟著任務分工參與了寶蘊樓修繕保護工程專案。剛走出校園的我,對一切充滿好奇和興奮:好奇的是,故宮的古建築修繕保護有著怎樣先進的理念和技術;興奮的是,我似乎可以一展身手,畢竟自己還學了點古建築知識。
然而,真正參與其中,我被潑了一盆冷水——自己以前學的偏重保護理念和形制研究,卻解決不了修繕過程中實際出現的具體問題,對於北方官式建築及工藝做法也基本不瞭解。最關鍵的是聽不懂“行話”,一跟施工人員聊天就知道自己不懂行。
但考古人天性樂觀,對世界保持好奇心,而且對於考古人來說,下工地不算事兒,只不過我從原來的“入地”,變成了“上天”。
我每天干得最多的,就是揹著相機爬腳手架,觀摩外界難得一見的修繕工作,向同事、同行、施工方和工匠們討教,把修繕的每個過程和做法都用相機拍下來,整理記錄。不僅是自己參與的專案,我還經常串門到其他同事的專案中去學習。就這樣慢慢地,我能看懂匠人們乾的活了;又花了很長時間,我能看明白他們幹得好不好了,到這一步,我才算是一腳踏進了古建修繕圈的門。
在寶蘊樓的修繕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古建築有很多隱蔽的部位,這些部位蘊藏的很多資訊,可能只有透過修繕才會重見天日,有的還可能顛覆以往的認知。
古建築修繕的一些環節,其實跟考古的解剖、發掘過程一樣,其間會有大量的原始痕跡資訊暴露出來,而且很多資訊在修繕過程中會消失,且不可逆,這更需要全面仔細地記錄。但修繕工程的記錄和考古記錄並不一致,前者偏重施工工序,重點並不在於記錄暴露出來的歷史資訊,這一部分往往一帶而過。
我突然覺得,自己找到了考古和古建築修繕之間的一個契合點。既然修繕的歷史資訊記錄比較薄弱,而考古的強項正好是記錄,那我何不發揮自己的考古技能,用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來加強這一方面的記錄和研究呢!
很幸運,我得了一個好機會。2015年,我開始全面負責故宮大高玄殿修繕工程的現場工作。有了寶蘊樓專案的經驗積累,我想把考古的理念方法運用到古建築修繕保護過程中。此時,我已加入了故宮考古研究所,一個在我入職不久後、2013年年底成立的非建制研究機構。
我將古建築的屋頂視為層層疊壓的“考古地層”,對上面所有的資訊按照營建層次和不同時期修繕所產生的疊壓打破關係,進行全面細緻的提取記錄,以獲取其不同時期營建、修繕所留下來的歷史資訊和工藝做法,最大限度儲存“真實性”和“完整性”。
因此,我首次帶領故宮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隊員們走上屋頂,在屋頂上佈置探溝、進行“考古解剖”,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發現。同時,我們把發現的重要遺物,按照考古學的方法進行編號、記錄與儲存,彌補了施工中大量文物資訊丟失的現象,也為後期的修繕保護方案提供了科學的歷史資訊依據。後來,這被大家戲稱為“屋頂考古”,也成為故宮考古的一大特色。
記錄與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紙上,這是與考古工作最大的區別。考古是發掘完了回填、收工,回到室內整理研究;而修繕專案是在解體之後還要再安裝還原回去。
曾有一座建築的木基層殘損嚴重,由於它在不同時代都經過修繕,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制做法,施工單位就來問我們和設計單位,以什麼形制為準進行復原。木基層是古建築的隱蔽部位,常常在施工圖紙裡得不到體現。但我們事先曾進行了詳細的測繪記錄,對現存的各種形制做法進行了分析,確定了原始做法。我們把資料圖紙給施工方,他們非常驚訝,也是心服口服,並據此進行修復。
在修繕過程中,我其實更多充當一個資訊記錄員的工作,跟著工匠,哪裡有修繕就“考古”到哪裡。我似乎又回到了考古現場。
在屋頂上的“考古”,讓我找到了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方向——在故宮把考古做成故宮特色,乃至中國特色,也讓我深刻感受到了考古的外延和生命力。從卸下的瓦、木、磚等各種構件上發現的資訊,似乎在向我傾訴一部無聲的史書,又像一幕幕電影在向我展示當時的人、文化以及社會。
(作者系故宮考古研究所工程師)
吳偉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