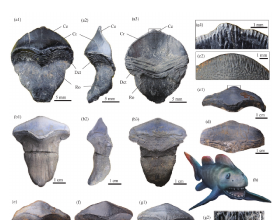羅志田
《昨天的與世界的:從文化到學術》,羅志田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昨天的與世界的》是我到北大教書後輯成的第一本面向非學院讀者的書,這些文字大多不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因寫作機緣不同,雖不免時泛迂遠之氣,畢竟說話相對隨意。而原序中所說的一些題外話,如今回看,頗有些感觸。
我是2003年初“非典”起而不宣的時候到北京的,當時如果公佈了,我就會延遲赴京,甚或就不會去了,因為導致我離開川大的“契機”,就在那期間改變了——
2002年我們歷史系透過的兩位博士生導師被學校否決了,我是分委員會的主席,不能不引咎辭職。學校當然挽留,先是一向很少過問他事的劉應明院士(時任副校長)撥冗給我這個後輩打了兩個多小時的電話,說及兩位中的一位別處已有大用,可以不必堅持了。隨後分管校領導來寒舍晤談,說得很坦誠,曰學校也不能沒有面子,可否各退一步,兩中上一?於是我們達成妥協。但這建議“上會”後卻未能形成決議,無疾而終,於是我也就踐諾北上了。
稍後川大更換了校領導,新校長是外來的院士,在“非典”警報解除後,帶了八位部處院系領導專程到京請我吃飯,命回校服務。這樣的陣仗,至少我是頭一回遇到。對於校長的禮賢下士,不能說不感動!但我也只能誠實告訴校長,我已不是小青年,不能言而無信,既已正式入職北大,恐怕一時很難離開,唯有期以後來。事後想想,若“非典”提前公佈,我的北上時間就要延遲數月。在此期間,很可能就被新校長挽留,便又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了。
因感恩北大對我的收留,並予以超高的待遇,所以到京就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閉門讀書教書寫作,不在北京演講(北大校內除外)。這個規矩基本遵循,在京十多年,只有極個別的時候以不公開發布的方式在校外有過幾場演講。這樣的心態在初版序言中隱約可見,其中引了兩段話,一是張彭春說“在他地教授者,多喜來京”。而“至京則懶惰優遊,毫無出息,不如前之勤奮”。一是傅斯年說陳寅恪在清華能“關門閉戶,拒人於千里之外”,於是“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數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我是心裡帶著這兩段話進京的,常以自勉。學問做不到前輩那樣高的境界,至少在勤奮上可以跟進。
由於重看書中關於“非典”的命題作文,回憶起昔年的情狀,不免心動,乃說些題外話。言歸正傳,本書的新版在兩年前已經與三聯書店簽約,同時簽約的還有最近剛出的《風雨雞鳴》。因為兩書同時編,所以內容有調整。其中本書“影響歷史的人物”一編悉數移出,放到《風雨雞鳴》中了。而新增的文字也不少,整體從原來的六編改為現在的七編,各編的具體內容也有不小的調節。因為人物的移出,書名的副標題也改為“從文化到學術”。
雖然簽約已較長時間了,因我長期未交出新版序言,書的編輯也一再推遲。適譚徐鋒工作室想要出此書,承三聯書店高誼,同意轉讓。出版社惦記的背後,大約是讀者的不棄,對此個人銘記在心,既非常感動,也非常感謝!既又籤新約,新序的撰寫也不能不加快了。
看稿時對比新增的文字和昔年的文字,頗覺那些年的心態比現在更積極,參與意識也更強,對學界的一些自以為不順眼的現象,頗欲貢獻意見。其實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社會,包括常被詬病的大學管理層,雖總有讓人不滿的一面,卻也有著不少溫馨的人和事。這樣的兩面性,從上述我辭職的經歷就很可看出。然而當年的建言,還是偏於批評的多,而讚揚的少。後來新增的篇目,就要恬淡平靜許多。可能是因為馬齒漸增,銳氣日減。不過最後一文裡無意中提到了將無同和蒼茫等人眼中閃爍的火花,或許那時的人就是比現在更理想化,亦未可知。
那是一篇為徐芳的《中國新詩史》所寫的書評,儘管出以非學術的形式,探討的卻是一個大問題——詩歌何以離我們而遠去?中國本是一個詩的國度,讀詩寫詩曾經相當普及。這個數千年持續的傳統,一直延展到二十世紀,卻在世紀之交寂然淡出。究竟是什麼力量,能不聲不響地消解一個長期延續的傳統,竊以為是一個亟需探討的重大題目。
再插一段題外話,我自己少年時曾在前輩指點下學過舊詩,不過尚未入門(連韻都沒來得及認真背就忽然可以考大學了),僅略知好壞,屬於眼高手低的一類。大學雖然讀的歷史系,仍帶點文學青年的遺風。進大學的第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出了陳寅恪的文集,七冊中我僅買了三冊,就是《柳如是別傳》。在陳先生的著作中,這是一般史學中人最不看重的一種。而且我們那時真沒什麼錢,買這三冊書是要少吃很多份肉菜的。就因以前讀過柳如是的詩,那句“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感覺能以如此疏淡的文字抒寫深情,必是高手。慚愧的是,或因隨後心思逐漸轉入史學,那書買來也沒認真看,然而對詩的感情是持續的。
要知道“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一個沒有詩的文化,一群沒有詩意的人,是不是缺了點什麼?那篇書評的題目是“歷史的不完全”,所本的是徐志摩的看法——歷史如果“沒有一部分想象的詩式的表現,是不完全的”。而本書的題目出自聞一多那句“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當我們心懷如此理念時,卻要面對一個逐漸無詩的中國,能不有深深的“不完全”感?
今天是冬至,昔以為陰極陽起之日。記得某位外國詩人說過,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遠了。是為盼。
2019年12月22日於青城山鶴鳴山莊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