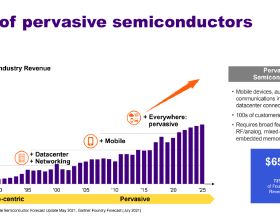“探源中華文明 傾聽燕趙跫音”大型全媒體考古系列報道之平山戰國中山王墓考古
翟蕩滹沱
這,是一個刻在石頭上的故事。
繼上世紀六十年代,滿城漢墓(西漢中山國)橫空出世僅僅數年,在滹沱河畔,另一個“中山”破土而出。它,就是被譽為“戰國第八雄”的戰國中山。圍繞該墓葬的系列考古,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
太行煙雨,白狄部族。戰國中山,歷史短暫,史載缺略,遺蹟湮沒於地下,兩千多年來鮮為人知,故稱“神秘王國”。幾十年的持續考古,填補了史海空缺,釐清了中山國後期世序,其精美珍寶和超凡藝術對當代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青銅、銘文、篆刻;征戰、興衰、融合……自春秋初年起,這個神秘部落從西北輾轉遷徙而來,從黃土高原插入太行腹地,以其獨特個性,五百年裡縱橫決蕩。在太行南麓的沃土上,演繹著一段恢弘的民族融合史。
中山國王陵陳列館。 中山國古城遺址管理處供圖
破譯“守丘刻石”
中國人喜歡石頭。但眼前這塊石頭,實在太不起眼。
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庫房內,一塊河光石靜靜躺在角落裡。長約90釐米,寬約50釐米,厚約40釐米,是滹沱河畔最常見的石塊。然而,真正價值連城的寶物往往就是這樣,彷彿有一層神秘包漿,沒有機緣和智慧,只會靜待明主。
這塊石頭,在滹沱河畔的泥土中,已深埋2000多年矣。
上世紀30年代,平山縣三汲鄉村民劉喜梅掘地開墾,偶然發現一塊河光石,上刻奇怪符號,他便把石頭搬回家中。世事變幻,轉眼到了1974年冬,三汲鄉大規模平整農田,農民們在附近大土丘發現了一些瓦片。河北省考古隊隊長陳應祺帶隊前去考察,尋到劉喜梅家中,見到了這塊石頭。
符號豎刻,像是大篆,又像是甲骨文。它們究竟是何種文字,又寫了些什麼呢?
陳應祺想到了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於是寫信求教。李學勤經過仔細考證,將其破譯為:“監罟有(囿)臣公乘得,守丘(其)臼(舊)(將)曼,敢謁後賢者。”具體解釋為,“現任監罟(注:監管捕魚的小官)的罪臣公乘得在此看守陵墓,他的舊將曼敬告後來的善良賢德的人”。
這塊石頭,後被稱為“守丘刻石”。這是中國已發現時代最早石刻文字之一,不僅對於戰國文字研究有很高的價值,而且對於尋找戰國中山提供了重大線索。曾有專家評價,如果不是破譯了這幾個字,戰國中山的橫空出世可能要推遲多年。“守丘刻石”的破譯,堪稱開啟中山國大門的一把鑰匙。
戰國中山,史書寥寥,語焉不詳。《史記》載:“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可兩千多年來,都城到底在哪裡,一直困擾著研究者。正是破譯了這塊相當於墓碑的刻石,考古人員推測,這一帶可能有王陵。
經過勘察,1974年11月,河北省文物管理處開始對M1墓展開發掘,清理三個陪葬墓和東西兩側建築遺蹟;1977年,清理其他三個陪葬墓、殘存在南側的建築及大墓主室;1978年,清理了二號車馬坑、雜殉坑和葬船坑。透過對M1與M6兩座墓的形制和隨葬物品分析,研究認為,M1主人應為中山國王,M6主人也應為王一級別。197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結合史料,充分確定了戰國中山國後期都城——靈壽古城。
1978年秋至1980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全面勘探靈壽古城的城垣垣基、夯築基址、城外墓葬、古道路,繪製城址平面圖。1980年4月到1987年1月,又在城址內先後5次發掘,發掘面積達9205平方米,搶救性發掘了城內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夯土建築遺址和居住址,清理了城址內外春秋中晚期至戰國中期的小型墓葬131座。
為配合朔黃鐵路建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莊市文物保護研究所、中山國古城遺址管理所對中山國相關遺存進行發掘。1997年12月至1998年8月,聯合對青廉戰國兩漢墓群進行搶救性發掘,共發掘墓葬415座,其中戰國墓葬250餘座,西漢和東漢墓葬138座,共獲得陶、石、玉、瑪瑙、水晶、銅、鐵等各類隨葬品3000餘件。
1998年4月開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歷經4個月在平山縣訪駕莊、北七汲、中七汲、郭村等地展開考古勘探發掘。訪駕莊發掘東周土坑豎穴墓9座;北七汲發掘戰國時期遺址175平方米,春秋土坑豎穴墓4座;中七汲發掘戰國土坑豎穴墓65座;郭村發掘戰國祭祀坑142座。同年4月至8月,對靈壽縣崗北東周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共發掘墓葬165座,出土銅器、陶器、玉器、瑪瑙器、石器、骨器等各類遺物……
回望歷史,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山國遺址及文物被大量發現,考古工作者在三汲村附近勘探了中山國都城靈壽古城,發掘了五座中山王族墓和百餘座平民墓,共出土文物兩萬餘件,基本弄清了城址範圍,城牆構築方式,城內道路、水系、大型宮殿建築基址、手工業作坊遺址、居民居住址等遺址佈局結構。
“中山是個藝術的民族,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那深沉悲壯的歌聲,它那婉約清麗的琴聲,它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們無緣傾聽和欣賞了,只有屬於兩千年前那些精美絕倫的遺物還留在我們的視線中,不時提醒我們:腳下這塊土地上,曾經有一個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個盛極一時的國家……”曾指導發掘滿城漢墓的郭沫若獲悉戰國中山橫空出世,並見到器物照片時,在病榻之上寂然神往。
尋覓中山古國
歷史,有多重視角。豐盈,固然可貴;缺失,亦不失為一種曲筆。與磅礴厚重的七雄相比,“千乘之國”似不足掛齒。反映在歷史記載上,對於中山國淵源脈絡,只能從幾篇殘存文獻中,去尋覓這個“戰國第八雄”的風雨飄搖——
中山族群,源出北狄。戎狄蠻夷,合稱四夷,是先秦中原王朝對四鄰民族的泛稱。狄,曾廣佈黃河流域,因地處中原之北,又稱北狄。白狄,是北狄支系,原與秦同居雍州,在晉國西,後漸徙晉東,包含肥、鼓、鮮虞、仇繇四個部落。目前,普遍認為,中山國系由白狄族鮮虞部建立。
《國語·鄭語》載:“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這是史籍文獻關於鮮虞最早的記載。
公元前774年,傳說中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快活歲月。鮮虞,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很快就淹沒在白狄群體之中。而西周的歷史,隨即在犬戎攻入鎬京時,荒唐而殘酷地結束了。幽王之子宜臼東奔,諸侯擁立定都洛陽,史稱東周,是為周平王。
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歷史車輪進入春秋。
周簡王四年(公元前582年)“冬,秦人、白狄攻晉”。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滷(杜注:大滷,太原)”。魯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有史學家認為,正是這一年,蟄伏240多年的鮮虞再次橫空出世,成為白狄部落聯盟首領。
《左傳》中記述,魯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後“克鼓而反……以鼓子鳶鞮歸”。魯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呂氏春秋·權勳》載:“中山之國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仇繇之君將斬岸堙溪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必欲攻我而無道也……君因斬岸堙溪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赤章蔓枝)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仇繇亡。”這是一段殘酷的篇章,智伯於周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被趙、魏、韓消滅,那麼白狄族分支仇繇的滅亡最晚當在公元前453年以前。
《左傳》中又載,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春三月……言於範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
——這是最早關於中山的記載。學者們多以該年為早期中山立國之年。
歷史記載簡約閃爍,給後世留下諸多難以索解之謎。
公元前506年到公元前414年,鮮虞與中山並稱。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414年),《史記·趙世家》記載“中山武公初立”。此後便無鮮虞,只見中山。
《戰國史》中記述,“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攻滅中山,命長子擊守之。後三年封少子摯於中山。”《史記·趙世家》中記述,“公元前377年,趙與中山戰於房子”,中山復國。
史料中又多有記載:公元前323年,“公孫衍發起燕、趙、中山和魏、韓五國相王”。公元前299年,“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公元前296年,“(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
儘管謎團眾多,但我們基本能勾勒出一個蒼茫圖景:自公元前506年後的二百餘年裡,中山國起起落落,在群強環伺的中原文化圈內奮力求存,以其倔強不屈和勇武善戰譜寫了一部文化交融的傳奇。
然而,掩卷自問,這樣的勾勒精確嗎?合乎歷史真實嗎?是歷史的全部嗎?
歷史,不單由筋骨構建,更應血肉豐滿。此前,人們普遍認為,中山國是嵌在燕趙之內的蠻夷小國,因城中有山而得國名,即便偶有作為,也不過曇花一現,故史載不詳。但是,這些若隱若現的記載,又晦澀含蓄地暗示世人,這樣一個小國,竟能與齊、魏、燕、趙等強國相抗衡,稱王於太行山麓,恐不可等閒視之。
戰國雄風,中山若何?
歲月模糊了真相,令人長嘆,但幸而又垂青考古。上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山王墓和靈壽古城發掘,中山國從滹沱河畔的風雨之中漸露真容,向世人撩開那神秘、華美而令人嘆惋的面紗,印證、糾正、填補、豐滿著中山國的血肉脈絡。
見證華夏融合
“一切的繁華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隨時光的流逝隱遁於地下,我們努力地去想象那曾經的亭臺樓閣,那曾經的金戈鐵馬,那曾經的絲絃笙歌……”病榻之上的郭沫若,如此描繪雄踞太行的中山,濃濃國風,撲面而來。
這是中原沾染異域風情?還是草原習得華夏精髓?
構思奇巧的珍寶、瘦挺骨感的中山篆……歷史長河中,後世有很多更強悍的漠北部落策馬中原,陸續建立了不朽或速朽之大業,也創造了燦爛文化。但品味其文學作品、藝術風格、精美器物乃至典章制度,儘管宏大層面上頗為同步,卻始終難言水乳交融,總缺乏那份不卑不亢的對等和談笑自若的底氣。
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山國是極獨特的存在。因為,僅就藝術創造和文化心態而言,迄今為止尚不曾見到在這等規格上,如此完美地既浸淫著華夏風格,同時又恪守漠北特色的文化藝術。
其背後,隱藏著什麼,昭示著什麼?
從獨樹一幟的器物說起吧。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座,入選河北博物院十大鎮館之寶,也是國家文物局規定的不準翻模複製文物。這件器物,極具建築學領域的開創意義。比如,四個龍頭分別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樣式是按照木構建築挑簷結構製成,將史籍所載斗拱技術出現於漢代的時間提前百餘年。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錯金銀虎噬鹿屏風底座、錯銀雙翼神獸……器物灑脫奔放,不似中原常見器物那樣中規中矩,反映了古中山人北方民族的獨特氣質。”曾有文物專家慨嘆,古中山只是“千乘之國”,在七雄夾縫裡生存都能創造如此燦爛之文化,可以想見戰國七雄及戰國時代的中國,手工業已何等發達!
但是,更深層次的價值遠不止於此。“中山三器”(鐵足大銅鼎、刻銘銅方壺、刻銘銅圓壺)及其銘文的出現,告訴世人這是多麼精美的書法,且清晰勾畫出失落的中山國世系傳承,更警醒的是“勿忘爾邦”的歷史鐘聲。
刻銘,填補了史書文獻之不足。其一,豎立了年代標尺。銅方壺“唯十四年,中山王命相邦賙”,銅鼎“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的銘文,說明二者鑄於王在位第十四年。同時,三件器物銘文都記載了燕王噲讓國及“邦亡身死”之事。燕國子之之亂亡國發生在公元前314年,據此推斷,中山王墓年代上限不會早於此。銅圓壺銘文刻於中山王去世之時,壺上有“王十三年”紀年,推測王去世為公元前313年。
其二,明確了中山國後期幾代王公世系,銅方壺“唯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純德遺訓”,由此可得知,中山國君共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等七代。
其三,銘長創紀錄。青銅器,西周多見長銘,戰國多為短篇,多者十幾字,少者幾字,“中山三器”打破了這一舊說,銘文總和1123字,其中大鼎銘文469字,僅次於西周宣王毛公鼎銘文497字,創戰國青銅器長銘之最。銅方壺銘文450字,用儒家思想,闡明得賢、民附和鞏固政權的道理。銅圓壺腹部銘文182字,為嗣王紀念先王之悼詞。
“中山三器”古樸深沉,出土後轟動世界。長篇銘文和青銅器,既保留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又融合了華夏傳統,為研究中山國曆史文化和早期民族融合發展提供重要價值,承載著中華文明轟轟烈烈崛起的行進步伐和精神信仰。
然而,考古目光不能僅停留於此,還應具體而微。
作為文化載體和重要組成部分,中山王墓器物,為戰國中山國器物型別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其中,銅禮器及陶禮器組合為研究戰國早中晚期器物形制發展演變及其器物分期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獨特的墓葬結構,石槨結構墓室多發現於中山國地域範圍,上至王公,下至貴族階層,從春秋晚期延續到中山國滅亡時期,是白狄族群特有的埋葬方式,也是區別於戰國七雄埋葬習俗的最重要標識。
1979年,李學勤在《文物》期刊上發表《平山墓葬群與中山國的文化》,從考古學角度討論了平山墓葬群文化性質及白狄中山逐步華夏化的軌跡。在專著《東周與秦代文明》中,李學勤還把中山國納入到春秋戰國大背景中來討論,認為中山國是北方文化圈中非常典型的方國,中山華夏化應視為春秋以來民族文化交匯融合整個潮流的組成部分。這些觀點,對於今天我們研究中山國依然影響深遠。
但歷史教益又不僅於此。當把多年考古成果和存世文獻相結合時,人們更驚訝地發現,儘管失落了2300多年,但中山國的影響始終不曾風吹雲散,而是作為文化根脈的一部分,早就深深融入中華文化之中。某種意義上,其墓葬、器物、城址等考古發掘,不僅僅是文化的接續,更是正本清源、追溯源流、回眸審視。
然而,我們回溯源頭,甄別史料時,有兩段記載也尤需警醒——
“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呂氏春秋》)“中山地薄人眾……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史記·貨殖列傳》)
文字如畫,風俗入目。大家史筆,寥廓悠遠。這,既是狄人固有習俗,也是中山民眾夜以繼日生活狀態之反映。曾經,幾乎完全華夏化的中山國,被一支穿著戎狄之服的騎兵軍團滅國。耐人尋味的是,這些騎兵來自一箇中原正統國家——趙國。如今,面對那些巧奪天工的器物,我們更應聆聽中山先輩對繼任者的諄諄告誡和對群強環伺的憂思。
如此,也就釋然,為何中山國有異域風情,卻這般交融無痕。
歷史,總充滿神奇的機緣。時值春秋戰國,正是中華文明融會貫通,爆發最自由、最純粹爭鳴之際,是大變革、大交融的前夜。歷經五百多年風和雨,正在孕育一個萬世綿延之根脈。 (張文瑞 龔正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