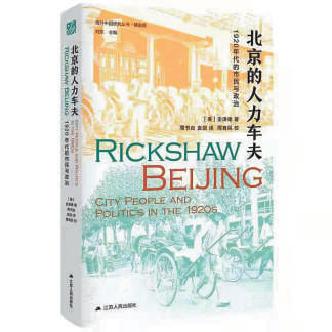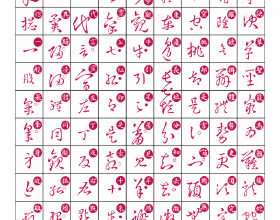如果我們突然回到1920年代的北京,人力車或許也會成為我們對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李景漢曾估算,當時北京的壯勞力中,每6人中就有1名人力車伕,他們連同家眷佔了北京近20%的人口,每天拉客高達50萬次,而當時北京城的人口也不過略微突破100萬而已。(李景漢:《北京人力車伕現狀的調查》,《社會學雜誌》1925年第4期)美國學者史謙德(Davide Strand)即以人力車為切入口,寫出了著名的《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聚焦於那個遍街跑著人力車的北京時代。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北京不再是皇帝的京城。進入1920年代,中國陷入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之中,北京處於動盪的時空。
儘管1920年代的北京失去了專制王朝時代的帝都地位,但“北京社會自然而然地追逐權力,這恰是這座城市五百年來最主要的產物和資源”。(《北京的人力車伕》,13頁)各式各樣的舊官僚、舊思想與舊勢力充斥著這座城市,使其比起上海、廣州、武漢等較早浸潤歐風美雨的口岸城市,顯得抱殘守缺。例如北京的商會更“傾向於遷就甚至是服從官權”。以至於受新思想影響較深從而積極籌劃參與抵制日貨和抨擊政府的商會會長安迪生,很快被控入獄並丟掉會長之位。而這恐怕源於其他商人對安迪生“激進行動”的不安,因為“他們把帶點自律和自主的順從看成是治安和賺錢的關鍵”。(第5章)
不過即便如此,北京還是發生著變化,儘管顯得速度慢一些。在這座城裡,不僅有傳統的水會、行會、民團等舊組織,也逐漸產生了現代意義的警察、商會、政黨和工會等新組織,並且有著密切的互動。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市民的政治意識和參與度逐步提高,而軍閥、政客、知識分子和人力車伕等群體則在各種博弈中扮演了頗為關鍵的角色。史謙德正是以上述關鍵詞為著眼點,“既細緻地描摹了1920年代北京的生活,又深入地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剛剛獲得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的周錫瑞認為,“在警察和人力車伕、商會和工會、政黨和行會的相互作用中,史謙德發現了一種嶄新的政治活動‘公共’領域的出現。這對我們理解近代中國政治具有開拓性的貢獻。”
車伕與警察:祥子與“我”的鬥爭與轉化
一說起北京的人力車,恐怕大部分中國讀者都會想起老舍的《駱駝祥子》。老舍在這部名著裡不僅塑造了由破產農民而轉為人力車伕的祥子,也塑造了車廠老闆劉四爺及其女兒、也就是祥子的老婆虎妞,和祥子的僱主曹先生等一系列人物。史謙德則以翔實的史料,考察了北京的車伕、乘客、車廠老闆的來源、構成、生活環境和工作情況等問題,給我們展現了一幅圍繞人力車的北京社會全景畫面。人力車伕們是20世紀20年代這個黑暗社會的底層,往往“離可怕的貧困線卻只有一步之遙”。有時候,一次意外就足以壓垮一個車伕的家庭。並且,車伕是靠體力吃飯,其職業生涯“從起步起就開始走下坡路,一旦年老體衰,便直線下滑”,陷入悲慘的晚年。(50頁至52頁)
然而,史謙德指出,老舍等當時的作家們“為了鞭笞民國社會的不良現象,戲劇化地描寫了人力車伕的生活”,將其當做受害者來描寫。這當然不錯,但這“只反映了車伕真實生活的一部分”。(45頁)實際上,車伕的世界要複雜得多。
面臨生活重擔,車伕們也不得不發展出一系列帶有底層特有色彩的街頭生存智慧。“在一座‘陌生人世界’的城市裡拉人力車,爾虞我詐簡直是家常便飯。”(62頁)史謙德指出,“這些‘街頭喜劇’終將演變成街頭政治,並相應地促使車伕們投身於大眾政治。”(45頁)郭德綱的相聲《怯拉車》裡就描寫了善於花言巧語、深諳乘客心理的“車油子”和坑蒙拐騙的“拉車賊”,可以為此做一註腳。
而當發生類似車伕與乘客的矛盾等“街頭喜劇”時,就該警察上場了。警察不僅負責維持社會治安,還要管理交通秩序,也要處理車伕和乘客之間的矛盾,這不得不使車伕厭煩警察。但遇到麻煩時,車伕又不得不向警察尋求幫助。對此,史謙德總結道:“車伕和警察難解難分,他們之間有著一種時而對立時而合作的關係。北京現代化警察官僚體系的發展與人力車行業的興隆形影相隨。”(63頁)
的確,車伕和警察可算是1920年代北京的關係複雜的難兄難弟。在老舍另一部名著《我這一輩子》中的“我”,就是一個警察。“我”原本是一個裱糊匠,由於時代變遷,生意銳減而沒了活路。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巡警和洋車是大城裡頭給苦人們安好的兩條火車道。大字不識而什麼手藝也沒有的,只好去拉車。拉車不用什麼本錢,肯出汗就能吃窩窩頭。識幾個字而好體面的,有手藝而掙不上飯的,只好去當巡警。”實際上,警察和車伕往往互相轉化。“我”曾遇上一位教官,“頭一天教我們操法的時候,忘了叫‘立正’,而叫了‘閘住’。”他就是拉洋車出身。(老舍:《我這一輩子》,第5章)史謙德也記敘了北京街頭一個警察和車伕衝突的案件。而這位車伕之所以對警察的管制憤憤不平,正在於“我也幹過警察,當過三年,知道規矩”。(95頁)甚至有人為了補貼家用,白天當警察,晚上做車伕。(64頁)
車伕厭惡警察,又不得不依靠警察。警察也視車伕為街面上的麻煩製造者,但沒有了人力車,警察也失去了重要的存在意義。這種複雜的關係,還體現在商人與政客、工人與行會、市民與知識分子乃至新舊技術、產業之間,在《北京的人力車伕》中得到了立體而豐富的展示。
交通問題折射出社會的面貌
與作為現代化產物的電車相比,人力車顯得落後且不人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車本身也是現代的發明。它在當時被叫做洋車,即東洋車的簡稱——它實際上是日本人在1860年代的發明。它的盛行需要橡膠輪胎、避震彈簧、滾球軸承和路況良好的硬質地面,而這些都是現代性的產物。然而除此之外,它也需要一些前現代的東西。例如大量掙扎在溫飽線上的貧民,提供了廉價的人力,以至於僱一個人拉車比養一輛馬車、牛車便宜得多。北京的電車在20世紀上半葉始終未能取代人力車,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客源太少,因此無法將電車運營成本降下來。而客源很少的原因在於,北京是一個消費城市而非生產城市,它沒有發展出太多現代的工業,缺乏大量需要在住所與工廠之間通勤的工人。可以說1920年代北京人力車的風行,從各個側面反映了民國社會的新舊雜糅和變遷。
陶孟和在其1928年出版的《北平生活費之分析》中認為,“各種失業之工人,無論有無技能,莫不以之(人力車)為棲身之所。”(38頁)
交通問題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側面,但窺一斑而知全豹,從中也能折射出整個社會的面貌。1920年代的北京,由於車伕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乘客,使得人力車越來越“卷”:1911年的車伕平均每小時可以獲取2角5分的報酬,到1926年則只有1角了,這使得北京的車伕跑得比東京等其他地區的同行快得多了。儘管警方曾試圖禁止“飛跑”以帶來的交通事故和車伕的猝死,“但是在北京拉車這一行當的現狀,使得限速和其他各方面不合理的措施很難推行。”(48頁至49頁)
史謙德講述的是100年前的北京,今天北京城裡早不見人力車的蹤影,除了後海等少數區域(但也早已改良為三輪車,作為一種塑造“老北京”風情的旅遊產品)。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謙德《北京的人力車伕》不愧是一部佳作,它不僅增進了我們對100年前中國社會的瞭解,也激發了我們對當下的思索。(責任編輯:李崢嶸)